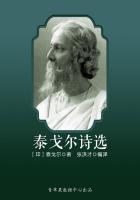“那就好,现在你的表几点?”
“十一点二十二分。”
路路通伸手从裤腰上的表袋里掏出一块大银表,回答道。
“你的表太慢了。”福格先生说。
“请您别见怪,先生,我的表是不可能慢的。”
“你的表慢了四分钟。不过不要紧,你只要记住所差的时间就行了。好吧,从现在开始,也就是自1872年10月2号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二十九分之后,你就是我的佣人了。”
说罢,福格先生站起身来,左手拿起帽子,用一种机械的动作把帽子往头上一戴,一个字也没说就走了。
路路通听到大门头一回关上的声音:这是他的新主人出去了。没过多久,又听见大门第二回关起来的声音:这是原先的仆人詹姆斯·伏斯特出去了。
现在只剩下路路通一个人在赛微乐街的寓所里了。
“说真的,”路路通开始觉得有点儿迷惑,自言自语地说:“我在杜叟太太家里看见的那些‘好好先生’跟我现在的这位主人简直一模一样!”
老实说,杜叟太太家里的那些“好好先生”是用蜡做的,在伦敦经常有很多人去观赏。除了不会说话,这种蜡人做得几乎跟真人一样了。
在刚才和福格先生简短的会面里,路路通就已经认真仔细地观察了他这位未来的主人一番。这人看来大约四十上下,面容清秀端正,高高的个儿虽然略微有点发胖,但是并没有损及他的翩翩风采。金褐色的头发和胡须,光溜平滑的前额,连太阳穴上也没有一条皱纹。面色白净,并不红润,一口牙齿,整齐美观。他的个人修养显然很高,已经达到了相士们所说的“虽动犹静”的地步。他具有凡是“少说话,多做事”的人所具有的所有特点。安详,冷静,眼皮一眨不眨,眼珠明亮有神,简直是那种冷静的英国人最标准的典型,这种人在英国是司空见惯的。他们常被昂·高夫曼的妙笔刻画成或多或少带了一点学究气的人物。从福格先生的日常生活来看,人们对这位绅士有一种印象,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不轻不重,不偏不倚,进退得当,恰如其分,准确得跟李罗阿或是伊恩萧的精密测时计一样。事实上,福格本人就是个准确性的化身,这一点从他双手和双脚的动作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因为和其他动物的四肢一样,人类的四肢,本身就是表达感情的器官。
福格先生是这样的一种人,行动精密准确,从来不慌不忙,凡事总有准备,甚至连迈几步、动几下,都有一定的规律,生活一向按部就班。福格先生走路从不迈出多余的一步路,走道总是抄最近的走。他决不无故地朝天花板看一眼,也不无故地做一个手势,他的情绪从来没有激动过,也从来没有因为何事苦恼过。虽说他是世界上最不性急的人,却也从来没有因迟到而误过事。人们也都能理解他生活孤独,甚至可以说与世隔绝这一点。他觉得在生活中总要和别人交往,总会发生争执,这就会耽误事,因此,他从不与人交往,从不与人争执。
说到若望,他又叫路路通,是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在英国待了五年,一直在伦敦给人当亲随佣人,但他始终没有找到过一个合适的主人。
路路通与福龙丹、马斯加里勒那一流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些人只不过是些耸肩昂首、目空一切、装腔作势、瞪眼无情的下流痞子罢了,而路路通却不是那种人,他是个很正派的小伙子,他的相貌很讨人喜欢。他的嘴唇稍微翘起,看来像是准备要尝尝什么东西、亲亲什么人似的。他那长在双肩上的圆圆的脑袋给人们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真是个殷勤而又温和的人。在他那红光满面的脸膛上有一双碧蓝色的眼睛。他的脸胖得自己都能看到自己的颧骨。他青年时代的锻炼,给了他这样健壮的体格:身躯魁梧,肩宽腰圆,肌肉结实,而且力大非凡。他那棕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不像古代雕塑家那样懂得密涅瓦十八种处理头发的技艺,路路通只懂得一种:拿起粗齿梳子,刷刷刷三下,就万事大吉。
这小伙子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性格,不管是谁只要稍微考虑一下,都不会说他会跟福格的脾气合得来。他是否像主人所要求的那样具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呢?这只有到他真正工作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人们知道,青年时代的路路通曾经历过一段东奔西走的流浪生活,现在他很希望过上安定的生活,好休息休息。他听到有人夸奖英国人的作风是有条有理、一丝不苟和典型的冷静的绅士气派,于是就跑到英国来碰运气了。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老天还是没有眷顾他,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扎根。他先后换了十户人家,这十户人家都是些性情古怪,喜欢冒险,四海为家的人,这些人家都不合路路通的口味。他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年轻的国会议员浪斯费瑞爵士家做佣人,这位爵士老爷是海依市场的牡蛎酒吧的常客,晚上经常在那度过,他往往还会喝得烂醉,第二天早上叫警察给背回来。路路通为了不失对主人的尊敬,曾经冒险向爵士老爷恭恭敬敬地提了些很有分寸的意见。结果爵士老爷大发雷霆,路路通就不干了。刚好在这时候,他听说福格先生要找一个佣人,了解了一下关于这位绅士的情况,知道他的生活是十分规律的,既不在外面住宿,又不出门旅行,连一天也没有远离过家宅。为这个人工作,对路路通而言实在是太合适了。所以他就登门拜见了福格先生,把这件差事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谈妥了。
十一点半刚过,路路通发现赛微乐街的住宅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马上开始把整个住宅巡视一番,从地窖到阁楼处处都跑遍了。这幢房子干净、整齐、庄严、朴素,而且非常舒适方便,还真是合路路通的口味。这下路路通可开心啦,这所房子对他来说就像个蜗牛壳,贴体又舒适。这个蜗牛壳是用瓦斯照亮的,因为这里一切照明和取暖的需要只用瓦斯就能满足。路路通在三楼上一点没有费事就找到了指定给他住的房间。他对这个房间非常满意,里头还装着电铃和传话筒,可以跟地下室和二楼各个屋子联系。壁炉上面有个电挂钟,它跟福格先生卧室里的挂钟对好了钟点。两个钟准确地同时敲响,一秒钟也不差。
“这太好了,我这一回可称心如意了!”路路通自言自语地说。
他突然注意到,在自己房间的挂钟顶上贴有一张注意事项表。表上注明了他日常工作内容的所有细节——从早上八点钟,也就是福格先生起床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十一点半福格先生离家去俱乐部吃午饭为止——茶和烤面包要在八点二十三分送上,刮胡子的热水是九点三十六分送到,四分钟后理发……然后这位井然有序的绅士不在家的时候,从上午十一点半一直到夜间十二点,所有该做的事,统统都被预先规定好,交代得清清楚楚,写在注意事项表上。路路通高高兴兴地把这张工作表细细地琢磨了一番,并把各种该做的事都牢牢地记在心上。
福格先生的衣柜里面装满各种服装,简直是应有尽有。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甚至每一件背心,都依次排列标上一个号码。这些号码同样又写在取用和收藏衣物的登记簿上。随着季节的更替,登记簿上还注明哪天该轮到穿哪一套衣服,就连穿什么鞋子,也同样有一套严格的规定。
总之,在那位大名鼎鼎、放荡不羁的西锐登住在这里的时期,赛微乐街的这所房子,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而如今住在这里会有轻松愉快的感觉,陈设也非常优雅舒适。这儿没有书房,甚至连书也没有一本,这些对福格先生来说没有必要,因为在俱乐部里他可随意阅览里面的两个图书馆——一个是文艺书籍图书馆,另一个是法律和政治书籍图书馆。在他卧室里面,有个不大不小制造得非常坚固的保险柜,既能防火,又可防贼。路路通在他的住宅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无论是军事用的,或者是打猎用的,统统没有。这一切都显示着主人喜欢安静的性格。
把这所住宅仔仔细细地察看一番之后,路路通情不自禁地搓着双手,扬扬得意的笑容展露在他宽宽的脸膛上,他兴高采烈地一遍遍说道:“真是太棒了,这份差事像是为我而设的,福格先生跟我准会合得来。他是一个不爱外出走动的人,他做事一板一眼,活像一架机器!妙呀!我是非常乐意为一架机器服务的,现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