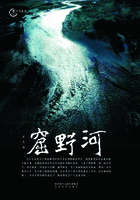于学军赶到饭店时,天已经黑了。门前已经停了七八台出租车。饭店里灯火通明。他疾步地走了进去。那个叫“小日本”的抬头看见了他,微微一笑,同时用眼睛示意正在说话的徐军强有人来。徐军强转过头对站在那里的于学军说:“军子,来,坐我旁边,老谷马上就到。”
话音刚落,门外就响起一阵汽笛声。
“来了,来了,上菜……”
大花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到于学军的背后,随着她的那声大喊,几个小服务员就把菜摆满了桌子。
“哎呀,你可真是稀客,好久没听你做报告了,若不是因为军子,你还不能来呢?”
大花姐今天似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头发盘得高高的,摩丝喷得发型像一顶帽子似的扣在头上。一件黄绿色的连衣裙挂在身上,前后都显得宽宽大大的,耳朵上大圈耳环在灯光下更显得大而亮。
“军子,这就是强子他们的头——老谷大哥。”
还没等徐军强介绍,大花姐抢着先对于学军说。
“久仰你大名,在部队时就如雷贯耳。”
老谷走到于学军的跟前紧握他的双手。
“哪里哪里,你过奖了,现在该我这么说你了。你才是大名贯耳,刚才强子对我说了,向你学习!”
“相互学习吧,来,大家都坐下。”
老谷拉着于学军的手一起坐了下来。
“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是我们‘爱心的士车队’的代表,我们这个车队共有三十台车,因为你开的是徐军强的车,他是我们这个车队的队长,所以你也应是我们‘爱心车队’的一名队员,来,大家举杯欢迎于学军加入我们的组织。”
老谷说完拿起酒杯先跟于学军碰杯,再分别碰其他人。都是性情中人,于学军一饮而尽。他品了一品觉得不是啤酒,便小声对徐军强说:“强子,这不是啤酒,可颜色一样,是什么?”
“是大花姐专门为我们这些开车的人酿的水果茶,即提神又败火。”
徐军强在于学军耳边说道。
“军子,你哪年生的?”
老谷夹了一筷子“手撕大白菜”放到于学军盘里问。
“五七年。”
“哦,那你得管我叫哥,我是五五年的,强子是五六年。来咱哥俩干一杯。”
老谷站起来先干为敬。
“我说,从今天起‘军子’就是咱‘爱心车队’的一员,无论行驶到哪里有麻烦时,我们大家一定要全力相助。”
“没问题,军子是你和强哥的兄弟,也就是我们的大哥。”
轰的一声全桌人都站了起来,把杯子举向于学军。
“谢谢,我谢谢谷哥,也谢谢大家。”
于学军双手抱拳后又敬了个军礼。于学军敬礼的手还没放下,老谷和徐军强也站起来,向于学军回敬个军礼。结果刚刚坐下的人,又都站起来向于学军,敬了个不是标准的军礼。
“军子,你刚干出租车,今后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不顺心的事,别在意,慢慢就会好起来的。不出三个月你一定会是个很出色的好出租司机。我刚开始干时也是一样,就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八年了别提他了……’”
老谷讲起他刚干出租车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刚包车的第二天晚上,接车后就碰了个大活去水师营。乘客下车后又跟上一个返程活去飞机场。我心中挺高兴的,心想去这么远的地方送客,没放空车回来,今天真够幸运的。我把高兴写在了脸上,以至于连乘客都看出来了。
“什么事,乐成这个样子。从我上车你就咧着嘴,到现在也没合上?”
那乘客笑着问。
“我今天碰到幸运之神了。”
我也笑着说。
“谁是幸运之神?”
乘客不解地问。
“你呀,还有刚下车的那位老兄,你们都是我今天的幸运之神。”
听我说完,那个乘客也高兴地笑起来。
“托你的福,我今晚乘飞机去北京谈一桩买卖,看样子一定能成。我是你的幸运之神,那你就是我的幸福之星。”
哈!哈!哈!我们俩都笑了。当车行驶到市郊辛寨子附近时,突然一男子冲到马路上挥动双手示意我停车。我把刹车的闸踩到根底下了,车才慢慢地停下来。车上的那乘客也被这突然的急刹车吓着大叫起来。并冲车窗外面喊:“你脑子有包,打车还有站在马路中间打车吗?”
“司机兄弟,行行好,老婆要生孩子了。”
拦车的人乞求地说。
“快上车吧!”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路旁站着一位孕妇就急忙说。虽然我老婆也生过孩子,可那时我在部队,我老婆生孩子的过程都是我妈陪着。老太太很精明,她怕出事,所以不到日子就把我老婆送去住院了。虽然我没经历过这种事,但我知道这事可马虎不得。拦车的人扶着他媳妇坐在后座上,先上的乘客见此情况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我下车再等一辆,你们先走。”
我加速行驶,当车刚驶到周水子立交桥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孕妇开始呻吟了,而且是一声大过一声,最后简直是声嘶力竭了。
“不好了,我老婆要生了!”
拦车人尖叫道。我不知道怎么办,也不敢回头看。只是打着双闪、加速、再加速向前奔。一路按着喇叭冲到了妇产医院。我刚刚停稳。回头一看婴儿的头已经出来了。我马上摇上了车窗的玻璃。下车就冲进了一个门上写着“手术室”的房间,焦急地向屋里的人喊:
“快来人哪,生了,生了……”
“出去,出去,这里不让男性进来。”
一个身穿绿色套服的大夫,用她那双沾了鲜血的手推我,搡我出去。
“生了?生在哪儿?”
大夫关上了手术室大门,摘下口罩问我。
“哦,生在出租车里,车在门口!”
我说这句话时,不知是急的还是吓的,嘴都哆嗦了。
大夫喊上几个人一起跑到出租车前,一看产妇两腿之间正夹着一个婴儿的头。
“来不及了,马上分娩。”
她当机立断,带着两个助产士挤进了车厢里。这时值班的护士送来了产包,并用白布把出租车四周的玻璃窗围了起来。
一会儿,车厢里传出婴儿“哇哇”的哭声,一个小生命诞生了。后来那个大夫告诉我,如果再晚几分钟,那婴儿就会因母体羊水流尽窒息而死。
正因为这件事,我们爱心车队的全体司机,每人人手一个急救包,我们还参加了红十字会学习班,学过专业的急救知识,为的就是能解决这样的突发事件。
前几天,强子晚间开车就遇到了一个摔得不像样子的醉汉,要不是他有急救包和简单的处理外伤方法,那个人还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老谷,你这样瞧得起兄弟,我绝不给‘爱心车队’丢脸。”
于学军严肃地保证。
另外我告诉你一个窍门,做好事不耽误挣钱,这好心和好利是相辅相成的。
“爱心车队”刚成立时,我在车仪表盘上方,风挡玻璃前,放了一个写着“军人、教师、公安干警、老弱病残者免费”的服务牌,为的是让这些人打车时,感受到我们的温暖。有一天,一位韩国人上了我的车,他是在外国语学院教学的专家,汉语的基础不错,当他看到我的这块服务牌时问我:“外国老师也可免费乘你的车吗?”
“雷锋精神不分国界,我的服务也不分国界。只要你是教师,乘车就可以免费。”
我跟他说。
“我到过很多国家,像你这样的服务还是第一次遇到。”
因为这件事我们俩成了朋友。这位韩国先生任教期满回国后,还给我介绍了许多来中国旅游的韩国朋友。他们在韩国起程前就打来电话让我到机场接,接下来就包我的车,在城市各景点游玩。每天包车价都不低于五百元,还不算中午吃饭钱。最让我高兴的不是收入可观,而是他在韩国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号召首尔的出租车司机向我学习。我们“爱心车队”的事迹都跨出国门了。
“别说了,飞机都要下来了,去拉两趟活再回来接着说。”
大花姐一面推着黄毛和“小日本”离开椅子,一边说。
“军子,咱以后和老谷多见几次面,他有很多的事迹都登在报纸杂志上,你慢慢地看。军子钥匙给我,你在这歇一会儿,我去机场拉两趟活再回来,困了后厨房边有个小炕睡一会儿。”
徐军强拍拍于学军的肩膀说。
“你回家吧,我去那。”
于学军想把早晨看到梦萍的事说出来,但又觉不妥才这样说。
“我干夜班。你刚开始干不懂一些规矩,以后慢慢了解了再干。”
徐军强仍坚持这样。
“你有老婆孩子,干夜班不合适,我没家没牵挂,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再说了不熟悉的事情不接触,就永远学不会,你回去吧!”
于学军想无论怎样也得让强子今晚回家,也许回家后他们就会好的,不回去,只能加剧事态的恶化。
“那好吧,不过你要小心,有事给大花姐打这个座机电话,她就睡在这里。大花姐,军子我就交给你了。”
“知道了,赶快走吧,再不走天亮了。”
大花姐一边说一边推着这些兄弟出了大门。她见一辆辆出租车都闪着大灯上路了,又对徐军强说:“你等会儿走,我开车送你回家,让军子干活挣点钱。”
还没等于学军说“谢”,她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叫:“军子快过去,对面有个打车的人!”
于学军刚发动起车,一辆出租车就蹿到了他的车前。大花姐一看车号是黄毛就骂道:“你个‘大肚皮’,走哪儿都抢食,没看见军子已经开过去了吗?!你和他抢食你也下得眼!”
“大花姐,我不是故意的,今儿车停的远我没看清是军子的车,对不起我先走了军子。”黄毛吃饭是个“大肚皮”,干起出租车也是眼尖手快。老谷常说:黄毛长了一双小偷的眼,天生就是干出租车的料。
黄毛扬长而去,于学军问打车的人:“你去哪儿?”
“去星海三站。”打车人大声说。
“军子把他送到星海三站后,就往前溜溜车,溜到黑石礁电车站,那里晚上可有大活。”大花姐对于学军说。
“好咧!”
军子一脚油车向离弦的箭一样飞去。
按照大花姐的指点,于学军送完这个乘客就奔向黑石礁电车站。这里的确停着不少的出租车,于学军把车子停在最后一辆出租车的后面,打算排队等活。他点上一支烟刚吸了一口,就看见几个剃着光头的人向他走来,他赶紧下车踩了烟问:“打车吗?”
“新手是吧?”
其中一个穿彪马运动衣的人,拍了一下车的后备箱盖问。
于学军觉得很奇怪,我是第一天干出租车,可他怎么知道呢?就在疑惑的时候那个人又说了:“你是干正规的出租车,还用到这里抢活吗?”
于学军抬头看了看停的那些车,再低头看看自己开的车也觉得没什么不同,车体颜色、顶灯……
“都是干出租车的得懂规矩,这个地方是我们哥几个的饭碗,你不能来抢,看你面生肯定是头一回,不然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那个人说完把眼眉朝上扬了扬,意思是看于学军还有什么反应。
“不客气?怎么做是不客气?!”
于学军这个足球场上的前锋,二十几年没说过小话。他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一边用烟敲着烟盒,一边也盯着这些人问。
“不客气就是砸了你的车!叫你走就走,不走等‘菜’呀!看你那木滋滋的样子就欠收拾!”
站在穿彪马运动服旁边的另一个年轻人上来插话。
于学军看着说话的人不觉笑了起来:“要练练是吧?巧了今天我还真就想同你们试试。怎么练,是单挑还是……”
“叫你(方言:傲慢)梗梗!”
那个年轻人从怀里掏出一把砍刀,冲着于学军开的出租车的车顶就劈了过去。刀落车顶就出现一道深沟。于学军心里一阵收缩,心想:这可不是自己的车,明天怎么向徐军强交代?这时其余的几个人,同时都手拿砍刀向于学军逼过来。
“还不走是不是?”
那个砍车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问于学军。
于学军看了看车上一道深沟,再瞅瞅眼前这几个虎视眈眈逼近他的人,他轻蔑地说了句:“什么样的豺狼虎豹我没见过,还怕你们这几个花脸狗熊。”
说完他飞起一脚踢了出去,就犹如当年足球比赛时的临门一脚。那个家伙扔下刀,捂着裤裆跑了。
“兄弟,别动武,都是出来混碗饭吃的……”
那个穿彪马运动服的人说话了,但语气和先头说的不太一样了。
“我们开的都是套牌的出租车,也叫‘黑车’。就是没有营运手续的非法车辆,这样的车,白天不能出来,出来就被抓。所以只有晚上出来干点挣点。你说,你这开正规车再来抢活,我们能不急吗?大哥对不住了……”
“我这是给人家打替班的,开的是车主的车,你把车砸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向车主交代。你负责修车吧!”
“给老板打电话!”
穿彪马运动服的人,一听于学军提出要修车费,就摆出一副要说理的架势。还没张口就见于学军的脸色像猪肝似的,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吓得他忙对那个人喊:“赶快给老板打电话,请示怎么办!”
不一会儿,那个人拿着电话小跑过来说:“来了,来了……”
“老板,有台不懂事的车被兄弟们砸了,对方要修车费,你看……”
“你猪脑袋呀!按既定方针办。”
一个生硬尖刻的女人的声音,传到于学军的耳朵里。
“你几个意思?是赔还是不赔?”
于学军揪住那个穿彪马运动服的后脖领子问。
“大哥,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