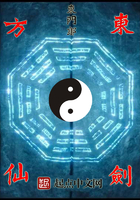一汀狞乱刺眼的血泊后,纤柔的少女长发及腰,她拢袖站在檐下,一袭白衣纤尘不染,便如晴空照雪一般静丽美好。林雨墨表现得非常安分,也做好了引颈就戮的准备,周围却莫名安静下来。
乾化见几名后生目光呆滞,神色多有流连忘返,愈加怒火中烧,蒲扇大的巴掌将崆峒弟子裹个遍,破口骂道:“看!有什么可看的!美人骷髅,穿肠毒药,悟不透这一层,你们永远别想有大造诣。哼,小小年纪就生着一副妖媚惑人的样子,不愧是古墓邪教调教出来的祸害!”
沈岸轻咳一声,贴耳问道:“狄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若有个这般模样的女徒儿,肯否将她赶出山门,任世人屠戮?”
此情此景,难得他还有心思玩笑,狄修扬嘴角抽搐一下:“不敢说,她小小年纪就能做到处事不惊,单这份气度就让人割舍不得。但越是如此越见她心机深沉,很多事不能就此论彼,你我就别操那份闲心了。”
沈岸点头称是,乾化已火冒三丈指着林雨墨道:“你一个瞽人,我也不问你昨夜知晓什么,或许你手底下干净,但到了今时今日,我是非杀你不可,你可有怨言?”
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为众多中原人枯燥的迁徙生涯增添了难以言表的趣味,登台看戏,哪里还有比这等场景更香艳刺激的,活色鲜香的女子,锋光毕露的刀兵,顷刻之间便是血洒五步,瞧热闹的人们期待之心愈浓,端看妖女如何做答。林雨墨犹像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冷眼看待即将发生的一切,漠然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只怕,你不敢下手。”
前后二十余日,她只说了两句话,语声既轻且淡,却是句句求死。
这女人失心疯了,在场每个人都这样想,沈岸与狄修扬亦看出对方眼中的惊讶。这般地有恃无恐,莫非她还有什么后手?乾化又道三个“好”字,不再啰嗦,猝然拔剑刺了出去,冷冽的剑光乍现,似狂舞的火焰一寸寸舔舐羸弱的花朵。
及至此刻,狄修扬二人眼角猛跳,幡然惊悟过来,连忙扑去阻拦,同时叫道:“乾掌门住手!”然而一切都晚了,数丈开外的距离,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把夺命的利刃刺进少女心口,暗自叫苦不迭。
“天地风月,万象柔情。以你之质,奈何无心尘世……”
遥远的虚空中一道真气疾驰而来,卷起满院子落叶红花飒飒飞涌,一径击入剑身,长剑“叮”得一声从中断裂,分作几块碎落在地上。
剑锋已然刺破肌肤,少女胸前的白衣迅速蕴染出星星点点的血色,只消再进半寸,立时一个香消玉殒的下场,纵然大罗金仙在世也断然回天无力。但变故来的太突然,那击落长剑的气劲宛如天外飞来,胜似鬼神莫测之手法,欺过了所有人的眼睛,若对方的目标不为毁剑,那么在场每一个人都决计躲不过去。
一帮江湖侠客顿成惊弓之鸟,连忙拔出兵刃戒备,警戒的目光四下扫视,却未发现任何端倪。乾化鼻子都气歪了,人没杀成,这崆峒派祖传的掌教信剑倒像脆瓷一样给人毁了。他正要开骂,回廊下悠悠步出一道妖冶俊美不似凡人的影子,拊掌赞道:“乾掌门好大的威风,对战苏焾没见你出半分力气,在一个瞎了眼的女人面前逞能耐倒是把好手,佩服佩服。”
乾化又惊又怒,脸色冷然变了变,闷声哼道:“柳相南,你竟然护着这妖女,莫非你也生出所谓怜香惜玉的心思?”
玉面归鸿来得巧合,理所当然被视作帮凶,再说除他之外谁还有那般化气为形的功力。乾化言之凿凿,两眼几乎喷出火来,柳相南却根本不理,神色一动,立时回首遥望,他目力所触,极远处的三层阁楼上,一扇洞开的雕花窗镂后,明光暗影间,竟是落进一双清冷无情的天眸中。
那样一种平静至深的注视,如渊如海一般,越过这人世间的纷纭幻象,看透了前尘往事,看透了年轮流转,似寒月高升九天,静静俯视着三千尘寰下一切的水火欲孽。再没有人比柳相南对这双眼睛留给他的印象更为深刻,二人四目相接,绝顶高手之间无声无息地交锋,柳相南脸上闪过一阵怪异,倒也不去点破,他回眸直视乾化:“蠢人,你眼睛瞎了,看不出她分明是在激你!”
流光潋滟的眸若妖若仙,柔美而邪肆,隐隐勾勒出最具惊魂动魄的绝色,竟迫使乾化不敢与之对视,柳相南抬手捏住少女的下颌,戏谑冷笑起来:“有意思,一路行来竟未发现你是这般的秒人儿,倒叫人刮目相看。”
林雨墨被迫仰起头,一张清美绝伦的面容近眼前。生死之间她神色如常,近乎于绝情的冷漠震惊了所有人,此刻受制于人,她仍无半点抗争之意,双睫轻颤,认命般地闭上了眼睛。
见她这个样子,柳相南不屑一哼,复贴近几分,近乎可以触及少女曼妙的鼻尖。他却无欣赏之心,指端力道加重,几乎要捏碎林雨墨的下巴:“你一心求死,我却偏不遂你意,不妨告诉你,苏焾的命本公子要定了,其余的你想都不要想。”他冷言吩咐道:“这女人暂且有用,谁都不许打她的主意。好生看管,到时两个魔头来了,我自有计较。”说完意味深长瞄了乾化一眼。
崆峒派好歹中原几大名门之一,众目睽睽之下,乾化三番两次遭他奚落,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正欲咬牙发作,被沈岸和狄修扬拉开耳语几句,不知说些什么,他面色一滞,似恍然大悟,这才冷脸罢休。
……
一缕青烟自香炉内冉冉升起,芳香袅袅,浸人心脾生津,浅浅消散在闺阁中。梳妆台前,一个娇艳的女子着中衣坐在凳上优雅打理着半湿的长发,铜镜里一张面容美丽白皙,肌如凝脂,若出水芙蓉一般,清晰可见唇翘鼻挺,眉眼清越,与寻常女子相较少了几分柔弱妩媚,多了些明艳灼人的英姿。
屋内摆有一张香桌,另外几名鱼纹道衣打扮的女子围坐一团莺莺耳语,三言两语讨论什么,不时发出银铃般的脆笑声,一人惊讶道:“不会吧,那一剑真的刺下去了?”
水荇生得脸蛋圆润,人比娇花,闻言翻个白眼:“乾化是什么人,向来说一不二,还能有假?清晨围观的好些人都看着呢,要不是柳相南亲手阻拦,十个妖女加在一起也经不住那一剑,最后不了了之,直把乾老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一女弟子捂嘴娇羞道:“不愧是玉面归鸿,人美性子邪,狂妄亦霸气,谁的面子都不买。”
几人开始笑她,欢声笑语间,又一身量娇弱的少女趴在桌上,神色迷茫感慨,托腮幽幽道:“说来她也是可怜,被关在黑漆漆的柴房,没饭吃,不能沐浴更衣,还没有地方睡觉,换作我早就崩溃了。你们想,她好像没犯什么错,一路上寡言少语的,眼睛还看不到,便被当作囚犯一样任人喝来骂去,更险些给莫名其妙地杀死,挺让人同情的。”
女孩们心思细腻,谈到此处设身处想了想,桌上便没了声音,忽有一人道:“照你这样说,当初我打她两巴掌也是错喽,莫非该去给她赔罪道歉?”
几人吓一跳,抬头见大师姐不知何时梳完了妆画好了眉,正好整以暇地站在一旁,那少女缩缩身子,嗫嚅道:“师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连红玉倒未生气,如一个长姐耐心叮咛幼妹,抚摸她的脑袋道:“阿衡,你这多愁善感的性子始终改不了。她可怜,我们死去的师父和许多同门姐妹就不可怜?妖女至此不肯吐露魔头的下落,单凭这一点她便死有余辜,你明白吗?”
阿衡踌躇着还想再说,桌下被人偷偷踩了一脚,闷闷不乐地“嗯”一声。连红玉拾起榻上的服饰陆续穿戴,道:“各自回房,把换下的衣物拿去后院清洗,这里有水,不是在荒漠中,你们谁都别想给我偷懒。”
穿行幽暗的甬道,两旁经年未被打理的毛竹和野草早已荒芜,缠满蛛网的枝桠横贯小道,几人一边埋怨一边小心翼翼地躲避。步过扇门,入眼一大块旷地,一群青年正于柴房窗前来回推搡,争先恐后地往里瞧,落后者神情愤慨,两眼喷火,嘴里不停骂骂咧咧。
见此情景,连红玉等人怀抱木盆目瞪口呆,随后明白过来。水荇愤然难平,捺不住心底翻涌的怒火,上前斥道:“你们干什么!”
经她一喝,众多青年男子俱是一哆嗦,回头讪讪道:“那个,我们没……”
一切自不必多言,他们羞恼的神情出卖了所思所为,水荇脸色愈黑,当下骂道:“好啊,昆仑派、点仓阁、五老峰,还有崆峒、巨沙帮,都是些名门正派的弟子。哼哼,光天化日之下,一群大男人像马蜂似地围观一个妖女,她长个天仙样还是生了三头六臂,让你们这般痴迷?没见过女人怎的,说出去定让你们身败名裂!”
那群人原本理亏,经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登时不乐意,一名昆仑弟子犟道:“见过怎样,没见过又如何?反正她长得比你好看,我们奉师命看守这院子,又没违规犯戒,你管得着嘛。”
水荇越发冷笑:“我是管不着,你们只消看,不过这地方刚死过人,你可当心点儿,莫要步了他们的后尘才好!”
泥菩萨尚有三分土性,青年们笨嘴拙舌,斗不过她伶牙俐齿,脸上一沉,随即握紧拳头。水荇早看在眼里,“噔”地搁下木盆,环臂道:“怎么,想比划比划?你们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怕还不够看,没瞧见我大师姐在这里,我看谁敢放肆!”
几人愣住,见连红玉不悦地瞟过来,顿时悻悻低下头。栖霞派虽为女流之辈,但这连女侠却出了名的不好惹,不光脾气火辣,嫉恶如仇,武艺也非同一般,据说一套栖霞剑法练至臻境,端的是厉害非凡,连各派长老都要给她几分薄面。
有人垂着脑袋颓丧道:“罢了,小爷我宰相肚里能撑船,不与你们一般计较。”众人陆续走开,先前辩嘴的昆仑弟子嘟囔:“世风日下,狗仗人势……”
“站住!”一声娇喝再起,那弟子一个激灵,暗呼倒霉,便见水荇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微笑,伸出胖嘟嘟的手掌朝他招了招。
“干嘛?”
“钥匙拿来。”
那弟子暗松一口气,挠头道:“什么钥匙?”
水荇翻个白眼:“当然是柴房的钥匙。”
那人立马摇头,脑袋晃得如同拨浪鼓:“这可不行!长老们严令要看管好她,你莫要使坏,出了岔子我们几个都得遭殃。”
水荇又气又好笑:“你个小家气的,我不过把她放出来干活,你们守着就是,又不能长翅膀飞了。”听她这样说,道姑们均是不解,阿衡扯了扯她的衣袖:“水荇,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让她为咱们洗衣裳了,我的大小姐——”水荇拖着长音,继续道:“现成的苦力不用,岂不便宜了她,我说得对不对?”
道姑们嬉笑围上来,纷纷捏她的脸蛋:“还是阿荇聪明,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个好法子。”
水荇更为得意,冲昆仑弟子挑眉:“喂,你磨磨蹭蹭的,到底给是不给?”
那人还在犹豫:“真的只是洗衣裳?”
“废话!”水荇指向木盆:“不然劳烦你?”
也是她胆大,盆里乱七八糟积满了鞋服,皆是女子的贴身衣物,道袍、褶裙、中衣、亵服,盆底甚至露出一角绯色肚兜,青年的脸色立马涨红,胡乱把钥匙丢给她,落荒而逃。几名道姑捧腹大笑,连红玉无奈低叱:“胡闹,成什么样子。”
阿衡仍在迟疑:“这样做好吗,这么多衣裳教她一个人浣洗,要忙到什么时候去?”
水荇懒洋洋道:“随便你喽,你喜欢做好人可以帮她,我们也不拦着。”
阿衡咬咬唇,不再说话。
厚重的门板“吱呀”打开,满室灰尘腾起,一股股霉味扑面袭来,水荇急忙掩鼻退出去,嘴里念咒,暗骂这柴房果然不是人呆的。她挥袖荡开飞尘,立在门外叫道:“喂,小妖女,别拄在里面发呆了,快出来透透气。”
早在之前林雨墨已听到她们的谈话,知道这一次躲不过去,脑袋里翻来覆去思索“洗衣服”。除了字面意思,搜肠刮肚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她从未洗过衣物,但想事情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入神,以至于习惯性忽略周围的动静,如此便让水荇感觉自己被无视了,心道你一个阶下囚还敢摆架子,无名火噌地窜上来,近前指骂道:“臭丫头,真拿自己当个人物,还不给姑奶奶滚出来!”
少女仍像木头一样拄着,水荇更加恨得牙痒痒,只觉她气定神闲的样子分外碍眼,抬手便要抽打,对方在巴掌抬起的一刹转身朝屋外走去,留她一人举着手,打也不是放也不是,分外难堪。
林雨墨不喜欢多事,很多时候她宁愿一个人独处,但麻烦总是接踵而来。索性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姑们连同她言语的力气都省了,只有水荇颐指气使道:“衣服都在这里,你可选择不洗。”
“好。”
“算你识相。”水荇无所谓地笑了笑,给她指点方向:“你左手二十步有一口井,打水上来就可以用,别怪我没提醒你,那井深得很,掉下去十有八九没命,别指望有人救你。”
几人哄笑离开,连红玉走了几步忽然停下,盯住她手里那根笔直的竹杖问:“你叫什么?”
“林雨墨。”
水荇嗤笑:“什么破名字,墨,近墨者黑。黑色的雨,一点意境都没有。”
依稀记得很多年前,周桐说,“你的名字不能再用了,以后就叫雨墨吧。”她记性差,师父很少郑重其事地告诫什么,那是第一次,所以一直记着。
阿衡沉吟一下,自言自语道:“我怎么觉得挺好听。”
连红玉不理她们,又问:“你不姓姜衣?”
林雨墨歪着脑袋对她,似在询她为何这样问。阿衡奇怪道:“师姐,姜衣不是古姓吗,你问这做什么?”
连红玉不再多说,摇头甩掉那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
日头渐中,当空骄阳明媚,一只灰鸟振翅落在破败的墙垣上,林雨墨叹了口气,端起木盆朝井边徐徐走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她无畏生死,但也不愿多生是非,浣洗一些衣物还好说,若是不从,刁蛮的栖霞弟子保不准使出什么更阴损的招数。
指尖顺着生满青苔的井沿摸过去,她触到一根粗长的麻绳,一只滑腻腻的大水桶悬空吊在井口,一个铁轱辘,上面缀有弧状木质把手,还有许多横七竖八的轨杆,不知做什么用的,林雨墨便愣住了。
远处长廊上,两个女子凭栏眺望,水荇原打算看场好戏,不想少女半晌没有动作,她实在看不下去,咕哝道:“那蠢女人,她发什么呆?”
阿衡揣测:“她好像不会打水。”
水荇感觉智商被侮辱了,当即撇了撇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现成的东西都不会用,真当自己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家小姐了,这般没脑子,活该给人捉住。”她甚觉无趣,转身走回房间。
阿衡暗暗咬唇,想了又想,沿着木梯往楼下跑去。一路来到后院,她心里扑通打鼓,难免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远远见林雨墨仍在发呆,又不禁多打量几眼。
她着一袭素净的白衣,衣上没有绣纹,周身也不见任何金玉坠饰,只在发上随意绾了一支浅碧色的木兰花簪。她的样子很恬静,半垂的眼睑一眨不眨,像个没有生机的瓷娃娃,不知习惯还是怎的,她总喜欢把手拢进宽大的衣袖里,阳光落在那白衣上,明晃晃的有些刺眼。
她有着羡煞天下女子的容颜,螓首蛾眉,玉致冰洁,胜似古画里走出的佳人,比师姐还漂亮许多,脸色却格外苍白,阿衡想或许是古墓里多年不见天日的缘故。她的气质很特别,文静、乖顺、少言,逆来顺受,沉静如水,看着温柔娴静,无形中又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像连骨子里都透着冷清,谁都不肯搭理。
阿衡不解,该是怎样的经历让一个人养成了这种性格,漠视身边的一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连自己的生死都置若罔闻。那一刻天高云远,日朗星疏,阿衡恍惚觉得世上只她一人,长空碧洗,风月如梭,她遗世独立,又仿佛不该属于这个世间……
阿衡被自己荒唐的想法激出一身冷汗,捶着脑袋不敢再胡思乱想。
生锈的铁轱辘旋转起来,发出磨牙一般尖锐刺耳的噪音,木桶打到水面,在井里溅起巨大的水花,“噗通”一声震响,林雨墨好像被吓一跳,轻轻拧眉对着那人。阿衡赧然笑了笑,随即想到她看不见,腼腆地说道:“那个,我看你一直站在这里,就过来帮帮你。你别害怕,我没有恶意的。”
林雨墨没理人,阿衡也不介意,开始吃力地摇起把手,木桶刚抬出水面又砸下去,如此来回几遍,她终于撑不住,试着问道:“你能不能帮帮我?”
林雨墨犹豫一下,撸起袖子偎过去,阿衡看那双雪白娇嫩的小臂暗生羡慕,拉起她的手放在摇柄上,又见少女脸色不太好看,直觉到她不喜与人接触:“我们两个一起用力,试着把它拉上来,你不反对,我就开始了?”
林雨墨手握摇柄,许久才低应一声,阿衡便莫名有些雀跃,两人开始摇动把手。
满载的水桶一点点提上来,又一次次掉进井里,二人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没拗过一只木桶,最成功的一次,那桶距离井口不过尺许,然后重重跌落下去。阿衡手臂酸痛难忍,低呼道:“不行,我撑不住了。”她心疼揉搓着手指,见林雨墨几乎苦大仇深地蹙着眉头,不禁问道:“你在想什么?”
“会不会……少打一点?”
“……”阿衡欲哭无泪:“你为何不早些提醒我?”
林雨墨有些讶然:“你没想到?我以为行不通的。”
“我的天,咱们俩是在比蠢吗?”阿衡扶额。
阿衡是个细心的女子,一点点教她撒放皂角,捶打衣物。林雨墨洗得不快却很殷勤,阿衡歇了数次,她倒像是和自己较劲一样,始终不知疲倦地劳作。二人自晌午忙到傍晚,阿衡把衣物折叠整齐,擦了擦额角的汗水,终于露出轻松的笑容,她欲言又止,正要想法子搭话,对方却一声不吭转身走进柴房。
阿衡无奈,怎会有这般不近人情的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