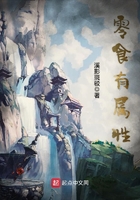四境之内,梁人风雅,青平镇虽处偏远,仍见百姓尚美之风。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男子玉佩叮响,锦衣添彩,举手投足儒雅有致,女子多梳堕马髻,青丝半挽,腰若素约,华丽的绫罗勾勒出婀娜多娇的身段,堪引一众目光。
驱车徐徐驶进城心主道,红墙上茂盛的樱花枝头洁白若雪,沿路多见马队绵长的塞外商贾,两面商铺门庭大开,糕点、首饰、字画、胭脂、茶叶、酒水、丝绸、金银器皿……应有尽有。
转过两道巷口,车马停在一家别致幽雅的客栈前,门旁一位妇人翘首等候多时,慌慌忙迎上去,招呼一声:“谢公子。”不由分说便往车厢内打量,正对上林雨墨温存浅笑的容颜:“莫娘。”
分离不过一夜,经历过生死关头,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莫娘一刹那百感交集,拭了拭眼角:“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多谢公子照料,雨墨眼睛不便,有劳你费心了。”
谢鸢和声道:“在下义不容辞。”
一番离奇的灾厄幸好有惊无险,莫娘无比欣慰,把林雨墨搀下车,硕歆喜滋滋托着鱼篓邀功,不料遭莫娘呵斥:“死丫头,一大早跑得不见人影,还以为你给山匪掳了去!”
硕歆厚脸皮惯了,笑嘻嘻道:“莫娘,我和小姐都不见了,你害怕没有?”
“还敢贫嘴!”莫娘作势要打:“你说我怕不怕?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你又是莽莽撞撞的性子,不加约束些,天都能给你捅个窟窿……”
硕歆掏掏耳朵:“得,你那些话都留着吧,唠叨一夜,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没趣,我去找墨白哥哥玩儿。”
她逃也似地跑开,莫娘苦笑:“这丫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早晚吃个大亏。”
有客栈小厮牵走马匹,几人陆续走进大厅,迎面堂梯上施施然迈下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见其轩昂挺拔如新月秋竹,卓雅之躯若璞玉琢就,几可揽尽光华,满室生辉。硕歆凑上去道:“墨白哥哥,快看我抓的鱼肥不肥,等下你烤给我吃。”
少年摸摸鼻子,想到昨晚带回来的獐子腿,面上七分赞许、两分羞赧,还有一分无奈,只点了点头。
硕歆拉过他介绍:“小姐,谢鸢哥哥,他就是墨白,是他救了我们,不然我和莫娘就见不到你们了。”
莫娘道:“昨晚情况危急,幸亏有这位墨白公子仗义相助。”
回想起昨日那凌空一剑宛如天外飞来,于险厄关头洞穿匪首的胸膛,莫娘到此时仍感惊佩。不光武艺超群,这小后生临敌时的冷静果敢连她也自叹不如,以势如破竹之姿击溃百余名恶匪,见血封喉的手法已堪臻境,更难得其人恭谦有礼,含而不露,果然是一等一的少年英才。
林雨墨欠身施礼,语态平静端祥:“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墨白暗自一个激灵,忙去扶她:“姑娘不必客气,此乃我分内之事,何敢当此。”
林雨墨没有多言,莫娘和硕歆满头雾水:“分内之事?”
熟料墨白朝谢鸢兜头揖道:“公子。”
“……”莫娘二人面面相觑,突然摸不着东西南北:“谢公子……你们认识?”
少年这一礼揖得太过突兀,莫娘压根不曾想过他们会有瓜葛。毕竟谢鸢、墨白皆是途中不期而遇,这二人若相识未免过于巧合。墨白问过安,说道:“夫人有所不知,我家三公子外出游历,每月皆有书信同府中往来。因家中老爷、夫人年岁渐长,思心愈切,特命我来寻公子回府一聚。”
莫娘心有疑窦,这对主仆多年不见,初次相逢未免太过于平静。但总归受人家大恩,不好当面质询,试探道:“这么说你也是谢族之人?莫非得谢公子授意,故而对我们施以援手?”
“晚辈此前不曾与公子相逢。”墨白有点发虚,若是认下便解释不通林雨墨何以整夜未归,他不动声色打量一眼,见林雨墨似乎没打算戳穿,续道:“有缘救下夫人二位本是误打误撞,晚辈曾与公子信中商定于栈阳道附近碰面,来时得知山里有大批马匪,恐公子有失,所以……”
硕歆娇笑打断他:“然后你去寻他,正好碰上我们?”
“不错。”
他这样说倒也过得去,莫娘道:“那你说分内之事……”
墨白见公子只含笑看戏,并不打算帮腔,硬着头皮道:“公子与三位一同进来,我以为你们结伴而行。夫人护我家公子周全,晚辈投桃报李本是应当。”
这般解释已是勉强,少年的脸色开始不自然,莫娘欲言又止,硕歆道:“好啦,莫娘,人家救了我们,你不要老是问东问西的。我都饿了,先用过饭再说嘛。”
略点几样客栈的拿手小菜,四人依次落座,墨白很自觉地杵在谢鸢身后,这举动让莫娘多少有些为难,谢鸢看在眼里,随即吩咐道:“你也坐吧,不必拘礼。”
一件寻常小事让人看出闻名天下的谢族门风严而不迂,硕歆抖抖鱼篓,委屈兮兮:“我的鱼怎么办?”
莫娘道:“馋嘴丫头,就知道吃,我让厨房给你烧了如何?”
硕歆不满,瘪嘴不吭声,墨白道:“其实,烤的话也挺快……”
莫娘笑道:“别惯她这毛病,哪有一再麻烦公子的道理。”
墨白挠挠头:“夫人还是别叫我公子了,晚辈早年跟随三公子身边伴读,你唤我墨白就好。”
伴读书童?武功居然这么高?莫娘感觉脑袋不够用,大门大户出来的果然不同凡响,硕歆甜甜道:“墨白哥哥,你好呆哦,你的剑法这么高明,跟谁学来的?”
“我自幼习武,公子离家后,又拜入玺阳宫潜心修习了几年。”
莫娘道:“玺阳教派以剑术著称,算得上中原数一数二的名门。”
“夫人听说过玺阳宫?”
莫娘点头笑道:“略有耳闻。”
菜品送上桌,跑堂小厮殷勤询问:“客官可需要酒水?小店有窖藏的女儿红、竹叶青、桃花酿,还有招牌特色仙人醉,入口绵香醇厚,回味无穷。”
谢鸢淡淡道:“不必了,你下去吧。”
莫娘招呼几人动筷,林雨墨于膳食向来不挑,吃的也甚少,莫娘和硕歆逐次往她碗里添菜,墨白瞟上几眼,看得莫名其妙,眸底不时流露出古怪。他的莫名其妙来源于林雨墨不去拆穿那些谎话,莫娘很自然误会了,与他解释:“小姐眼睛不好,打小落下的病根。”
墨白收回目光:“抱歉,晚辈失礼了。”
不多时,客栈门前聚拢了三五衣着光鲜亮丽的年轻女子,端看房中两名男子新奇的面孔。但见一人温文尔雅、清贵难言,一人唇红齿白、俊朗非凡。不同的气质却同样超凡脱俗,人中麟凤,少女们目色含羞,以帕掩唇娇声笑语不断,交头接耳相互推搡,大有壮胆、怂恿之意。
硕歆正低头扒饭,挑起莹亮的眸子来回打转,她终于忍不住,咬箸笑道:“这下可好,头一回领略掷果盈车、看杀卫玠的情形。谢鸢哥哥,你们俩千万别去街上溜达,免得祸害一帮怀春少女。”
莫娘啼笑皆非:“臭丫头胡说什么,不成体统。”
谢鸢笑笑不语,墨白沉吟片刻,抽出篓内一根竹筷“哧”地甩出去,竹筷飞若流光,携带疾劲的风头掠过一名女子鼻尖,激起一团团惊呼,瞬间钉入实木造就的门框,只外露三寸嵌在上面。
女子们受此惊吓一哄而散,莫娘、硕歆:“……”
这少年,似乎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温顺。
临近晌午,客栈里接踵踏进一些南来北往的行脚客,哄笑声稀稀落落,热闹而响亮,林雨墨简单进了两口稀粥,道:“我先失陪。”
她起身要走,猝不及防头脑一阵强烈的眩晕,恍惚间竟失去意识,一个趔趄生生朝后倒去,幸得谢鸢眼疾手快扶住:“姑娘。”
莫娘与硕歆叫道:“小姐!”
林雨墨稳了稳神,推开谢鸢道:“无事。”
硕歆将她送回房间,点上紫铜香炉内的檀香,随后抵膝坐在林雨墨身旁,一双人前清亮的眼眸转为盈盈娇态,关怀道:“小姐,你的脸色好白,哪里不舒服吗?”
“我没事。”
硕歆咬咬唇:“小姐,你困吗?我扶你躺下休息?”
林雨墨低眸摇头。
硕歆默看眼前恬静唯美的玉容,忽然感觉所有的话语都是多余,亦或是很久以来,硕歆早就习惯了她的沉默,以致再也找不到可以交谈的话题。林雨墨不适合闲聊,不适合谈心,或许她会以极好的耐性安静含笑地倾听,但笑容里总带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牵强,只因那份清深入骨的孤独早已渗进了血脉。
硕歆明白,她的小姐与所有人都不同。相处之道在于包容而非挑剔,不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套用在别人身上。她有她的性格,有她的苦楚,有她不为人知的经历,所以硕歆从未怪过她。
她的小姐,并非凉薄冷漠,只是擅长独处、不喜欢与人交流而已。至少在硕歆眼中,小姐是这世上待她最好的人。然而相处久了,常年面对一个缄默少言的人,无趣难免变成失落,硕歆低落道:“小姐,我先出去了。”
“嗯。”
硕歆关上房门,长廊玄关处一个少年正抱剑俯视着楼下:“墨白哥哥,他们人呢?”
墨白道:“公子回房了,夫人外出寻找郎中为林姑娘诊治。”
……
行走在人潮川流的大街上,莫娘仍在盘算谢鸢、墨白之间是否有猫腻,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无法推测,但为小姐着想,有些东西她不得不多做揣摩。初遇谢鸢时,林雨墨刚刚逃出中原人的魔爪,继而又遭御虎堂雷霆绞杀,莫娘本打定主意与小姐一同赴死,不过在碰到这个年轻书生之后,一切境地却突然有所改善。
如狼似虎的中原剑客没有追上来,恶名昭著的西夏御虎堂半点踪影不见,连预想中诸方蠢蠢欲动的隐暗势力也消声匿迹,一行人竟然就这样平平静静度过半个多月。直到与栈阳道一群马匪交锋,更巧之又巧的被一个少年英雄途经救下,而那少年又是谢鸢的书童……
世上没有这么多巧合,无巧不成书一贯乃人为造就。
尤其是谢鸳,莫娘总觉他身上有种莫名的气势,说不上来却真实存在,存在于他清越淡然的眉宇间,存在他温和浅笑的薄唇中,那样一种遇事超然闲定的姿态,时刻透有一股自信,仿佛能感染身边所有人。但若想深入探究,他又像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深邃而不可测,使一切窥探消弭于无形。便是漆华山里两位主上的心思也不曾这般无迹可寻,莫娘深感挫败。
她不是没想过与林雨墨相商,小姐凡事藏于心底,即便猜出什么也实难吐露出来。莫娘想不通索性搁下思绪,对方能在险恶之境救自己于危难,显然不存恶意,何况这谢鸢一向让人琢磨不透。
街道两侧画轩茶楼林立,琳琅满目的摊铺前几个姑娘正兴致勃勃地挑选绣品,莫娘拦下一位迎面走来的青年:“敢问小哥,附近可有医馆?”
青年看了看她:“听夫人口音是外地来的吧,身边有人生病了?”
“是,受了点伤。”
青年笑道:“那你可算来着了,沿这条街往前走,有一座四方六角的凉亭,亭子里有位神医仙子正在义诊,不单医术高超,而且分文银财不取。”
莫娘道声谢,加快步伐往前赶去。不久,果然看到一方碧瓦飞甍的凉亭,亭子四周被围得水泄不通,中间一道长龙般的队伍蜿蜒十多米,不时有百姓簇拥排上去。自一侧远观,亭内摆有红木书案一张,细藤靠椅一条,旗竖的条幅两面各书:悬壶济世,妙手回春,颇具江湖游医风范。
亭上两个妙龄女子一坐一立,一着杏黄纱衣,一穿浅绿襦裙,皆是肤白貌美,秀眸盈笑,无怪能吸引一帮看热闹的人群。莫娘心里泛嘀咕,这么年轻的丫头,当真会有一手好医术?她倒不着急上前,粗略打看绵延拖沓的队伍,见问诊的百姓穿着光鲜,一个个脸色红润有光,绝非想象中的面黄肌瘦、苟延残喘,更无一人像染病,顿时哭笑不得。
黄衣女子诊脉断症极快,纤纤玉指轻执狼毫,三言两语便写完一张药方。直至人群散尽,她略显疲惫地揉了揉玉腕,身侧的绿衣少女抱怨道:“呈姑娘,你这义诊一开,瞧瞧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个顶个的绫罗绸缎,富态流油,一个病患都没有。”
黄衣女子掩唇笑了笑,轻柔甜美的嗓音若珠玉落盘、花间微雨,吟吟说道:“天下五国四境,梁人占据南境最肥美的草原土地,人家有钱,你还能管的了别人穿什么不成?”
“有钱又怎样?我看不惯他们爱贪小便宜。”
“青平镇的百姓富裕,真正染病的岂会等我们来治疗?他们不过图个安心罢了。”
“还不是看你医术高明!”绿衣少女颇为埋怨:“堂堂药王谷的嫡传弟子居然沦落到抛头露面,当街看诊,公子这样做到底有何深意?”
女子秀眉微沉,轻叱道:“莫要多舌,公子吩咐的事岂容你来置喙,这场戏务必陪我好好演下去。”
绿衣少女讪讪不再搭话,这时街面上匆匆走来一位留有八字胡的儒衫老者,二话不说,打袖口掏出两块金锭顿在桌子,拱手道:“多谢姑娘圣手回春,鄙庄主终日哮疾缠身,多年来遍请方圆几百里内的名医不见疗效,昨日幸得姑娘赐下良方,老爷服药后,今早起来便感觉呼吸顺畅了许多,姑娘真乃扁鹊当世、华佗再生。一点心意不成礼数,请姑娘收下,以全鄙庄上下感念之心。”
黄衣女子正要婉拒,身旁鬼灵精怪的少女抓起金锭对敲两下,怡然笑道:“药之妙用在于对症,寻常庸医对药性的理解岂可与我家姑娘相提并论。还有,扁鹊、华佗皆是苍颜鹤发的老宿,拿他们作比,不是平白把一个韶华佳人给比老了?再者说,就算他们真的来了,也未必能及我家姑娘的医术。”
一段话若竹筒倒豆,说得极为利索,老者没想这丫头如此刁蛮,暗地抹了把冷汗,悻悻道:“是小可言语不周,冒昧之处请两位姑娘见谅。”
呈珠啼笑皆非,拿过金子道:“老先生切莫理她,小女子自幼习医,多见民间疾苦,能凭一手医术为百姓略尽绵力也算得偿平生夙愿,区区一张药方哪里值百金,老先生请收回吧。”
还是这个女子谦淑有礼,老者暗暗赞赏:“姑娘仁医善心,小可实为钦佩,但行走江湖不可全凭一颗赤诚之心,路上吃穿用度总得需要钱财,哪样也缺不了。”
呈珠笑笑摇头:“老先生看我可像穷苦之人?”
老者闻言审视起来,见她容貌清丽,气质娴淑,言谈举止端庄得体,非是出身书香门第便是贵胄世家的女子。再观其穿戴,发上珠钗乃血玉精雕而成,耳下坠饰由翡翠细琢而就,不显眼的纱衣同样是难得一见的雪岭蚕丝所织,当真非富即贵,老者心底了然,由心钦叹道:“小可眼拙,以粗鄙之物污损姑娘的眼睛,惭愧惭愧。”
呈珠温言道:“老先生一片好意,小女子心领了,这便请回吧。”
儒衫老者离开后,妙染啧啧笑道:“好个两手不沾铜锈气的杏林医仙,送到手边的金子都能推回去,老头活了一辈子怕还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吧。”
她正自取笑,呈珠秀眸轻轻一耷,低声道:“快闭嘴,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