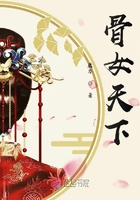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白雪飞苦笑数声:是呵,帝国皇室以天为姓,他们就是天,就是独断乾纲,掌生握死的天。
午饭是萝卜,豆子,腊肉和冷馒头,还有半碗几乎不见米粒的稀饭。香拂先生嚷道:“喂喂喂,雨老头,怎么天天都是萝卜豆子。”雨禅真在车中回道:“香拂先生,你有幸和白侯爷同队而囚,才能吃上这萝卜豆子,若是单独而行,不过是窝头凉水而已。”
香拂先生撇撇嘴骂道:“我刚才明明看见你的侍卫给你端了肥鸡烧鹅!雨老头,你这么大年纪了,吃的如此油腻,小心油脂积于血脉,哪一天忽然就嗝屁了。快把你的肥鸡烧鹅端来和我的换换,我的清淡爽口,正适合你这种老年人。”
雨禅真默不作声,想来是懒得理他。白少棠夹了一片萝卜送入口中,糟糠难咽,也不住抱怨道:“这萝卜怎么一日比一日难吃。”
白语棠将自己碗中的腊肉挑出,从囚车内递了出来,一旁的禁卫接过,递到了白少棠的囚车中,似是已成习惯。白少棠知道姐姐生来不吃荤腥,但日日白菜萝卜豆子的,也不禁担心她是否吃得消,于是叫道:“姐姐,你身体如何?”
白语棠道:“甚好。你不必挂念我。”????
用完午饭,队伍休整出发,又走了两个多时辰,雨禅真命传令兵道:“前方不远,乃是澶渊津铁索浮桥,请各位打乱脚步,准备过河。过河后在”
大日川是帝国第二大河,仅次于江水,也是孕育大陆文明的母亲河。澶渊津是大日川下游唯一可以渡河的地方。白少棠自小便对大日川充满了向往,听见即将要渡河的消息,不由得坐直了身体,倚在囚车边,将缦布拨开,向外看去。
只见官道两侧,黄沙漫漫,草木萧索,极目远眺,不着边际。夕阳余晖之下,瑟瑟西风,扑面而来,风中夹杂着河水的潮湿和清凉之气。白少棠深吸一口气,徙囚以来多日的烦闷,略有纾解。
越往北走,离河越近,黄沙越多,而草木越稀。白少棠低头往下看,官道早已到了尽头,而车下的沙子细细密密,在车轮的碾压下,留下一道道的辙印,沙土上有夏天涨水时留下的冲刷痕迹,波纹曲折,如同巨鱼的鱼鳞。再往前,黄沙开始变得湿泞难行,一簇一簇的槐叶满江红匍匐在地上,围成一个个的小圆圈,像是这沙土开出的绿色花朵一般。成丛的芦苇,叶子还残留着绿意,只是随风摇曳的芦花却已经白尽。
白少棠远远看见河水,在夕阳的照耀下,如同一条洒满金色和红色的绸带,似是从西方天际垂下,缓缓飘来,又消失在东方的天地交接处。粼粼的波光,映着西天的云霞,是真正的长河落日圆,水天共一色,这些年来读过的许多诗书,忽然在此时,豁然开朗了起来。
感觉队伍的行程缓慢了下来,雨禅真在车中冷哼道:“不是已预先告知本地官员,要在河边铺设碎石路吗?怎么如此怠惰?”掀开车窗向外张望,只见前方不远处确有碎石所铺的道路,囚车和自己的车驾前行,不至于再因为河沙湿软而行动缓慢。
澶渊津是大日川下游最大的渡口,近来入冬河水枯竭,河面变窄,铁索浮桥得以通行,南来北往的客商行人众多。不过因为雨禅真的到来,地方官府已经提前一天封禁浮桥,等待雨禅真与囚队通过。
雨禅真命令地方官员不得迎来送往,所以空无一人的大日川边,除了如画的美景,却不免因为了无人烟而显得落寞凄凉。
听见前车吱吱呀呀的声音,白少棠就知道车队已经上了铁索浮桥。白少棠梗着脖子往外看,看到两头大铁牛立在水岸边上,高约七尺,宽约五尺,长丈余,伏卧于铁山之上。铁牛旁边,则各铸有一位高鼻深目,高丈许的铁人。牛尾上铸有横轴,长约八尺,横轴上栓连着铁质桥索,桥面以极厚的木板铺成。白少棠在典籍中曾见过,言道大日川铁索浮桥的镇河铁牛,重逾数十万斤。囚车虽重,但是在这国之神器所造的浮桥上,却如履平地。
白少棠的囚车走上浮桥时,白雪飞的囚车已经到了对岸。囚车稳稳前行,白少棠趴在车内,掀开缦布一角,正面向西边欣赏长河落日的美景,忽听囚车东侧的侍卫惊呼声此起彼伏,口中嚷着:“龙吸水了!快看快看。”
白少棠连忙站起,双手举起东侧的缦布,看到河中情景,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只见东侧远处的河水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向半空,形成一道巨大的水柱,在半空中来回飘摇。
只听雨禅真沉声喝到:“加速前进!”队伍行进速度果然加快了。却见那道水龙卷却陡然向队伍扑了过来,白少棠眼前一花,雨禅真身影鬼魅似的飘了过来,立在了车前,左手施降妖手印,右手在空中连划,口中急速念着什么咒语,只听他急喝一声:“去!”一道六芒星痕凭空化现,向水柱击去。
六芒星痕击上水柱,水柱果然四散,雨禅真回头看了白少棠一言,哼了一声,说道:“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何来龙吸水之相!全速前进,速过此桥。”
话音刚落,耳畔轰隆一声巨响,眼前蓦然出现一道巨大的水墙,直窜上空,又直直的砸了下来,雨禅真大惊之下,身形一飘,瞬息回到岸上。水墙砸下,白少棠只觉眼前一黑,耳边姐姐和父亲凄厉的惨叫还没听完,就连人带车被卷入了大日川中。
白雪飞和白语棠的囚车此时已过了桥,眼前这一幕让二人心胆俱裂,白语棠见白少棠的囚车被卷入大日川中,瞬间沉没的不见踪影,一声凄惨的“小弟”还未叫完,人就晕了过去。
白雪飞双手抓住缦布,尽力一扯,登时将缦布扯落,他发指眦裂,此时只想跳下河去,营救儿子。不及细想,双掌雄劲一运,十重功力全部打在囚车上,妄想破车而出。然而囚车乃是精铁所制,坚硬无比,双掌击出,非但徒劳无功,劲力反冲,震的胸口痛不可挡,后退两步,一跤坐倒,哇的一声,呕出一大口鲜血,已是受了极重的内伤。
雨禅真面如寒霜,走向白雪飞囚车,阴沉着声音道:“白侯爷请保重身体。”
白雪飞怒目而视,想到儿子落入大日川,定是有死无生,心中悲痛,又哇的一口喷出鲜血。
雨禅真双手笼在袖中,脸色稍缓,说道:“白侯爷这戏,十足逼真。”
白雪飞双眼一闭,满脸哀痛,伤势亦十分沉重,无法做声。此时,河水恢复平静,只余桥上的河水正顺着桥面缝隙缓缓流回河中。押送最后一辆囚车的兵士站在河对岸,看着雨禅真,不知所措。
雨禅真丹田一沉,声音不大,却平稳的传向对岸:“继续前行。”押送香拂先生的囚车和压轴的九卿车驾才又缓缓前行。
“你看,香拂先生对令郎掉入河中,似乎毫不关心呢。”雨禅真缓缓说道,顿了一顿,又问道:“这难道不是贵府事先安排好的吗?”
白雪飞听他如此说,睁开眼睛,艰难道:“雨……雨术师,此话,怎讲?”
雨禅真道:“白侯何必明知故问?河水凭空而起十几丈,再以千钧之力砸落,囚车边的禁卫军,无一幸免。而令郎身处精铁囚车,又有缦布为罩,抵消了一部分水击之力,反而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这就是贵府的盘算。”
白雪飞怒道:“我子在囚车中入河,必然溺毙!飞水十数丈,岂是人力可为?雨术师反诬我预先安排,居心何在?”
雨禅真反而微笑起来,缓缓道:“白侯,水飞十数丈,确非人力可及,可是白侯莫忘了,令郎返祖遗传,身负令祖母之能,能与妖言,人力不能之事,于妖族,却易如反掌。”
白雪飞怒道:“雨术师未免以小人……未免揣度太过了!我等入京,生死尚在未定之天,而大日川水势之凶险难测,天下共知。我何必冒险,让小儿一受水击,二入河川?犬子自幼不识水性,再加上囚车沉重,入水即沉,无所觅处。我以未定之死,换犬子未必之生,雨术师,是我愚笨,还是您的推理太过蠢钝?雨术师,你事事将可能都推于犬子与妖族,未免太可笑了。”
雨禅真沉吟片刻,见白雪飞悲痛愤怒,不是作伪,于是招呼随行军医为白雪飞和白语棠诊视。香拂先生的囚车也已到得此岸,雨禅真转身走向香拂先生囚车,命人掀开缦布,却见香拂先生倚在囚车一角,鼻现微酣,却是睡去了。
雨禅真冷笑道:“呵呵,香拂先生倒是气定神闲,如此状况,还能沉沉入睡。”
香拂先生打了个哈欠,睡眼惺忪,揉揉眼睛,问道:“咦?怎么不走了?雨老头,你站在我车前做什么?”
雨禅真道:“先生及时睡去的?”
香拂子伸了个懒腰道:“那谁知道,你拿个黑布罩住我的囚车,让我分不清白天黑夜的,我就困了睡,睡饱了起,哪知道什么时候。”
雨禅真问道:“故而方才河中发生之事,香拂先生全无所知?”
香拂子茫然四顾道:“河中?何事?”
雨禅真心中自然是一百个不相信,却无可奈何道:“令徒囚车过桥之时,恰遇龙吸水,囚车被卷入大日川中,不见踪影。”
香拂子先是极为惊讶的啊了一声,然后哭丧个脸,哭天抹泪的大叫道:“徒弟哎,我苦命的小徒弟哎,你怎么舍得就这么离为师而去了哎!”表情浮夸,语气浮夸,让人看不出悲伤,反而觉得甚是可笑。
雨禅真微笑道:“香拂先生如此举动,想必白侯爷和老朽一样,放心不少吧。”转身看向白雪飞,白雪飞也十分诧异,不知香拂子此举何意。
香拂子干嚎一阵,忽然住声道:“雨老头,你受命押送朝廷钦犯,我徒弟不行落水,为何不下河救援?到了京城,我一定向陛下告状,告你一个失职之罪。”
雨禅真呵呵一笑道:“香拂先生说笑了。徙囚途中,皇家只配了重甲禁军和寻常杂役,并无一人识得水性,如何下水救援?皇帝陛下明理善察,岂容你砌词诬告老夫?”
香拂子嘟了一下嘴,哼了一声,又装模作样哭徒弟去了。此时军医来报,白语棠气血不足,身体孱弱,受此打击,一时晕厥而已,并无大碍。但白雪飞受自己十重掌劲反击,内伤沉重,加上尚需长途远行,纵使性命无碍,功体却受损严重,恐无法复原。
香拂子一听,嚷道:“雨老头,你这是什么狗屁军医!让我去白侯囚车中诊视,有我南五省第一神医在,保证让白侯恢复如初!”
雨禅真淡淡道:“我只负责让白侯安然进京,功体恢复与否,不在考量。”说完转身回到自己车中,香拂子气的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
徙囚队伍继续前行,只留下四合的暮色,慢慢的暗了宽阔的大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