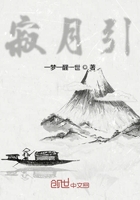夜。
五月的夜实在是闷热而又烦躁,尤其是南方,更是让人感到烦闷。
整个村庄都早已陷入了黑暗,只有间或响起的几声蛙鸣。
虽然闷热,但这的确也算得上是一个普通但却宁静的夜晚。
那些勤劳朴实的庄户人家,早已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劳作,早早的进入了梦乡,等待着明朝日头的升起。享受安详而又宁静的夜晚,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平常但却再美好不过的事情。
但就在这宁静的黑夜中,却有两匹快马在疾驰着。不知道要奔向何方。
“我们要去哪里?”讲话之人是个女子,声音清丽而又婉转,好像春夜柳树枝头上鸣唱的夜莺。
“临安。”答话的却是个男子,声音低沉而又嘶哑,充满了疲倦。
他的确疲倦,不光他疲倦,就连那与他同行的女子也十分疲倦。
因为他们已经疾驰了三天。
“为什么去临安?我们不应该是去找那些杀手报仇?”那女子的声音中充满疑惑。
“仇自然要报,但是,”这男子讲话的声音停顿了一下:“你知道他们在哪里?”
“不知道,你知道吗?”那女子道。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去临安。”
“去做什么?”
“找人。”
“找什么人?”
“胡不归。”
“胡不归是谁?”
“最有可能知道消息的人。”
临安实在是一个繁华而又美丽的城市。
山环秀郭,湖抱丽城,荷香十里,柳韵千株。
在这早早便苏醒的城市里,现在就站着两个人,两个在日出之前刚刚到达的人。
“我一直以为我们蜀中的景色就是人间绝美的了,没想到临安的景色却比蜀地还要美上千倍。”
“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嘛,蜀地也美,临安也美,不过现在我们应该先去做两件事。”
“做什么?”
“吃饭,睡觉。”讲话的男子伸出手,轻轻的拭去身边女子脸上那因奔波和疲倦而沾满的汗珠。
“我们已经赶了这么久的路,当然要先吃大一顿,然后再美美的睡上一觉。”
“可是……”那女子还要说些什么,却已被这男子打断:“我现在饿的几乎能吃下一匹马。”
“小二,点菜。”人还没进门,声音便已经传进了客栈的门。
“好嘞,客官请进。”小二张口应答着,抬头便看见了刚进屋的客人。
一个身着青布长袍的男子,身材中等,长相一般,属于丢到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身旁却跟着个年轻女子,柳眉杏眼,虽算不上倾国倾城,但也是清秀佳人。只可惜左边脸颊却有一道寸许的伤疤。
这男子便是徐三,跟在他身边的自然就是唐婉儿。
“二位吃点什么?小店应有尽有。”小二招呼着。
“什么都有吗?”徐三笑着看着小二。
“那是自然。”小二嘴上应答,眼睛却是盯着徐三旁边的唐婉儿。
这女子虽然算不上人间绝色,但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忍不住想去多看一眼。
“真的什么都有?”徐三对他这种行为暗暗有些生气。
“有,您就是要活人脑子现砸,我们也有。”小二却是信口开河。
“那好,我们就要活人脑子现砸。”徐三一脸认真的看着小二。
“客官说笑了,光天白日之下怎能当真杀人不是。”
“我不光要活人脑子现砸,而且我就要你这颗脑子。”徐三盯着小二的脸,脸上带着值得玩味的笑。
“这……客官……这……”小二的双腿已经在发抖,他本是随口一说,却没想到这客人却在较真。
“呵~徐三你真是。”唐婉儿终于忍不住笑出声:“小二哥,给我们来一份东坡肉,一份西湖醋鱼。两份蛋黄清蟹,再来两碗虾爆鳝面。”
“好……好嘞。”小二擦擦脸上的汗:“好嘞,客官您稍等。”
“等一下,还少了一样。”徐三突然伸手拉住小二。
“客官您还要什么?”小二的手又在发抖,生怕徐三再蹦出一句“活人脑子现砸”。
“还缺了什么?”唐婉儿也有一丝疑惑。
“酒,好酒。”徐三笑着松开小二的手。
“我们为什么要找胡不归?”唐婉儿一边吃菜一边问徐三。
“因为他不光是是张进酒最好的朋友,也是江湖上有名的消息贩子,更是最有可能知道消息的人。”
“张进酒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唐婉儿放下筷子看着徐三。
“是。”徐三回答的很干脆。
“但你却不是他最好的朋友?”
徐三迟疑了一下:“不是。”
“唉,那你可真可怜。”唐婉儿满脸怜惜。
徐三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这种事岂不是很平常,你最在乎的人,最在乎的人却未必是你。而且相比而言,最可怜的人也不是我。”
“那是谁?”
“张进酒。”徐三喝光杯中酒:
“至少我还活着,他却已经死了。”
太阳已经西斜,烧的的西边天空一片橘红,橘红的阳光就那么照下来,染红了临安城里的一切,也把临安城里的房屋行人的影子拉的老长。
徐三和唐婉儿已经在客栈睡了整整一天,散去了连日来长途奔波所积累下的疲倦。
“我们现在去哪里?”唐婉儿伸个懒腰,笑的温柔而又甜蜜,好像一只温柔又甜蜜的小狐狸。
“赌场,临安最大的赌场。”徐三整好自己的衣衫。
“为什么要去赌场?”
“因为我们要去找赌鬼,而且是全临安最大的大赌鬼。”
“若要找最大的赌鬼,当然要到最大的赌场。”
胡不归当然就是那个大赌鬼,当徐三他们到赌场的时候,胡不归正用力的摇着手中的骰盅。
今天他已经连续贏了三十四把,几乎已经快赢光了这桌前的所有赌客。
他用的骰子是价值昂贵的象牙骰,他摇的盅是手工大师用湘妃竹制成的骰盅。
但他的骰子和骰盅却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
如果一个人摇骰子的技术足够好,那他便是拿个破酒碗,也可以摇出他想要的点数。
胡不归的技术便很好,所以他总是贏。
这张赌桌上的赌客已经越来越少,就连看客也变得很少。
因为他们的口袋都已经变空,空的就像饿了三天的肠肚。
莫说是食物,就是粪便也没有一点的肠肚。
所以他们的人也都像被吸光血的羊,疲惫,空虚。
这让胡不归感到很难受。
没有人陪他赌,这对于一个赌鬼来说实在是最痛苦的事情。
而对于一个赌场的老板来说,若是没有客人来赌,那也是最为痛苦的事。
而胡不归既是这家赌场最大的赌鬼,也是这家赌场的老板。
所以他的现在实在是痛苦的厉害。
就在他最为痛苦的时候,便看到了一个身着青袍的男子,带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
有新人进来实在是一件让赌鬼感到开心的事。更何况还有个女子。
女子进赌场,确实是很少见的事。
但这女子不光进来了,还很大方的坐在了赌桌前,坐在那男子的身边,看着这赌桌上的局势。
他们二人就那么看着。也不说话,也不下注。
只看不赌,这让胡不归感到实在是难受,就像被扒光了衣服丢到闹市一样难受。
于是他抬起头来,冷笑着看着坐在对面的两个人:“二位,玩两把?”
徐三笑着看着他“玩可以,不过,只玩一把。”
“只玩一把?”胡不归有一丝愤怒,又有一丝激动。
只玩一把未免太过无聊,但若是一把能让对面两人变成穷光蛋,那也实在是不错。
“一局定输赢。”徐三笑着说。
“好。”胡不归突然大笑,一把推开了桌上的骰子、牌九、马吊牌,显得十分激动。激动到浑身都在颤抖。
“赌多少?”胡不归看着坐在对面的两人,肥胖到油亮的脸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这不是燥热的汗,也不是惊恐的汗,而是激动的汗。
只要有人陪他赌,便足以让他激动。
若是可以让那个人输个精光,那更能让他感到激动。
“一条消息。”徐三淡淡的道。
“你可知我是谁?”
“我知道,胡不归,一到赌场就不归的胡不归。”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胡不归这里的一条消息,值多少钱。”
“我知道。一条消息三千两。”
“那么,钱呢?”胡不归冷笑着盯着徐三,仿佛要从他身上看出些什么。
“我没有,一文都没有。”徐三哈哈一笑:“你这里若是有酒的话,倒是可以先给我一壶。”
“那你拿什么和我赌。”胡不归盯着徐三,就像盯着一只没有肉的羊。
“这个。”徐三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把刀,一把长不足五寸的飞刀。看起来就和江湖上那些使暗器的江湖客用的刀没什么区别。相比之下,甚至显得有些粗糙。
唯一特别的,那便是这把刀的主人。
――张进酒。
花间一壶酒,袖下一飞刀的张进酒。
胡不归盯着徐三手里的刀,盯了足足有一刻:
“赌什么?”胡不归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随便。”徐三接过博头递过的酒壶:“多谢。”
那博头是个同样肥胖的中年人,一双肥胖的手比胡不归还要胖上三分。
“您客气。”那博头上完了酒,默默的退到一边。
“随便的意思,就是都可以?”
“对,牌九,骰子,打褐,马吊,什么都可以。”
“好!”胡不归长长的呼出一口气:
“不过我要和她赌。”胡不归看着坐在徐三旁边的唐婉儿。
“好,赌什么?”唐婉儿回答的很干脆。
“简单点,赌马吊好了,两个人,梯子吊。”
“好,就打马吊。”
“四十张牌,十万贯、万贯、索子、文钱四种花色,各十张牌,以大击小,大小以‘十字’、‘万字’、‘索字’、‘文钱’为序,只有‘文钱’一门是以小管大。姑娘可清楚。”
“清楚,清楚的很。”唐婉儿笑的很悠闲,悠闲的就像刚才的徐三。
“哈哈”,徐三突然笑出了声。
“阁下笑什么?”胡不归很是好奇。
“我若是你,就决不与她赌。”
“为什么?”胡不归昂着头,冷笑着看着徐三。
“因为你已经输了。”徐三笑着说。
“为什么?”在胡不归听来,这是在是一句胡话,只有醉鬼才会说的胡话。
不光胡不归,就连旁边的看客也觉得,这汉子莫不是进门的时候,被房梁撞昏了头。
还没有开赌便夸下海口,若是输了,不知道会死的多难看。
“若是一个人可以把这四十张牌牢牢地记在心中,你岂不是输定了。”
“哼,徐三你真是扫兴。”唐婉儿狠狠地锤了徐三一拳。
“你当真可以记得所有牌?”胡不归一双肥胖的手死死的摁在桌面上。胡不归自问赌技高超,但若要把这四十张牌记得分毫不差却也是不能。
唐婉儿笑着看着胡不归:“你左手边第一张,枝花。”
胡不归伸手揭开那一张牌,的确是一张枝花。
“旁边那一张可不得了。”唐婉儿故作神秘的看着胡不归:“你猜那一张是什么?”
“是什么?”胡不归的汗已经从他的胖脸上淌了下来。
“宋公明,万万贯。”
胡不归揭开那张牌,确实是一张印着宋江图样的“万万贯。”
“我这一张就差一些了。”唐婉儿笑着叹了一口气:“只不过是个武二郎。”
说完随手揭开一张,的确是印着武松的“千万贯”。
“那这一张呢?”胡不归伸手从牌堆中拿起一张。
看着那张牌,唐婉儿笑的像一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张嘛,空汤。”
胡不归手中的那张牌:“铛~”的一声掉到桌上,牌面露出,空空荡荡,确是一张空汤。
“怎么可能。”胡不归瞪着唐婉儿,仿佛见到了什么不可名状的鬼怪一般。
不光唐婉儿,桌边那些还未散去的赌客也都愣在那。
一副牌四十张,每一张的背面都是一模一样的,却又如何能分辨得出。
“这却不能怪我,要怪也是怪你。”唐婉儿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
“寻常人玩的马吊牌,大都是纸质的,而你这副却是用了乌木所制,贵重的很。”
“那便如何?莫不是贵重的牌还会说话不成?”
“会,不光会,而且说的很清楚。”
“你可知这木牌上是有纹路的,树木的纹路。”
“那便如何?”胡不归按在桌上的手更加用力,仿佛要把桌板掰断一般。
“每一棵树的纹路都不一样,甚至于同一棵树不同部位的纹路也是不同的。
“所以这每一张牌的纹路自然也是不同的。”
“既然不同,我自然记得住,分的出。”
虽然没有在赌桌上狠狠的贏胡不归一把,但还是出了个不小的风头,所以唐婉儿现在十分高兴。
“我输了。”胡不归沉着脸站起身来。
一个人若是知道他手里的牌是什么,那他怎么可能能赢。
“老爷,喝杯茶吧。”那博头端着一杯茶接过来。
“好,好。”胡不归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博头手中的茶杯。
刚刚的唐婉儿那一手着实是惊到了他。
“你们想知道什么?”胡不归坐回桌前,打开茶碗上的碗盖。
“我们要的消息自然是极重要的,那么……”徐三看看周围的赌客。
“好,请跟我来。”
胡不归起身引着徐三二人走向赌场后面的院子。却不知为何那博头也跟随着一起到了后院。
赌场本就是开在胡家大院门口的,赌场后面就是胡不归的宅院。
“阁下想知道什么?”
“你是胡不归?”徐三却没头没脑的冒出这么一句。
“是。”
“一入赌场就不归的胡不归?”
“是。”
“你若是胡不归,那他是谁?”徐三盯着胡不归身后的博头。
胡不归紧闭着嘴。
“阁下是如何把我认出来的。”胡不归身后的博头开口了。
他才是真正的胡不归,刚刚的胡不归不过是他的替身。
“因为一个博头,没理由穿的比赌场老板还好。”徐三喝光手中酒壶里的酒:“你刚刚递酒的时候,我刚巧看到了你里面的衣袖。”
“而且他对你的态度未免太好了些。”徐三看着胡不归的替身:“对博头这么恭敬的老板我还从未见过。”
“好眼力,徐三先生既然拿着张进酒的飞刀来,想必所问之事与他有关吧。”
原来胡不归也早已认出了徐三。
“不错,张进酒死了,死在烛影摇红的杀手手中。”
“徐三先生,”胡不归闭着双眼,伸出手揉着眉心:“鄙人奉劝你一句,若是为了这件事,还是不要问的好。”
“为什么?”唐婉儿疑惑的道。
“这对你们没好处,而且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若我偏要问呢?”徐三脸上依旧笑着,背在身后的双手却已经握紧。
“那我也不会告诉你。”
唐婉儿道:“你莫要忘了,这条消息是你输给我的。”
胡不归却耍起了赖皮:“是他输给你,又不是我输给你。”
“那还不是一样,世人只知是胡不归输给我,哪里分的出真假。”
沉默半响之后,胡不归终于开口:“好吧,二位若真想知道,不妨去天香楼一趟。”
唐婉儿眨眨眼:“天香楼是什么地方?”
“妓院,全临安最大的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