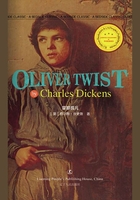我知道,只要再坚持一会儿,跑出这一百多米的黄花草坡,敌人命中率会更低。当我终于瞅见俯冲的地势,一个箭步窜滚下去,从敌人射击的平滑线上消失,已是满脸泥土和黄色花瓣。
躺在软软的草地上,身体由惊恐转入疲惫,额头的汗水沾黏着长发,被阳光蒸干后,仿佛长在肉里似的。自己还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必着急,隔着深深的山涧,敌人短时间内无法追击至此。休息了一会儿,我朝盆谷凹地的方向继续奔跑。天黑之后,我已经远离大船五公里,借着朦胧的月光,打开背在身后的小皮筏,横渡过汩汩奔流的溪涧,开始往对面峰顶攀爬。
假如不清除掉剩余的两个海盗狙击手,我很难向杰森约迪率领的九个海盗展开战斗,否则,只能处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危险境地。
今晚的月亮,很大很圆,挂在黑幕似的夜空,格外突兀。我谨慎的甩动三根钩绳,试探着往山峰顶端靠近。这片山壁比较陡峭,我费了很大周折才爬上峰顶,立刻找了片坑状的草洼,蹲在里面,边休息边吃些鲶肉和淡水,恢复足够的体力。
浓密的树林,在月光的烘托下,显得格外阴森,大片奇形怪状的黑影,像地狱无数沸腾欢呼的妖魔,张牙舞爪左右飘晃。我左手抓着阿卡步枪,右手攥着锋利的朴刀,弓背挺颈朝大船位置跑去。
快到附近时,我立刻放慢前进速度,依靠一簇矮树掩护,观察大船的动静。幽深的山涧下,鬼火点点,形成椭圆型圈状。杰森约迪最终识破了空城计,此时正舞动着手上的烟斗,指挥手下往游艇上搬运武器。
而大船的甲板上,四周插着火把,为这群掠夺军火的海盗照明。“come-on,look-out!”跋扈杂乱的叫嚷声,像乒乓球一样,磕碰着左右岩壁弹跳上来,如地狱泛起的尘嚣,听得人心发毛。
杰森约迪崔赶着手下,尽快把大船上的军火搬码上小艇,他明白自己在免费抢劫军火,知道那些枪多拿一条是一条。好比古代诸侯分封,骑着快马奔跑,一天之内,无论圈起多少土地和人口,都归自己所得。两者都有着因贪婪而产生的焦躁,或许对他们而言,那是种怪异的快感。
我最担心的,是海盗搬运完军火后,会不会把大船炸毁。当然,这由不得我走过去商量,恳请敌人通融,虽然这对彼此来讲最好不过。但我更相信,他们会在我意思表示之前,一枪打死我。
敌人的五艘小艇,甚至加上我停泊在大船尾部的那艘,也不能一次性搬走货仓里的所有军火。甲板上的海盗,或许又损失了一到两名,因为我使用过的小艇,方向盘下同样设置了鱼线雷阵。
剩余的两个狙击手,不知身在何处,就像他们此刻不知道我就在附近一样。打开缠在腰上的钩绳,我试着攀爬下去。
假如找到机会,趁着夜里没狙击视线,我可以偷袭一下甲板上的海盗,干掉几个算几个。
但这样做很冒险,我仔细一想又抽回双腿,不再往山下攀爬,敌人既然点着火把,如此嚣张的搬抢军火,一定不是白给的。万一海盗配备了夜视仪器,可轻易看到一个蓝色轮廓的四肢动物,浑身布满红色热量,正从头顶朝下缓缓攀爬。
他们当然知道这不是猴子,便假装没发现我,心里却偷偷阴笑,等我消耗完大部分体力,快爬到山壁半腰,再一枪把我从岩壁上击落。那我就等于中了人家的计谋,自寻死路。
若放这群家伙运走第一批货物,等他们再回到大船时,海盗数量可就不只眼前残余的这几个,到时更不容易对付。所以,现在必须干扰敌人,拖住他们返航的时间。
此刻,枪火之类的武器,我一律使用不得,这会招致黑暗处的子弹射杀自己。悄悄潜伏到一个可垂直俯瞰大船的位置,借着朦胧的月光,我蹲在地上挪动,睁大了眼睛,寻找足球大小的石头,堆积在峰顶边沿。
五分钟后,大概堆齐了一百多块儿石头。然后,我摘下背上的步枪,拎着朴刀砍些细软的藤枝,扎编成一个草人形状,插在石堆后面。身后十米远的那棵大树,早先埋藏了一箱手雷。我利用鱼线,快速拉扯出一片雷阵。
一切布置完毕,我再次蹲回岩壁,往山涧下瞅了一眼。那些像蚂蚁一样忙碌着搬运的海盗,全然不知大祸临头。我怀抱大石,举头望月,十分钟后,终于有了云遮月的瞬间,我急速抛丢石块儿,仅一分钟,石堆儿便消失在眼前。漆黑幽深的山涧下,不久传来尖锐的惨叫,雷同地狱里的哭声。
石头密集持续的嗖嗖下落,一旦砸中人的头顶和肩膀,破坏力不比炮弹委婉,可以说杀人于无形之中。山涧下的海盗,被雨点般落下的石头捶得抱头鼠窜,死的死,伤的伤,不敢继续搬运军火。
以前,晚上站在甲板上,捕捉溪水里的猎物,我曾抬头仰望过夜空。这会儿,山涧底下那群海盗,根本看不准我的位置,抬头仰望的话,只能瞥见一线天处几颗星斗。而且,这个仰望过程很刺激神经,说不定哪个黑点在眼前一闪,砸个满脸花,或者鼻梁骨凹陷进面部,把眼球挤出来。
时间差不多了,我拾起身后的步枪,越过边缘扯好的一条条鱼线,朝黑乎乎的树林深处猛钻,奔跑到三百米的位置,火速爬上一棵大树,将巴特雷狙击枪管儿对准草人的方向。
狙击镜中,视线模糊得很厉害,黄圆的大月亮,像慢慢眨了一下眼睛,又给山林洒下银辉。T型标线,如飞进阴云里的乌鸦,不能再像白天,很准确的捕捉到目标。
我静静的等待,假如杰森约迪没被乱石砸死,一定气急败坏,调动峰顶的海盗狙击手,让他俩快速赶往这里,清除抛砸大石的敌人。
喉结在脖子里吃力的耸动一下,我感觉自己正如一条伏在树枝上的变色龙,专心致志守候着眼前,一有昆虫掠过,便依靠快速弹出的舌头,打下稍纵即逝的猎物。
那一百多块儿石头,估计也毁坏了部分甲板,若以后夺回大船,我再筏些木头,做木板修补回去。
“唰”一到电光闪起,贴在狙击准镜上的眼睛,瞳孔被刺激得急速放大,与此同时,一颗捕捉生命的子弹,也被我从长长的枪管儿中放出。
插在峰顶石沿的草人,不一会儿工夫,就被隐藏在黑暗中的狙击手击倒。那家伙击中目标后,依靠另一名海盗狙击手的掩护,想悄悄匍匐过去验尸。岂不料,刚跑到距草人五十米的位置,便趟到了鱼线,五颗手雷接连炸响,轰得落叶漫天飘舞。
那片鱼线雷阵,铺设的范围很大,因为不知黑暗中的敌人会从哪个方向潜伏而至,所以弹片伤害到目标的可能很小。但是,雷光闪亮的瞬间,一个端着长长步枪的海盗,浑身如同挂满八爪章鱼似的轮廓,赫然出现在我守候的T型准线上。
“嗖”一颗伺机良久的子弹,正如变色龙的舌头,利用瞬间的洞察,准确朝猎物飞去。那家伙儿意识很强,手雷炸响的瞬间,虽然知道弹片伤及不到自己,但仍有急速卧倒的迹象。他明白,雷光暴露了他黑暗中的身形。
诚如我当初潜入沧鬼的大船,偷窃他们的枪支弹药那般,当时若有一颗手雷在大厅炸响,我怀抱箱子打算溜走的姿态,也会立刻彰显出来,必死无疑。
子弹的速度没给对手任何机会,他刚想前倾,做一个俯冲翻滚的动作,还等做出来,钻进左肋的弹头就令他停止,呆立两秒钟后,重重跪倒在地,脑袋杵进落叶层,永远抬不起来。
“嗖啪”一颗幽灵子弹,猝不及防地还击,打在我遮挡右肩的树干上,撞碎一块儿水分很大的树皮,胡乱飞溅起来的木屑,迸射到我脸颊,热辣辣的疼。
灼热的子弹,在夜晚飞行时,很像萤火虫,加之速度极快,又划出火红的弹道线,十分拉风。那个疯狂的海盗狙击手,顺着这条射杀队友的火线,急速反射过来。整个过程,就像打出去的乒乓球,被对手接住后拍了回来。可想而知,对手的反应能力及下意识多令人悚然。
我几乎是从树上摔下来的,没等起身逃跑,头顶上的树干又连中数枪,断枝残叶之类,纷繁落满肩头。这么变态的狙击手,一定是白天追射我的那个家伙。
这次,我利用奸计,又杀他一个队友,肯定进一步刺激了他满腹的仇恨;如若不然,白天时我都跑进两千米远的黄花草坡了,他为何还不肯放弃,固执地射个没完。一个出色的狙击手,从不靠运气代替瞄准镜,但现在,我却把他逼到这份上。
朝着盆谷凹地的方向,我急速飞跑,这一带地形,早被我印记在大脑,即使现在光线不足,我依然知道,跑那条路速度最快,遭遇阻挡和危险的概率最小。
我没命的奔跑,生怕最后一名海盗狙击手朝我盲狙,虽然击中我的概率很小,但可能性存在。先前摆设的六个牵魂替身,估计这家伙早已识破,在他眼里,我是个很棘手的同行,宛如一只蚊子不时叮咬狮子,兽王自恃强大,却难抓拍到它,对狮子来讲,这也是棘手的问题。
这种棘手,不仅不会让对手敬畏,反而大大刺激他的鄙夷之心。我很了解那些手腕老辣的幽灵狙击手,他们痴迷和同行对战,每杀一名狙击手,就像猎杀了一只豪猪或山鸡,纯属乐趣儿。
但射杀之前,他们绝对不会告诉对手,这是一场老虎和山羊的较量,更准确得说,是屠杀。
刚才丢砸的石头,一是击杀甲板上的海盗,拖住其搬运军火的时间;二是牵引敌人的注意力,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自然会心有余悸,总翻眼珠望峰顶。这样,我就有机可乘,下到山涧底部,偷袭这群眼睛总往上看的盗贼。
跑出两千米,我快速解开钩绳,尽量节省时间朝山涧下攀爬。身后追击的狙击手,又消失在黑暗中,带着愤愤之情,准备下一轮的交锋。
待我攀到滚滚奔腾的溪岸,腕上的手表显示凌晨一点一刻。溪涧水位升高很多,以岸边前踩着奔跑的大理岩石,已被掩盖在两米多深的水下。为了不跌滑进溪水,遭受急流冲走,我只得努力着往山壁高处走,抓着横生的树枝,斜着身子朝大船方向逼近。
眼前黑蒙蒙一片,万一岸上趴着几只大鳄,一脚踩进它们嘴里也有可能。我腰间虽有移动光源,此刻却使用不得。湍急的溪流,哗哗响不停,芦雅和伊凉她们,一定在巨型巢穴里睡着了,或者太牵挂我,失眠了。
我左手攥紧朴刀,只要有什么爬动的东西,敢不友好的朝我奔扑而来,利刃先剁下它大块儿肥肉。然而,当我真看见一条不友好的大体积的活物,从溪水对岸朝我游奔而来时,我却没敢挥刀迎敌。
由于月光混黄,那个只能看清轮廓的活物,仿佛被放大了许多,水流似乎并不阻挡它横穿溪涧的身躯。来不及多想,我急速掏出钩绳,卯足了劲儿抡上高处的大树,猴爬杆儿似的朝上猛窜。
那一刻,我真感觉自己是个毛茸茸的猴子,因为四肢上的寒毛,几乎将贴在肌肤上的袖子和裤管儿全支顶起来。
一口气攀高二十米,才敢回头观察,水中那条拱出巨大脊背的东西,已将头部和前肢扒伏在岸边。我又急又气,若换作平时,管它什么野兽,就算真有白垩纪时代的巨型生物,照样抽出阿卡步枪射它脑袋。可现在,我连手枪都不敢开,生怕刚才那个狙击疯子真得追赶到附近。
“咕咕安,咕咕安……”那个看不清形状的巨大水兽,叫声刚渗进耳朵,就惊得我浑身一哆嗦,差点从蹲趴的树上掉下来。这叫声,像一只失去母亲的幼仔,呼唤着哺乳或陪伴。或许,它真把我当成什么亲人,哀求我靠近它。
宁可枉杀了它,我都不会下去给这畜生安慰,大自然创作的动物,各有各的捕杀技巧,天知道那叫声是不是捕食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