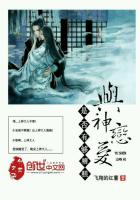还记得七五年那年,赵庆生还生活在一处山区和平原交界处的县城。
那里有一条不大不小的街道,因为是农村进县城的必经之路,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通中心。
虽然破败不堪,但每天早晨都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街道旁有低矮的平房错落的分布着,其中一栋破旧的老院子内一个中年男人正站在院里,看到西屋还关着门,立刻扯着粗嗓门吼道:“霞子,你睡死了吗?还不快起来,这都啥时候了?”
随着喊声,西屋木板门咯吱一声拉开,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姑娘从屋里走出来。
“一个闺女家的,咋这么懒,也不知道早点起来。你还上工不了?”
“知道了。”赵庆霞嘴上应着,心里却不服气,生子不也没起来嘛,父亲真是偏心眼。
她看了一眼仍旧没动静的东屋,撇了撇嘴,转身拿着盆去打水洗脸了。
而外头的动静,赵庆生躺在炕上早听见了。
照理说这个时间他也该起来了,但是今天躺在炕上,一点也不想动弹,脑子里乱作一团,他甚至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还在梦里。
梦里他被困在姐姐的身体里,承受着自己带给姐姐的一切痛苦,要不是自己,姐姐现在已经是重点中学的学生了,要不是自己不务正业,姐姐更不会因为自己欠了人家赌债跟青梅竹马的对象分开,被迫嫁给那个一天就知道打媳妇的老男人。
想到这里,那恐怖的梦又一点点的涌了上来,只是…他看了看周围熟悉的环境,心中不由得庆幸还好是梦。
突然他觉得脖子有些疼,扭过头,看了一眼炕柜上的小镜子,发现自己脖子上居然有一道细小的疤痕。
他还记得梦中姐姐就是用刀割了脖子才死的,突然一股从心底涌出来的疼痛和寒冷让他的意识开始向记忆中的梦境里跌落。
“啊…啊啊!”
他颤抖着身体,张开嘴,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惊叫,就好像胸膛被人用刀劈开了似的。
“叫叫叫,你鬼叫什么呀!”
第一个进来的是姐姐,她一脚踢开东屋门,气哼哼地斥责道。
此时,厨房内,正在吃力地端着一个大瓦盆的李娟,刚抄起水瓢准备做饭,就听见儿子的喊声,立刻把水瓢一扔,转身就进了东屋。
正好听见自己闺女的话,立刻埋怨道:“霞子,你怎么这么说你弟弟,他可能是磕到哪了吧,也不说关心关心,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嘛。”
“哈!他哪里像磕到了,睡得跟猪似的,肯定是做噩梦了。”
霞子指着还坐在炕上发呆的赵庆生冷嘲热讽。
“就是做噩梦了,你也不应该这么说你弟弟!”这时父亲也沉着脸走了进来。
“呵呵!我看呀,他不做亏心事就不会做噩梦。”
“霞子,你少说两句吧,快去盛饭,吃完了好上工。”李娟看自己丈夫的脸都变了,知道他要发作赶紧将闺女推出去,就怕她再说些不中听的话。
“生子,你没事吧?”赵文成看到儿子那张略显苍白的脸,有些担忧的问。
赵庆生此时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本能的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