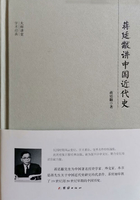在希腊悲剧的阿波罗部分即对话中,所有突至表面让人见到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单纯、透明、美丽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话是希腊人的化身,他的本性在舞蹈中表露无遗,因为在舞蹈里,最强大的力量只是潜在的,却通过灵活敏捷、多姿多彩的动作表现出来。因此,索福克勒斯的英雄的语言以其阿波罗式的确切与明快让我们感到如此意外,致使我们以为看到了他们最内在的本质,并且略微诧异于深入本质的道路竟如此之短。然而,倘若我们撇开英雄浮现到表面清晰可见的性格——这性格不外是投射到黑暗墙壁上的影像,即彻头彻尾的现象——倘若我们深入到投射在这些明亮映象中的神话本身,那么我们就突然体验到与熟知的光学现象相反的现象。当我们试图用肉眼观察太阳,感到目眩而掉过脸时,我们的眼前就会有黑暗的色斑,仿佛是疗治眼睛的药物。反过来,索福克勒斯英雄的明亮的映象,简言之,面具的阿波罗因素,是观察自然的内在奥秘和可怖本性的必然产物,如同治疗受恐怖黑夜伤害的眼睛需要亮斑一样。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认为我们正确理解了“希腊达观”这一严肃而重要的概念。而在现代,我们随处都可见到达观这一概念被误解为平安惬意的现象。
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不幸的俄狄浦斯这个希腊舞台上最悲惨的人物是一位高尚的人。他虽然聪慧过人,却命中注定要犯错受苦,但是由于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最终他对四周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福气四溢的力量,这力量在他去世后仍起作用。这位深沉的诗人想告诉我们,高尚的人不犯过错。任何法律,任何自然秩序,甚至整个道德世界,都会由于他的行为而毁灭,正是这个行为产生了一个更高的神秘影响区,这些影响力在被摧毁的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世界。这就是诗人——倘若他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的话——要告诉我们的东西。作为诗人,他首先给我们看一个结得严严实实的讼案之结,法官一环一环地解开这个结,自己也随之毁灭。这种辩证的解决激起的真正希腊式的快乐如此之大,以致一股欢快之气贯通整个作品,减弱了这个讼案的可怖前提的锋力。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1]剧中,我们又发现了这同一种欢快,不过那是无限神化的欢快。一方面是这位遭受大苦大难的老人,他全然是个受苦人,屈从命运的摆布;另一方面又从神界降下超凡的欢快,并喻示我们,英雄由于采取纯粹被动的态度而达到远远超越他的生命的、最高度的主动性,而他以往的思想和追求却使他只能陷于消极被动。这样,那个在常人看来无法解开的俄狄浦斯故事的死结就慢慢解开了,当我们看到辩证法的这一神圣的对立物时,人间最深沉的欢乐不禁涌上我们的心头。如果这个解释切中诗人的本意,那么我们还可以问,神话的内涵是否已经穷尽?我们看到,诗人的全部见解不外是我们看了一眼深渊后,治疗百病的自然提供给我们的那个光亮的映象。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破了斯芬克司之谜!这种命运的神秘的三重性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个古老的,尤其在波斯流传的民间迷信认为,智慧的巫师只能由乱伦而生。考虑到破谜和娶母的俄狄浦斯,我们马上就可以这样解释这种民间信仰:凡是预见未来而又神秘莫测的力量打破了现在和未来的约束、僵化的个体化法则,甚至自然的真正魔力的地方,必定有巨大的违背自然的事件——比如这里所说的乱伦——已经作为原因先期发生。因为,倘若人们不通过非自然的手段反抗自然,战胜自然,怎么能迫使自然暴露它的奥秘呢?我看到,俄狄浦斯可怕的三重厄运清楚地体现了这个道理。那破解自然——双重变态的斯芬克司——之谜的人必定要破坏神圣的自然秩序,弑父娶母。这个神话似乎要轻轻地告诉我们,智慧,尤其是狄俄尼索斯智慧是违反自然的暴行,谁用知识把自然推入毁灭的深渊,谁就得在自己身上体验自然的瓦解。“智慧之矛调转矛头刺向智者,智慧是对自然的犯罪”,这是神话向我们高喊的可怕语句。但是,希腊诗人却像一束阳光那样,抚摸这个神话的庄严可怕的门农之柱[2],使它突然用索福克勒斯的旋律发出鸣响。
现在,我将照耀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的主动的光荣与被动的光荣作对比。思想家埃斯库罗斯要告诉我们他作为诗人只想通过类似譬喻的形象让我们感悟的东西,青年歌德借用普罗米修斯之口,用一番豪言壮语作了揭示:
我坐在这里造人,
按照我的形象,
一个类似我的族类,
他们像我一样,
受苦,哭泣,
享乐,欢喜,
不把你看在眼里![3]
升华到巨神界的人争得了他的文明,迫使诸神与他结盟。因为他凭借他特有的智慧,把他们的生存和界限操在手里。这首普罗米修斯诗按其基本思想本是对不敬神的赞美,然而诗中最奇妙的东西却是埃斯库罗斯对正义的深深的渴求:一方面是勇敢的“个人”的无限痛苦,另一方面是神的困境,对诸神末日的预感,这两个受苦世界的迫使两者和解,达到形而上统一的力量,所有这一切极其强烈地促使我们想起埃斯库罗斯世界观的核心和要旨,按他的世界观,作为永恒正义的摩伊拉[4]高踞于诸神和人类之上。埃斯库罗斯把奥林匹斯世界放到他的正义天平上,真是勇敢非凡,面对这一点,我们不禁想到,深沉的希腊人在秘密的宗教仪式中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坚定的形而上思想基础,会冲着奥林匹斯发泄他们种种突发的怀疑。。尤其是希腊艺术家,面对这些神灵时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朦胧感觉,正是在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身上,这种感觉得到了象征性的表现。这位艺术巨擘身上有一种坚强的信念,坚信自己能创造人,至少能毁灭奥林匹斯诸神。他以其高度智慧从事这个业绩,当然,他不得不为此而永远受苦,借以赎罪。这位伟大天才的杰出“才能”(为此而永恒受苦的代价算不得什么),艺术家的苦涩的自豪,这就是埃斯库罗斯作品的内容和灵魂;而索福克勒斯在他的俄狄浦斯剧中奏起了圣徒凯旋曲的序曲。然而,即使用埃斯库罗斯对神话的解释也不能测出神话所蕴含的深不可测的恐怖。毋宁说,艺术家对成长感到的快乐,蔑视一切灾难从事艺术创作的欢乐,只是蓝天白云映照在黑暗的悲伤之湖上的明亮倒影罢了。普罗米修斯传说是雅利安各民族共同的原始财产,是他们善于感受忧郁悲惨的东西的天赋的证据。这一神话之于雅利安人,很可能与堕落神话之于闪米特人具有相同的表征意义,两个神话之间有着兄妹般的亲属关系。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前提是天真的人类赋予火以极大的价值,把火看作每一种新兴文化的守护神。但是,人自由地支配火,人得到火不只是靠上苍的馈赠,如点燃一切的闪电,温暖一切的阳光,这在沉思的原始人看来真是一种罪过,是对神圣自然的掠夺。于是,这个原始哲学问题就在人神之间设置了一个令人为难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如同一块巨石,把它横在每种文化的门前。人类所能分享的最宝贵的东西是通过犯罪争取到的,人类不得不为此承受其后果,即忍受被冒犯的上天降给正在兴起的人类的痛苦与苦难之长河。这是个苦涩的思想,它赋予罪恶以尊严,并以此尊严与闪米特的堕落神话相区别。在这堕落神话里,好奇、欺骗、脆弱、色欲,总之,一系列主要是女性的爱好被看作罪恶之源。使这一雅利安观点显得突出的是把这种积极进取的罪孽看作真正普罗米修斯德行的崇高见解。同时,我们由此发现了悲观悲剧的伦理基础,即为人类的不幸辩护,既为人类的过错辩护,又为由此产生的苦难辩护。事物本质中的不幸(深沉的雅利安人无意加以抹杀),世界内心的矛盾,在他面前显现为诸如神灵世界和凡人世界等不同世界的交错混杂。每个世界作为个体都是合理的,但它们与其他世界并列时,却要为自己的个体化受苦。当个人勇敢地融入一般,试图摆脱个体化的引力,想成为整体的世界生灵本身时,他就亲身遇到了隐含在事物中的原始矛盾,也就是说,他亵渎并因而受苦。雅利安人视亵渎为男性,闪米特人视罪孽为女性,正如原始亵渎由男人所犯,原罪为女人所犯。况且男巫合唱队如此唱道:
女人已走千步长,我们无须细较量,
不管女人多卖力,
男人一跃便赶上。[5]
谁理解了普罗米修斯传说的实质,即泰坦般奋发向上的个体必然要亵渎神灵,他同时就必定会感觉到悲观观点的非阿波罗成分。因为阿波罗恰恰在个体之间划出界限,一再提醒他们,这些界限是神圣至极的、要求人们“认识自我”和“适度”的世界法则,以此安抚个人。为了使形式在出现阿波罗倾向时不至变得埃及式的僵硬冷漠,为了在设法画定道道波浪行进的轨道和范围时,不致使整个湖面变成一潭死水,失去活力,狄俄尼索斯的洪流巨浪又不时地冲毁阿波罗意志企图制约希腊精神的所有小小的规矩。那骤然暴涨的狄俄尼索斯洪流背负起众多个体的小小波浪汹涌向前,就像普罗米修斯的兄弟、泰坦巨神阿特拉斯[6]背负着地球一样。要成为肩负所有个人的阿特拉斯,用巨背将所有个人越举越高,越举越远这一强烈渴望是普罗米修斯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的共同点。在这个意义上,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是狄俄尼索斯的面具,而先前提到的埃斯库罗斯对正义的深深追求则表明,就父系而言,他源于阿波罗这位个体化和正义界限之神,源于这位明智者,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的双重性格,他兼有的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本性可用下面一句概念化的话加以表达:“一切存在既公正又不公正,在两种情况下都同样合理。”
这就是你的世界!这就叫世界![7]
注释:
[1]《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索福克勒斯写的悲剧。科罗诺斯位于雅典附近,是俄狄浦斯最后居住和逝世的地方。
[2]门农,特洛亚战争中的英雄。希腊人把埃及阿门科忒佩三世的雕像称为门农。据传,该雕像在第一束阳光照到身上时发出类似人声的哀鸣。
[3]这是歌德《普罗米修斯》中的一节。
[4]摩伊拉,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同时也指神和人的命运、劫数。
[5]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3982~3985行。郭沫若译为:男子不必尽斯文,女人纵快一千步,男子一跃便赶上,女人虽快复何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5页。
[6]阿特拉斯,泰坦伊阿佩托斯和克吕墨涅之子,曾与其他泰坦一起反对宙斯,失败后被罚去顶天。
[7]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409行。郭沫若译为:这便是你的世间!这也算是个世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