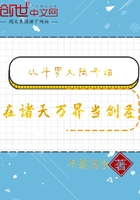慕流云背着手在公主府门口来回走着,不厌其烦地在此地绕了数圈。
看门的守卫们揉了揉有些花的眼,其中一人道:“慕公子走得辛苦,既不愿在府中等着殿下,不如让小人去寻张椅子来让公子做稍许歇息。”
慕流云暂停脚步,冲那个守卫摆摆手,温和地笑道:“你们日日在此守着,比我辛苦百倍,我这才走了几步,何谈辛苦,又怎能麻烦守卫大哥再替我走上一遭,往日不觉在这守门竟是如此劳累,我定要让公主给你们涨涨工钱……”
他还未说完,余光瞥见晏珏骑马而来,顿时眼前一亮,向几人挥挥手便迎上去:“阿珏你可算回来了,我有要事与你商谈。”
两名守卫也紧跟着迎上去,一人牵住马头,另一人恭立在旁侧,待晏珏下了马,两人忙将马牵走。
晏珏行至府门前,早有行完礼的守卫打开门将她迎进去,进府后她才淡淡地看了慕流云一眼:“何事?”
慕流云道:“你已许久不曾来翰院,师父又云游在外,我读史颇有心得,却无一人可共论,因而特来府中寻你。”
晏珏似笑非笑:“读了哪部史?有了什么心得?”
“读的是《余朝正史》,我反复思量其中的那篇《烈帝本纪》,还是觉得余烈帝驱逐尚琴是他的一大败笔。史载‘自尚琴而后,贤臣纷纷致仕隐退,满朝文武尽皆叵测之徒,偌大王宫无一忠恳之辈。及至李家作乱,余名存实亡。’”慕流云抖抖广袖,以一句话结尾,“可见正是余烈帝亲倪远贤,又因尚琴一事令其余贤臣寒心避世,才导致烈帝晚年被奸贼害死和大余之亡。”
晏珏停下步子看着他,眸中光影明灭不定,许久,她叹息道:“我无兄弟,你是我师兄,我视你为亲兄长。你有事直言便可,我就是不听又会拿你怎样,何必拐着一大圈串通旁人来游说我。”
慕流云怔立在原地,他呆呆地看着晏珏离去的背影,尚未及笄的女子身形已是十分窈窕,墨色长发大半散下,小半用金簪简单束起,红衣在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交错中仍格外醒目。
她独自走着,周身一人也无,从背影望去看不见平日或飞扬或显露锋芒的双眼。慕流云耳边仍在回荡着方才女子所说的那句话,他喉间一涩,忽然便觉得他效忠的师妹孤独无比,一个人站在山巅,周围布满锋锐的刀刃,稍稍一动就是遍地鲜血淋漓,她下不来,旁人也上不去。
她在等人上去,却直至今日,或许一生,都孤立无援。
慕流云静立片刻,又想到晏珏话中透出的意思,才有了几分高兴,清安想必是劝过阿珏了,那么除去赵玄一事,大抵可成。没有了赵玄,宗七屈权等人又是那么个不争不抢的性子,他便可全力应付薛家,无需担忧己方后院失火了。
.
皇宫,紫宸殿。
“你倒是许久未来了,今日怎么就想起上我这来了?”
“见爹爹还需要理由嘛,前几日阿珏不是忙着那些破事才无暇来看爹爹,爹爹难不成就要因这怪罪阿珏么?”晏珏摇着抱在怀中的手臂,轻声撒着娇,眼睛却是略显茫然地看着地,不知在为什么事而烦忧。
言弦歌看在眼里,放下手里的书,道:“温左相前几日已被问斩,其家人也流放至北疆,温时一人翻不起什么风浪,这事你父皇已记你一功,百姓中也多有赞扬你。李府日日有官差进出调查案件,民间皆以为是薛家害了李太傅,薛家这次怕是难将自己从此事里干干净净地拔出来,朝中各方党羽一时人人自危。现今局势算不得高枕无忧,却也算是有些许进展,你为何愁眉苦脸?”
晏珏展颜:“无事,只是许久不曾进宫,想念宫中御厨做的饭食,一时便苦了脸,让爹爹忧心了,是阿珏的不是,阿珏给爹爹端茶,爹爹勿怪勿念勿忧。”
言弦歌接过晏珏端来的茶水,摇了摇头,对这马屁精很是无奈。
“我也管不了你了。这就叫人传膳,你走时把这些厨子带回府去,免得日日在府里愁容满面,像谁欺负了你似的。”
晏珏闻言,顿时喜笑颜开:“阿珏谢过爹爹,爹爹风姿依旧,世间无双。”
.
心满意足地领了一队厨子出了宫,晏珏大手一挥,让车马带了厨子先回府,自己则带着阿七径自往东陵王府去。
先不论东陵王府看门的守卫见了这位小祖宗怎一个目瞪口呆吓得魂不附体,生怕是来踢场子砸府邸的,这等事这小祖宗幼时做的多了,这两年倒是收敛了好些。
许多人都习惯了珏公主的有礼有节进退有度,但他们仍不忘当年这二世祖是如何带着一干护卫四处砸权贵之家的大门,告上金銮殿又被皇帝和宫中的那位软硬兼施生生让这些遭罪大臣们诉苦无门。
晏珏掠过无关人士,只寻正主。
“东陵王府处处透着暴发户的气息,这么多年竟也不改一改,你这般的仙人住在这近二十年岂不是要被染黑了?”晏珏摸着手下玉质通透手感甚好的桌子嫌弃道。
晏纪熙一身天青色锦袍,外罩同色罩衫,衬得眉目如画,好似仙人。他正要开口,一道声音便传来,打断了他欲出口的话。
“他人皆道我王府典雅韵致,公主此言倒是新奇得很,却不知是不是那起子人统统耳聋眼盲,竟说的和公主所言全然不同。我为公主长辈,腆着脸问一问公主,何样的府邸您才觉得好呢?像您的公主府那般金梁玉栋珠帘翠瓦好?还是像您的表叔父季九爷那样结草为庐才是好?”
说话的人打扮颇为富态,眉眼高高吊起,眸中尽是讥诮,在丫鬟的搀扶下缓缓走来。
晏珏一改方才的散漫,面上一片冷意:“表叔心性出尘,从不在意身外物。我公主府再如何富丽,那也是按规制建的,我住得坦荡,自然是最好。不像那些心比天高的人,总觉自己不够,偏要从别人那里挖些东西过来,不知用得安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