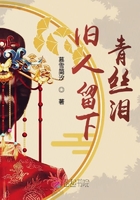——[德国]布·克罗瑙埃
女面包师的举动突如其来,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回家的路上我才想起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首先想起了一次晚班火车。在一个小站上,一群年纪大的妇女也不管有无座位,蜂拥挤上车厢。她们个个显得异常激动,衣着随便,穿着褪了色的套裤和大衣。体形与衣着一样,看上去也很不顺眼,但她们根本就无所谓。有几个穿得好一点的,可也吓人,衣服紧绷在身上,恐怕也不太舒服。车厢里顿时一片喧闹,犹如年青人的宿舍。
这些来自小县城的妇女,身体健壮,此刻没有丈夫的陪同,马上就混入一群活泼的小姑娘中间,她们老是“我们……我们的……”唠叨个不停,还不时地跑到女导游那儿去撒娇。她们相互指点和寻找货物发送站的表册,就像在上演精彩的木偶戏。其中有一个妇女还向别人讲述,在夜间如何将座位摆成卧铺。
我想,女面包师也会在她们中间的。不过,即使在她们中间,她也不会自在。她或许还是不引人注目为好,就像小老太婆一样。她根本不能和她们相提并论,她是个孤独的人,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是个从一开始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
的确如此,在周末里,她在家里磨磨蹭蹭。可她总弄不明白,平时的街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真是川流不息,有的匆匆忙忙,有的慢慢腾腾,尔后便都消失了。而她一定要待在自己那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有时还要将百叶窗放下,自个儿就这样打发日子。如果她星期一不露面,不按常规走出家门加入到人流中去,不向这个人那个人问好,她或许就被人们遗忘了。
这是一家洁净的、生意繁忙的面包铺子。在这里,人们总是那么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她在里面当然会很受排挤。她呀,简直称不上面包师,在我看来,她只是个面包铺子的职工,或者只能算是个辅助工。我暗自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倒霉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取的,就像叫那个身体魁伟、面色红润的老板娘为“守护神”一样。
这儿所有的面包,一天两次送往市内各销售点出售,卖不掉的大小面包晚上再送回来。由于一切都经过仔细计算,准确核算,又通过电话落实当天的销售额,所以面包往往销售一空。碰上意外的好生意,准会使她们高兴。这儿的工作是两班制,售货员换班不规则,什么活儿都得干。有那么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固定的营业点,对那些算账不够快,不能很准确、利索地分切大蛋糕,不能对繁忙的工作应付自如的年轻姑娘常常要调换。而手脚熟练的同事,总是冷眼旁观。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铺子如同修道院的修女跑到街头去做买卖一样。售货员接待顾客的态度,时好时坏,变化无常,令人难以捉摸。有时她们热情地招呼你,服务也很周到;有时则冷若冰霜,使个眼色算是在问你“要什么”,到最后才很不乐意地把价格从牙缝里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店里所有人员的做法总是一致的,如果有哪个人违背了这个规则,那么他根本没有在此长期工作的可能。
一天,“倒霉鬼”站在那儿,个头要比其他的人都高,灰褐色的皮肤就像干瘪的面包,瘦骨嶙峋,没有一点儿精神,还有那厚厚的嘴唇更显得厌烦,怏怏不乐。她压根儿就不知道面包的售价,不得不一再向同伴们发问。在顾客面前,其他同事可随意支使她。显然是出于“守护神”和她的棍棒的威慑,大伙儿才将注意力集中到顾客身上。她们就像老相识似的同我打招呼,我刚一开口,她们就猜到我要什么了。
今天,她是新手,其他人,不论是站在柜台前还是站在柜台后的我都认识。当然,面包铺伙计们这种热情的劲儿不会维持很久的。不过,只要“倒霉鬼”站在一旁,这些有经验的售货员就比以往更饶舌,她们俨然以行家自居,将新来的排挤在一边。她们能见机行事,处事利索,忙而不乱,和颜悦色,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倒霉鬼”的生意招揽过去了,当然也包括我的生意在内。顾客们就因为她们态度好,所以都喜欢到她们那儿买小面包。假如有人到她们那儿去选购,“倒霉鬼”也是挺乐意的。店堂里一旦有什么笑话出现,她也鼓起勇气一起笑,不过笑得太晚了,只是人笑她也笑罢了。另外,别人算账,总是在人不经意的当儿,一眨眼就算好了;而她每次都得绞尽脑汁,总是吃不准似的嘟起了嘴巴。
有时,她也可能被安置在指定的营业岗位上。她们故意让她一个人到前面去站柜台,其他人干些记账、整理工作。她站在那儿被人监视,觉得十分难堪。她们眨巴着眼,倒好像有义务来检查她似的。与这些相比,她还是较适合搞搞手工和面。
一次,她碰到接待三个年轻学生的机会。他们不要马上把面包切开,而是要一只只地切,并且要切得一样。女面包师认为别人可能是想让她出丑,她必须一连三次切开各个小面包,中间夹上巧克力威化。她夹起面包来很不稳,摇摇晃晃地把夹心面包从柜台里递给他们,年轻人用脏手伸到她那沮丧的面孔前,做了个示范动作:该怎样用力一夹,面包正好夹扁,这样才恰到好处,可直接往嘴里送。三个年轻人故意全部用分尼,各自付了账。
在这期间,一位先生走了进来。他一头银发,身穿笔挺的驼毛服装。女面包师动作迟缓,一直让他久等着。作为一个顾客,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最后直到另一个售货员迈着轻盈的步子迎上前去,招呼了那位有身份的先生,这才避免了铺子的声誉受损。
夏季,那灰蒙蒙的七月天,所有的东西都沾满了灰尘,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各个角落和花园里,不时地传来孩子们的声音,这一切就像树叶长在树上那样为人所熟知。而“倒霉鬼”就关注着这些变化。我被人流挤到了她的面前,想买四块苹果蛋糕。她很自然地去规定她取货的地段拿面包,她的特点就是能干其他售货员所不愿干的事,明显的差别就在于此。
她很熟练地拿起托盘,将一块圆蛋糕放在上面。突然,她停住了,紧张地扫了我一眼,厚厚的嘴唇蠕动着,嘀咕着什么,像是警告我有危险,但我并没有很快理解她的用意。
“什么?”我大声地问,想让她也大声些,起码能让人听得到。她避开我的目光,提高嗓门,用做生意人的口吻反问我是不是要樱桃蛋糕,而眼睛里却流露出焦急和恳求的目光。
“不,”我很坚定地说,“为什么不能买苹果蛋糕呢?”她后退了两步,走到货架边,小心翼翼地往两边瞅了瞅,又低声对我重复说了一下。我觉得周围的一切确实有些蹊跷,我看到顾客们嘲笑的神情。她突然抓起一只装有蛋糕的纸袋,在上面涂了几个字,幸好这时大家都很忙碌,她的这一举动没有被别的售货员注意到。她像是很偶然的样子,将食品袋放到玻璃台面上,故作镇静,只差一点没有哼唱起来罢了。可我还看不清是什么字,我猜不出女面包师到底在警告什么危险。她默不作声,用责备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就算是回答了。
难道我该压低嗓门不成,我太笨了,她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作出不要声张的手势。接着,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出现了,她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通红,血红血红的。她到里面取了奶油蛋糕,然后又走到我的跟前,说:“是否还要点什么?”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她想要我跟她一起去,我马上跟她去了。她弯下身子,又嘀嘀咕咕着什么。不过,这次我竭尽全力终于听清了她说的话:“别买苹果蛋糕,那是昨天的,是昨天的!”很显然,她不希望有人听到她这几句从她牙缝里迸出来的话,也没人偷听她说话,很好!然后她惊恐地用手捂住那不断颤抖和抽搐着的嘴,急忙把纸袋从面前拿开,她在玩弄这一手法时,也顾不得外面等待的顾客了。她再一次指着纸袋给我看,并读着上面写的字:“昨天。”
“我不能把此情况泄露出去!”她轻轻地补充说,并当着我面将纸袋揉成一团,撕碎,将纸屑塞进工作服的口袋里。当然,我这回买的是四块奶油蛋糕。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她表示谢意,她也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目送我走出店门,好像我们经历了一次冒险活动。
走到回家的路上,我仔细回想起这件事的经过。对我来说,至少是有愧于她的。因为“守护神”老板娘会把女面包师私下辞退的,这个结局是必然的,也是无法改变的。
在我三十二岁生日那天,我与玛立欧一见钟情。过三十三岁生日时,他将海边的萤火虫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在我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得到了雪地上的“ILOVEYOU”。今天是我三十五岁生日,我得到了无名氏送来的三十五枝深红的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