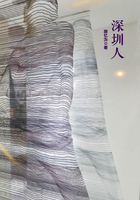山本忠贞斜倚到车窗上,缓缓抽着雪前,从歪戴着的军帽的帽沿那里,透过了从磁杯里边蒸腾上来的咖啡的热气,在这边望着她。
车一开出哈尔滨车站,在铺满了皑皑白雪的平原上驰走着,天慢慢地暗下来时,他已经注意到在隔壁那间卧室里,带一点汉城口音唱着《银座行进曲》的,那个不知国籍的女人是一个很可怀疑的人物了,为了她的老于风尘的样子,她的冷漠的声音,脚下那双名贵的缎鞋,轻捷的步趾,尤其是因为她的少妇型的,妖冶而飘逸的风姿。她老是在那里反覆地唱着同一的调子,悉悉地,象从紧闭着的嘴唇里边漏出来的。睡在床上机械地听着这充满了北国的忧郁的歌声,车顶上的电灯蚌珠似的放出光彩来时的山本忠贞完全忘了藏在帽徽里的,进攻辽东义军的军事密件,而对于隔室那位诡秘的夫人抱了满怀不可遏制的好奇心。一个娟好的独身妇人,那样的对象是不能不使哈尔滨特务机关的调查科科长山本忠贞少佐睁开一只侦察的眼和一只爱慕的眼吧。
“毒品的贩卖者么?舞女么?还是匪贼的间谍呢?”被这些问题苦恼着的山本忠贞在餐车里仔细地看了喝着咖啡的她,忽然毫无理由地高兴起来:“总之,不会是一个贞节的女子吧。”所以,推歪了军帽,摆出不修边幅的轻薄态度来。
坐在餐车里的她。穿着堇色的衫,有一条精致的鼻子和一张精致的嘴,眉毛修饰得非常纤巧,一身时髦的西欧风味一点也剖别不出究竟是哪一国人。她把香烟灰弹在餐盆里,时常把晶莹的眸子从鬓边闪到山本忠贞脸上来,碰到他的眼便低下眼皮,让长睫毛遮住柔媚的眸子的流光,把笑意约住在嘴角,温雅地拿起咖啡来的姿态简直是在跟他卖弄风情了。家眷远在东京的,过着禁欲生活的山本忠贞,只喝了半杯鸡尾酒便被桌旁的水汀烘得浑身的情欲古怪地燃烧起来。看看她在旁娉婷地走了过去,在他衣襟上留下了俱乐部香水的幽味,走到卧车里,碰地关上了门,他便似跌地闯进了她的卧室,用醉汉的声气喝道:“站起来!”
斜躺在床上她冷静地问道:“你有什么权利那样地命令我呢?”
“吹?特务机关调查科科长的山本忠贞少佐要搜查一个嫌疑犯也不行么?”
“很英俊的人为什么对于一个女子施行着那样粗鲁的仪态呢?”
“你那么漂亮的夫人不是也在做着不法的事么?”山本忠贞邪气地笑了起来。
“不法的事么?请你搜吧,随身行李都在这里。”把钥匙扔给了他,又丽丽拉拉地唱起《银座行进曲》来了。
“好本事!比我还镇静。可是你可知道山本忠贞少佐的眼是被称为显微镜的么?”一面咕哝着,一面打开了一只小提筐把一些零碎用品全倒了出来。他用把玩的态度检视着那些手套,丝袜,亵裤,睡衣,用责骂的口气调笑着道:“那样的睡衣!从浴盆里跳出来,穿着那样丝织的绣花睡衣,不怕一身的性感被水蒸气挥发到外面来么?这样珍贵的手套!连一双爱的手也铿吝到要遮蔽起来呵。呔!如果不是想怕腿部的肉来诱惑特务机关长山本忠贞少校,总不需要穿那样透明的袜吧。”挤着眼瞧了她的腿:“脚上的还是桃色的袜呢!你看不是连柔软的汗毛也看得很清楚么?可是山本忠贞少校并不是意志薄弱的家伙呵。”把亵裤拿到手里时,他已经不是在检查违禁品,却是在欣赏尖端流行物的猎奇趣味了。“也有那样瘦削的腰肢的么?把那样桃绯色的短裤穿了起来,就是印度的禁欲者也没有法子保持独身了吧!可是那只胸褡却不免大得和亵裤大不得称了吧,一个瘦削的腰肢也能承托这样丰满的胸部么?”
整个提筐全察看过了以后,索性把床下的那只大铁箱也打了开来,铁箱里边除了一双银缎鞋,一双水红的高跟鞋,全是些衣服,正在说着“衣服也留着余香呢”那样的话时,她却跳起来道:“还骚扰得不够吗?”
山本忠贞刚在搜寻不出什么违禁品,觉得没法下台,忽然看见铺在床上的毡,便抢前一步,扯开那张毡,一大包烟土在毡下赫然显现了出来:
“呔!那是什么东西!”
婉娈的,求情的笑马上在她俏丽的脸上浮现了出来,拖住他的手,显着那样柔弱迷人的样子:“是第一次,人家托我带的。总可以商量吧?我知道你是不会为难一个女人的。”
“可以商量,我和你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呢?”一只手抬着她的下巴,细细地看了一会道:“真漂亮!可惜做了偷运烟土的私贩。”
她可怜得象一只绵羊:“不是私贩呀,山本忠贞少佐。”
“你还是想跟了路警去呢?还是希望做三天山本夫人?”
她做了个媚眼道:“你还叫我选择么?”
山本锁上了门,哈哈地大笑着,把手伸到她怀里去道:“让我来测量一下你的胸褡的尺寸吧。”
她低低地笑着道:“这一带很多匪贼劫车的事件,而且,你看车动摇得多利害,又没有浴室,——到长春常磨馆去住三天不是很有趣吗?”
第二天,山本少佐和他的新夫人从宪兵和警察的双重搜查网里堂皇地跑了出来,在常磨馆最上好的房间里,亲密地站在窗畔眺望着街景了。
“这里不是有着马赛克磁砖铺的浴室吗?”
山本拉拢了丝绒的窗筛,拎着水红的睡鞋和绣花睡衣,把他的新夫人抱到浴室里边,在浴缸里放满了淫逸的热水,“一定要等灯亮了才行么?”那么地说着,捉住了她,给她卸衫,她缩在他怀里嘻嘻地笑着时,外面的电话响了起来。
“讨厌!是谁打电话来呢?”跑出去,拿起了电话。
“山本么?”电话筒里嗡嗡地讲着的正是宪兵司令冈崎义一。
“冈崎么?本来预备一到就来拜访你的,想不到你已经先打电话来了。”
“你昨天不是猎获了一个新夫人么?”
“你怎么已经知道了。”
“你跟她一同在长春下车,我是不能不知道的。”
“好家伙!”
“可是朝鲜人,讲话带一点汉城口音的,身材很苗条,鼻子旁边有一颗美人痣,笑起来很迷人,走路时带一点媚态,腰肢非常细的?”
“你认识她不成?”山本惊异起来了。
“现在还在你房里吗?”
“你想来看看她么?”
“你现在马上拿手枪指住她,别让她走一步。”
“拿手枪指住她?”
“你还不知道她就是有名的女间谍Madam X么?”
电话挂断了。
“Madam X可惜现在就被发觉了,过了今天再被发觉不是很好?”说着,霍地拔出手枪来指住走到浴室门口的他的新夫人:“亲爱的,请你在那里站一回吧。”
“用什么手枪呢?旅馆不是已经受包围了么?”声色不动地靠在门上。
“Madam X真是尤物!可惜了。”
她不做声,轻轻地唱起《银座行进曲》来。
五分钟后,冈崎义一指挥刀在腰间咯咯地响着,跟在十二个宪兵后面走了进来。
“Madam X久违了。”
他打开了那只小提筐,和那只大铁箱,从大铁箱里寻出那包烟上来,笑着说道:
“还是用这个笨拙的老方法么?”
抽出指挥刀从烟上的中间切下去,拿手指钳出一颗蜡丸来道:
“你还在担任传递工作么?”
他插好了指挥刀:“请你到宪兵司令部来谈谈吧。”向山本讲了一句:“对不起,请你另外再找一个吧。”带了她走了。
山本在长春住了两天,“另外再找一个,哪里再找得到那样名贵的宝物呢!”怀着这样的思想,安安静静地搭了车到沈阳,把行李放在旅馆里,去看了几个朋友,预备回来好好地睡一夜,明天上第二师团本部去把文件缴了,玩一星期便回哈尔滨去。
从朋友家里喝了点酒,回到旅馆,走进自己房里,只听得浴室里哗哗的放水声。
“见鬼么?”
刚想跑进去看时,浴室的门开了,在热腾腾的水蒸气里,亭亭地站着的,饱和了新鲜的性感的,站在瘦削的黑缎鞋上的,洁白而丰腴的裸像正是Madam X,他不由像见了狐精似的迷惑起来,半天才说出话来道:
“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
“你看,我不是刚洗了身么?冈崎怕有半年没有洗澡了,身上脏得像乞丐似的,把我的肉也弄脏咧。”
听了这样的话,山本的情欲,在车上给水汀蒸发出似的又给从浴室里喷出来的,弥漫的水蒸气毫无节制地蒸发起来了。
“脏也好,干净也好,既然回到我这里来,至少要请你做一小时山本夫人再送到宪兵本部去吧。”
野兽似的扑了过去。
从她身后闪出两个拿了四寸勃郎林式的手枪的壮汉来。山本在枪口前噤住了。
“你明白为什么我要车上勾搭你吗?难道是我会爱上一个粗俗的日本男子不成?不过是想你把烟土里边的蜡丸搜了去罢咧。不料你竟蠢到连烟上里边可以藏蜡丸的事也不知道。冈崎是比你稍为聪明一点的笨汉。他以为蜡丸里边藏的是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计划书,派了一中队去搜寻我们——明天你就会知道,你们的一中队全部覆没在我们机关枪底下了。”
山本不由咆哮起来道:“你就为了要把这些话来侮辱我才跑到这里来的么?”
“请你把声音放低一点吧,虽然是四寸的手枪,洞穿你的肢体的力量还是有的。”她拿毛巾抹着身子:“你知道我跑来干吗?你是不会知道的。我想来偷盗你的秘密文件的,想不到搜遍了全房间,还是搜不到,失望得很。现在我也不想你的秘密文件了,只想要你的帽徽做你对我的热恋的纪念品。
“呔!”山本刚一抬手,下巴给打了一拳倒在地上,给塞住了嘴,绑住了手脚。
“没用的东西!”
她把他的帽徽摘下了来交给那个壮汉道:“你们先去吧。”
那个壮汉啐了一口道:“那么没用的家伙,还费了两个人来服侍他。”笑着走了。
她从浴室里拿了一大堆衣服出来:
“你不是说把绯色的亵裤穿了起来,就是印度的禁欲者也没有法子保持独身了么?现在我就穿给你看,报答一下你的过份的称誉。”
她一面嘲笑着他,一面穿好了衣服:“莎育娜拉,特务机关调查科科长山本忠贞少佐!”走了出去,终于在房门外低低地唱起《银座行进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