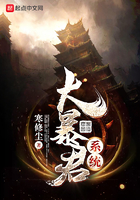狂沙派的弟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种都是些在其他行业犯了错误或者出过事故的普通人。这些人多为车夫,厨师,木匠之类。
他们通常不会武功,也不是江湖中人,到狂沙山只是在其他地方混不下去,来这里混口饭吃。与其说他们是弟子,还不如说是来这里做工的更合适。
这些人人数不少,将近少一半的数量,他们对或许对周掌门有些感激之意,但是对狂沙派没什么感情。
对他们来说,这里只是工作糊口的地方,他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等着供养。让他们拼命替已经死掉的掌门报仇,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
第二种,则是像周祝寅这样的非入室弟子,类似客人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武功已经练成,甚至已经在江湖上小有名气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周掌门请到了狂沙派来,不过基本上都没有拜在狂沙派门下,名义上不算狂沙派的人。
这些人数量不多,只有十几位,但这些人武功都不弱,所以平时在山上地位也比较高。只不过这些人通常都是来狂沙派躲避仇家,或者暂时无处可去来这里栖身的。
他们的心态比较微妙,因为他们心里其实对狂沙派没有那么深厚的情义,若是想要他们拼命报仇,他们是不愿的。可是现在既然掌门已死,而他们平时又是狂沙派的上层,此时如果能抓到机会的话,说不定能趁机接管狂沙派。
因此这些人此时都持一种观望的态度,既不像那些底层工匠们那样明显的表示出恐惧和闪躲的表情,也没有像领头高叫的那些人一样,表现出要决一死战的样子。
因为他们通过刚才周祝寅和周掌门的一战,已经看得出来两个人的武功均已经到了远超他们的境界。
虽然他们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周祝寅已经受了伤。可是俗话说“将死之虎也胜过群羊”,周祝寅到底伤势如何,如果他拼死一战,还能发挥出多大的战力,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更何况,旁边还站着一个外表平凡却充满了令人猜不透的气息的表弟。别的不说,单凭周掌门那一拳已经到了鼻子尖上,他都一动没动这一点,他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表弟,若不是一个绝顶高手,便是一个傻子。
然而,刚刚揭穿了周掌门杀人真相的人,会是傻子么?
因此这十几个人,现在的想法均是保持观望,看看下面怎么发展。即便要动手,也让那些狂沙派弟子先上,自己则看情况而决定到底帮哪一边。
除了这两种人之外,剩下的第三种,便是真真正正的狂沙派入室弟子了。他们这些人大多是一些没有亲人的苦孩子出身,在人生倒霉的关键时刻被周掌门收到山上,并且亲传他们武功。
再加上周掌门每天不停的给他们“洗脑”,是以这些人中的某些弟子,真的从心底里热爱着狂沙派。他们把狂沙派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家,而周掌门便如同他们的再生父母一般。
当周掌门承认自己杀人的时候,他们虽然也感到无比震惊,可是他们马上又都被周掌门的话给说服了。
不错,为了狂沙派的美好未来,死一个新掌门算什么呢?
而当周掌门对周祝寅出手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在心中为周掌门欢呼呐喊,以为以周掌门的武功,顷刻间便可将这二男一女三个外来捣乱的家伙击毙。
然而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掌门却以一种近乎耻辱的方式,被人杀死在了他们面前。
其中一个平时最是敬仰周掌门的年轻弟子,当时心中便如油锅一般沸腾起来,他抽出宝剑振臂高呼,要誓为掌门报仇。
如果周祝寅不吐这口血,其他的入室弟子或许还不敢如此。但此时看到周祝寅口吐鲜血站立不稳,便全都来了勇气,纷纷也都亮出兵刃高喊起来。顷刻间,他们便将周祝寅三人围在了当中。
小鲤鱼和周祝寅脸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而兰辉郡主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当下心中震惊、害怕、兴奋、激动甚至小小的期待等各种情绪乱成一团。
她跑到了二人旁边,摆出准备迎敌的架势,只不过手臂却抑制不住的微微发抖。
周祝寅在小鲤鱼的搀扶下,往四外看了一圈,咳嗽着笑道:“咳咳,小鲤鱼,你有点夸大其词了吧?对你来说,这些人怎么比得上我刚才摔死的那个麻烦?”
小鲤鱼道:“对于我自己来说,自然算不得什么,可是我现在两只手都被占满了啊。”
周祝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的确,以小鲤鱼的武功,别说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上,他也能游刃有余,轻松无比的全身而退。
只是现在,他另一边站着兰辉郡主。郡主虽然也会武功,可是终究不高,而且郡主几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若是真打起来,必须还要靠小鲤鱼保护。
保护一个人就够难了,现在自己身上也受了重伤,若是让小鲤鱼同时保护着两个人和对方打,确实难度大了些。
想到这里周祝寅挣扎从小鲤鱼的手中挣脱出来,往旁边挪了一步,扶着胸口站定道:“你只被占了一只手。”
小鲤鱼低声道:“这回我可是学到教训了,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好奇了,实在是太麻烦了。”
周祝寅道:“你的麻烦已经到头了。带郡主走,我保证没人能去追你们。”
不料郡主却说道:“呸,我不走,要走也要带你一起走!我当初都没能要了你的命,这些人凭什么杀你?”
小鲤鱼看了看周祝寅道:“看到没有,我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啊。”
刚才那群弟子虽然围住了三人,可是却也忌惮周祝寅的武功没敢冒然出手,此时见到周祝寅从表弟的手中脱出来,自己稳稳站在了一边,更是心中增添了不少畏惧。
这时,那刚才领头的年轻弟子见众人只围不攻,十分不满的喊道:“干什么?一起上啊!那杀人凶手已经受了重伤,另外还有一个女人,我们怕什么?”
被他这么一鼓噪,众弟子将包围圈缩的又小了一些,眼看着就要一齐冲上来了。
小鲤鱼从人缝中偷眼瞧了一下那些没有围上来的人,那些打工的人还是都尽量躲的远远的,生怕瓜葛到自己。而那十几个高层人士,看到这里,似乎已经认为自己这一方处于弱势,准备要出手帮对面了。
小鲤鱼轻叹一口气道:“哎,只希望周掌门收上来的人都不是草包,多少能识货一点吧。”
兰辉郡主问道:“喂,你要干什么?”
她话还没说完,就见小鲤鱼没有任何征兆的原地跃起,直奔那拿剑的领头青年弟子而去。
那弟子大惊,急忙挥剑朝着小鲤鱼飞来的方向用力刺去。谁知道他的剑眼看就要刺中小鲤鱼的胸口了,然而小鲤鱼却突然从他的面前消失了。
正当他感到不可思议之际,他感觉从身背后伸出来一只手,轻轻的用手指弹了一下他的胳膊肘。接着他便感到半边身子都瞬间麻痹起来,剑也脱了手。剑刚刚落下没有几寸,就被一个影子刷的一下给带走了。
原来,小鲤鱼刚刚趁着他刺出一剑之际,已经绕到了他的背后,从身后下了他的剑。
年轻弟子大骇,放声高喊:“快!大家一起拿下他!”
众弟子立刻炸开了锅,附近的人纷纷朝着年轻弟子的方向冲过来。
然而此时小鲤鱼真的宛如兰辉郡主口中的泥鳅一般,钻入了围拢住他们的人群之中。只见他一会儿从这个人的背后探出一条胳膊来,卸了他的刀。马上又从那个人的腰下钻出一只手来,夺下他的剑。
兰辉郡主的眼睛里根本看不到小鲤鱼,只能远远的看到一条影子在人群中忽隐忽现。影子所到之处,人群无不发出阵阵惊呼,同时阵脚大乱,互相碰撞,东倒西歪。
过了没多久,那影子腾空而起,从人群中飞出,轻盈的又会飞到了二人身边。
小鲤鱼重新站在了周祝寅和兰辉郡主的身前,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他两只手不再空空如也,而是抓满了各种各样的兵器。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他便一个人钻入人群,在一人未伤的情况下,将所有的人的兵器全都夺了过来。
他现在的双手,的的确确是被占满了。
小鲤鱼双手同时一松,兵器发出多声哐当哐当的响声,摔落到地面上。
这些围住三人的弟子中,虽然不是全都使用兵器,也有很多人是学习的周掌门的拳法,准备空手来迎战的,是以刚才小鲤鱼钻入人群的时候并没有碰到他们。
然而虽然刚才他们没有碰到小鲤鱼,可这仅凭一个人瞬间就将几十个人的武装全部卸下的壮举,也深深的震撼到了他们。
领头的年轻弟子虽然剑被夺走,可是却依然不甘示弱,大喊道:“你们干什么?就算没有兵器,我们也要替掌门报仇!就算粉身碎骨,也不能辱没了狂沙派的名声!你们看着干什么?上啊!”
然而人群中却没有一个人敢主动上前,全都默默的吞着口水,摆着架势,继续留在原地。
年轻的弟子大怒:“一群懦夫!我自己一样要报仇!”
说罢,年轻的弟子举起拳头朝着周祝寅冲了过去。然而他的拳头刚一靠近周祝寅,就感觉自己的手腕被什么如钢铁一般坚硬的东西给锁住了。
周祝寅一只手钳着年轻弟子的手腕,冷冷道:“你是条汉子,但你不是对手。”说罢,他用力一甩,年轻弟子朝旁边摔到地上。
谁知道年轻的弟子立刻又从地上爬了起来,准备再次扑上来。
就在这时,从大厅外面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一个人,一边跑一边高喊着:“哎呀呀呀,掌门,我回来了!”
众人全都被这叫声吸引,纷纷扭头看过去,原来是一个衣衫褴褛,双目呆滞的大个子男人从外面跑了进来。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上看,任何人一眼都能看出这个男人是个傻子。
这傻子也不看现场什么情况,自顾自的跑进了大厅,跑上了高台叫道:“掌门,你派我办的事,我终于办完了。我紧跑慢跑还是慢了,没赶上大典啊……掌门……诶?掌门你怎么了?”
傻子发现了周掌门的尸体,跑到了近前低头仔细的看着:“诶?掌门?你怎么了?啊?是不是走路没站稳摔倒,撞到墙上了?哎呀,我早就说过,掌门你平时就那么喜欢摔倒,早晚有一天会撞到墙上的,你当时还笑我。现在,你看,你真的撞到墙了吧……”
众人被这傻子的突然插入给打断,纷纷站在原地默默的看着这个傻子。连那年轻的弟子,也都似乎忘了报仇的事情,只是呆呆的看着傻子的一举一动。
傻子道:“掌门,你起来吧,你起来啊?掌门,你不要装死啊,啊?掌门,你真的死了啊?”
傻子终于发现了周掌门已经死了,马上跪到地上,抱起掌门的尸体嚎啕大哭:“哎呀,掌门啊,你怎么死了啊!我早就说过,让你小心一点不要再摔倒了,谁知道你还是撞到墙上给撞死了啊!掌门……”
这时,不知道人群中谁说了一声:“咱们掌门平时确实经常摔倒,也难怪傻子误会。”
过了片刻之后,角落里的那些打工的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喂,咱们掌门难道不是自己摔的吗?我刚才离得远没看清……”
接下来,那些打工的人群里便开始此起彼伏的响起议论声:
“对哦,咱们掌门刚才就是摔死的吧?”
“是啊,是啊,咱们掌门平时就特别容易摔倒的,摔死也不算太奇怪吧……”
“啊,说的也是哈……既然是摔死的,那就没必要报仇了对吧?”
渐渐的,这些议论之声从角落里的几个工匠,逐渐蔓延到了其他的地方。最后几乎整个大厅里的狂沙派弟子都纷纷高声的说起来:
“对呀对呀,咱们掌门刚才就是摔死的啊。”
“没错,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撞到墙上摔死的。”
“是啊,咱们掌门平时就喜欢摔跤,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嘛。所以,说是摔死的,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就是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平时喜欢摔跤,自然有可能会摔死的……”
“既然是摔死的,那就不用报仇了吧?”
“笨蛋,自己摔死的,找谁去报仇啊?找墙啊?”
年轻的弟子眼神绝望的看着自己的同门互相虚伪交谈的样子,顿时眼泪如雨。
他自知自己没能力报仇,可是也不想再和这些人为伍,他趁人不备一个地滚翻,滚到了小鲤鱼身前地上的那堆兵器前面。接着他侧卧在地上,从旁边捡起一把剑,对准自己的脖子就要割。
谁知道,他刚要用力,一只大手死死的攥住了剑刃,鲜红色的血液立刻顺着那只手的指缝中滴落下来。
是周祝寅,他在最后时刻,抓住了剑。
年轻弟子哀道:“你干什么?”
周祝寅慢慢的弯下腰,凑到他耳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弟子幽幽道:“卢有信……”
周祝寅道:“我刚才说了,你是条汉子,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你和周掌门很像。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去死。第二,成为狂沙派第三代掌门,把你师父未尽的事业完成。
当然,这第二个选择很难,那边那十几个人虎视眈眈肯定要和你争。第一个选择则简单的很,一死百了,你自己选吧。”
说完,周祝寅松开剑,直起身走了。
卢有信手中握着粘着周祝寅血液的剑,表情狰狞的挣扎了半天,最终他还是双手一用力,将长剑掰断成两截,狠狠的摔在地上。
两个时辰之后,在一辆马车上。
几乎已经无法动弹的周祝寅躺靠在车上,艰难道:“小鲤鱼,这次之多亏了你。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再遇到什么麻烦事,我会……咳咳咳……”
兰辉郡主在一旁责怪道:“你就不要再说话了,好好给我歇着!我告诉你,当初你害我中毒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清楚呢。对了,还有你说我胖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必须给我好好活着,要是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要死也得让我打死,死在那个什么周掌门的拳头底下,我可不答应!”
其实之前兰辉郡主的确对周祝寅颇有反感,不过经历过刚才的事情,他发现,自己不但对小鲤鱼有了全新的看法,对周祝寅的感官也改变了不少。
对整个江湖,也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周祝寅道:“呵呵,是,遵命,郡主大人,在你打死我之前,我不会被别人打死的。哦对了,这次也谢谢郡主大人,为了找到证据,竟然让郡主大人端死人的内脏,实在是……”
兰辉郡主笑起来:“哎呀,笨啊你,要是真是死人的内脏,我怎么可能会去端的嘛。那只是小鲤鱼杀的一只鸡啦,那盆里面是鸡血,外加一堆厨房里大典剩下来的已经腐败的肉而已。不过虽然不是死人身上的东西,也的确够臭的……”
周祝寅讶异道:“怎么?那铜盆里不是王掌门腹中之物?那……你们怎么……咳咳咳……”
小鲤鱼在前面赶车,回过头来笑道:“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有人会在那么激烈的打斗中,还会有空闲去吞掉对方身上的东西嘛。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什么证据,甚至连那个证据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周掌门在找什么东西而已,而且从他那么紧张的状态分析,很可能他找的就是和案子有关的证据。所以我才故意赌了一把,假装去开棺验尸,做了一个假的证据出来。
现在你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和他对峙的时候,是不是从来没说过他掉的东西是什么?是他自己一直在说他掉的是玉坠,而我一直在用‘那个东西’或者‘这个证据’之类的字眼来代替。为的就是怕说漏了嘴,上了他的圈套。
不过后来证明我赌赢了,那周掌门做贼心虚。看到小兰端了一盆血水上来,都没有上前去亲自鉴定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就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说实话,我当时还真是挺紧张的,生怕他发现我是在虚张声势呢。”
周祝寅苦笑道:“说到底,你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啊……”
小鲤鱼道:“是啊,那周掌门聪明谨慎的很,根本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给我们的。”
兰辉郡主道:“诶?既然他那么聪明谨慎,那他那个玉坠是怎么丢的?”
小鲤鱼道:“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丢在犯罪现场了,不然他早就找到了,不会之后还在继续去找。我猜,或许是他在杀人的时候根本没有丢,是在之后的某个时刻才弄丢的。也或许,是早就已经弄丢了,只不过之前没在意,是在杀人之后才发现已经丢了。
只不过他心中太过于心虚,才会以为自己是在杀人的时候丢在现场了,之后才会那么紧张的到处去找。其实如果他不那么心虚,不到处去找的话,我或许还真拿他没办法。”
兰辉郡主道:“那他那个玉坠到底丢在哪里了啊?”
小鲤鱼道:“我哪知道,就像他自己说的,哪里都有可能,毕竟他是狂沙派的掌门嘛……”
就在他们几个人在马车中说话的同时,在狂沙山的大厅内,一群人正在收拾残局。
其中那个当着小鲤鱼的面被周掌门雇佣过来的车夫,在搬起大厅角落里的一把椅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条椅子腿的旁边,有一块白乎乎的小东西在放光。
车夫弯腰捡了起来,竟然是一块拇指大小,洁白温润,巧夺天工的浮雕玉坠。
车夫急忙左右看了看,发现没人注意自己,悄悄的把玉坠塞到了自己的怀中,然后若无其事的搬起椅子往外面走去。
他心想:这个东西看起来值不少钱呢,卖了之后可以给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再增添不少新的衣服和吃食。剩下的钱说不定还能让自己去清楼中好好的逛一逛,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