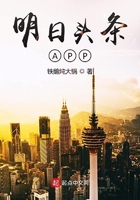五更天起床,是傅青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这个时候的街市还陷入沉睡中,向来是冷冷清清的。尤其是在入了冬之后,天亮得越发迟了许多,加上前几日又才落了一场大雪,故而待他打开药铺大门的时候,外面举目望去,乃是黑洞洞的一片,没有半点声响,也无分毫人迹。
点上灯,让橙黄的光给屋内增添几许暖意,之后他裹着单薄的衣袍来到厨房,用上一炷香的时间给师傅煎好药,亲自伺候着他一口口饮下,又服侍着对方重新躺好。
如此,他这一日,才算是正式开始。
通常而言,等他这时候在回到外堂时,天已然放出几许明光,对街以及毗邻的店铺也都纷纷有了动静。街道上零星地响着人声,甚至偶尔会有格外赶早前来的病人,已经探头探脑地候在了门边。
这是一种宁静得不断反复,平凡到近乎乏味的日子。或许在旁人看来,单调重复,索然无味,但他却觉得,这正是自己所渴求的生活。
只有在经历过极致的动荡,以及非常人所能想象的颠沛之后,人才会真正渴望平静。那是一种从心底油然生起的,不掺杂半分杂志的,真挚的渴望。
他的愿望,不过在这样细水长流的日子里,得一心人,然后,白首不相离。
只可惜,世事总是无法完满的,总归是要留下些许遗憾的……
手里拿着开方子的纸笺,傅青鸿静静地看着屋外那被雪光反射得格外明亮的青石板地面,无意识间,竟出了神。
直到一声呼唤,拉回了他的思绪。
那声音虽然极力压低着,依旧可以听得出,是个清脆而悦耳的少女声音。
傅青鸿循声看去,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并不陌生的面孔。
那是纪思嬛的贴身丫鬟之一,芝臻。
泸州城十年难见的大雪,如今早已停了下来,然而正如人们所说,化雪时候,天反而愈发的冷。她小小的身子,站在地面的残雪中,有些瑟瑟发抖,鼻头也微微地有些发红。
傅青鸿颇有些意外,随即却又想到什么,神情顿时紧张起来,道:“芝臻姑娘,你这是……”
“傅大夫放心,小姐无恙。我此番前来,也并不是并不是小姐的吩咐。”芝臻第一时间打消了他的疑虑,小心地走进来,又将声音压低了几分,“其实,是我自己有一件事……想请傅大夫能帮忙。”
想到自己方才的误会,竟被对方全然看出,傅青鸿神情中稍稍透出些窘迫。然而他向来与人为善,抬眼见芝臻一脸不安的模样,反而弯起眉眼,格外温和地冲对方笑了笑,以示安抚。
“芝臻姑娘有什么是在下能帮得上的,但讲无妨,在下定然尽力而为。”他徐徐开口,柔声道。
芝臻咬着下唇,却朝周围看了看,道:“可否耽误傅大夫片刻时间?”
见她如此,傅青鸿当即感觉得到,对方要说的怕不是普通的小事。便将芝臻引到里室,道:“此处方便说话,姑娘有什么事,吩咐便是。”
芝臻这才点了点头,迟疑半晌后,从随身的包裹中摸索出一物来,置于案上。
傅青鸿垂眼一看,见那是一个用丝帕包裹着的东西,乍一眼看去,却也不知到底是什么。
芝臻不说话,只是将斯帕解开。
里面不是什么珍贵物事,而是--散散的一抔泥土。
傅青鸿不解地看着她,道:“姑娘这是……”
芝臻道:“这泥土之中若是有毒,你可有法子将它提炼而出?”
傅青鸿虽不知她用意如何,却依旧认真地思忖了一番,道:“在下过去曾听师父提及过,无论是毒还是药,倘若洒入沙石泥土之中,若佐以蒸馏烘焙之法,是能有法子重新提炼而出的。”
芝臻闻言,一双眼睛明显亮了亮,道:“那太好了!大夫,我知道一旦有了毒在手,你便能制作出解药,可是如此?!”
傅青鸿知道,她话说所指的,乃是自己那日对纪思嬛所说的话。
“实不相瞒,在下并无十成把握,只能勉力一试。”他稍稍纠正了芝臻的意思。
“只要有一丝机会,便还请大夫尽力而为。”芝臻死死盯着他,眼中尽是希冀和恳求。
“此事倒也不难,只是……”傅青鸿迟疑片刻,道,“不知这泥土,芝臻姑娘是从何处得来?又不知此物同小姐中毒一事,究竟有何关联?”
谁料芝臻却道:“此事,我……还请恕我不能直言相告。只是我可以对天发誓,为了小姐我豁出性命在所不惜,是决然不会加害于她的!”顿了顿,似有觉得若是什么都不告诉面前的人,对方也实在是有蒙在鼓里的嫌疑,便犹疑着道,“这泥土是我亲手得来,若能提炼出毒来,必然便是小姐所中之毒!”
傅青鸿狐疑地看着她,试探道:“此事……小姐并不知晓?”
芝臻颔首,隐隐间竟有了泫然欲泣的意思,“我不告诉小姐,是有迫不得已的缘故。只是此事急迫,还望大夫能尽快完成!大夫的这份恩德,我会牢记此生,尽心还报!”说着,竟是作势要下跪。
傅青鸿哪里会真的让她这么做,赶紧将人搀住了,道:“在下答应姑娘便是。只是解药制成之后,为防又有什么差池,在下会亲自交付给小姐,确认这前因后果。”
芝臻破涕为笑,“一旦制成解药,无需大夫相问,我也会将前因后果,尽数告知!”
傅青鸿叹气,还欲说什么,却听外面响起隐约的人声,似乎有病人来了。
他只好面带歉意地看向芝臻,对方却抢先道:“我这边已没有别的事,不耽搁大夫诊病了,这便告辞。”说完又是一阵风似的,匆匆离去。
傅青鸿立在原地,没有立刻出门,却是看了看还摊开在桌上的那抔泥土。
心中疑惑万千,然而从头理了理芝臻方才的话,隐约可以猜得到,这泥土便是让纪思嬛中毒的媒介。若当真如此,按照对方的意思,从泥土中蒸馏出毒,进而尝试着配出解药,也的确是可行之法。
虽然芝臻遮遮掩掩的行迹颇有些可以,但她毕竟是纪思嬛最可信的贴身丫鬟,理当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纵然可疑也无妨,届时是否当真服用这解药,他会让纪思嬛本人亲自决定。
想到这里,他小心地用丝帕把泥土重新包好,转身走出了门去。
然而他并非是去诊病的,却是对来者道:“十分抱歉,这几日铺子里出了些事,无法开业。若有急病,劳烦去往临街的张氏药铺。青鸿在这里给诸位赔礼了。”说着,在原地长长地作了一揖。
他在坊间声明甚好,平素里且不论坐诊时候,多晚都一定会帮最后一个病人诊治完毕。便是上门诊治的时候,也从来便是风雨无阻,任劳任怨。
邻里街坊向来对他赞不绝口,多少人还暗自盘算着想把自家的女儿许配给他。故而此番听他突然这么一说,旁人只道他一定是有迫不得己的急事,才会到需要关门歇业的时候。不仅不恼,却是反过来安抚于他。
傅青鸿有些无奈将人送走,回到里屋,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凝视着桌上那被丝帕包裹着的泥土,他知道,纪思嬛的性命安危,也许就系在其上了。或许早一日晚一日并无什么大碍,但在他看来,但凡能早一日帮她解除身体里的危机,他便愿意倾尽一切而为。
更何况只是几日的生意罢了。
哪怕自己想要的,纪思嬛无法给予,但他却并无怨言。只要看到对方一切安好,于他,便也是莫大的慰藉了。
想到此,他回过身,轻轻地将门掩上。
与此同时也做好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不眠不休的几个日夜。
近些时日,纪思嬛忽地又觉得身子不适。
倒也不是毒发时候,那般撕心裂肺的情形,只是精力颇为不济,整个人也显得颇为慵懒嗜睡,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一连在床榻上躺了好几日,却依旧觉得手足间没什么气力。玉蝉芝臻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张罗着要去请傅大夫,却被纪思嬛制止了回来。
病在自己身上,她格外清楚。这情形,同那毒并无直接的干系,不过是身子长时间的为毒素所侵蚀,已然孱弱到了骨子里,便纵是请大夫看过,大抵也只是“体虚”“气寒”一类的说辞。
纵然开再多补气养身的方子,也不过是指标而已。
不能从根本上把那恼人的毒解了,自己这身子迟早有一天会被它拖垮。
纪老爷来看过她许多次,纪思嬛强打起精神,却着意告诉他,太子已然作为钦差来到泸州,故而他不必亲自登门谢罪。并且,由于太子此行是暗中受命,旁人并不知晓,在泸州面见太子,也不合适。故而谢罪一事,不如暂且缓缓。
纪老爷对她这番说辞并未生疑,全然应下,只转而告知了她另一件事:在纪思嬛有些昏沉的这几日里,秦王的媒人已然来过,并且成功下了聘。
听闻此言,纪思嬛有些欣慰地扬了扬眉。段天璘敢有如此堂而皇之的动作,只怕是他和段天玦之间的形势,又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只可惜自己终日只是卧病在床,并不知晓。
这样想着,意识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她强撑着想要对纪老爷说点什么,对方却把一切看在眼中,反而替她掖了掖被角,道:“若是乏了,就赶紧歇息吧。为父先走了。”
纪思嬛点点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困意便已然滚滚袭来。
醒来的时候,意识中仍旧残余着些许模糊的意味。纪思嬛在朦胧间动了动身子,还来不及睁开眼,却听到床畔响起一个声音道:“醒了?”
纪思嬛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但很快却发现……那是个男子的声音!
她霍然睁开了眼,然而双目一时间无法适应明亮的光芒,故而看到的,只是一道背光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