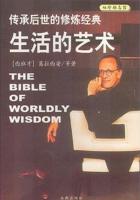大庭广众之下,李守忠敢对柴宗让动手。
如今私底下,又没有外人看见,李守忠反而不肯动手了。
见得柴宗让扑了过来,李守忠只是避让。
将身子一矮,便从对方肋下躲了过去。
不愧是逃命惯了的人物。
草屋又没有多大,柴宗让一把扑空,“啪嗒”一声,撞在了门上。
这货也顾不上伤痛,翻身又是扑来。
李守忠一边躲闪,一边压低声音求告:“殿下息怒,且听微臣一言!”
“背主之贼,安敢再度相欺?”
伤心、气愤、不甘,柴宗让已经是半疯狂状态,哪里还听得进去。
李守忠无奈,也只得拼命与之周旋。
两人扑闪的三五趟,实在不行了!
如此下去,动静太大,必定引起那贱民同韩德那蠢货疑心。
李守忠麻着胆子,瞅准机会,又是一巴掌抽在柴宗让脸上:“殿下!速速醒来!”
算上这次,第三次了!
有些人就是贱!
一巴掌下来,柴宗让倒是被打醒了不少,捂着脸愣在那里。
李守忠长叹一声,从袖筒取出一把匕首来。
一见到对方手中的匕首,柴宗让心中一惊,更是完全清醒了过来,赶紧喝了一声:“大胆贼子!君前露械,莫非有弑君之意?”
身子不由自主往后退去。
李守忠苦笑了数声,殿下竟然疑心自己若此?
走前数步。
见得对方持械前来,柴宗让心下更是大惊,连连往后退去:“有事好说!别动刀枪!”
李守忠更是苦笑不已,殿下竟然胆小若此?
“啪嗒”一声,李守忠跪了下来,将匕首倒转,刀柄往前伸来:“殿下既有疑心,微臣愿一死以证清白。只求殿下给微臣片刻功夫,死前且让微臣一诉衷肠。”
虽然是倒持,匕首到底在人家手里。
柴宗让又岂肯前来?
退后数步,背脊倚上了柴门,没法后退了。
摆了摆手:“先生有何言语,尽管说来!”
李守忠长叹了一声,将匕首放于地上,远远推向柴宗让,跪伏了下去:“自赵逆篡位之日算起,到如今已有十年。十年来,微臣不治家产,不配婚姻,所为者何?正为受世宗皇帝厚恩,而欲报之于殿下!十年间,赵逆重重围剿,探子屡屡作乱,臣奉殿下四处逃亡,常于梦中惊醒,只恐殿下有所万一。十年来,臣殚精竭虑,勉力维持,已是心力交瘁。顾臣今年三十有六,而华发早生,双鬓已斑,惶惶然如垂暮之人。所为者何?殿下若果然有相疑之心,请赐微臣一死!”
说到这里,李守忠泪涕齐下,拜伏于地。
想起这十年的点点滴滴,柴宗让也有了几分感动。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众人逃亡这十年来,中间数次险些为赵逆所擒,要不是这李守忠数度舍命相救,哪里会有自己的今日。
感动归感动,自己小命要紧!
柴宗让走前数步,将地上匕首远远踢开去。
又是前行数步,到得距李守忠二尺开外,不肯再往前来,也不上前扶起李守忠,反而开口道:“若有苦衷,何不说来?”
“殿下可知,今日我等已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这话柴宗让明显不信,自己货真价实的殿下身份乃是最大的保障。
在场的都是忠贞之士,谁敢对自己这位殿下动手。
这货刚刚开口就被李守忠扑倒在地,倒是没看到四周一圈的刀子。
对这话自然是不信:“休要大言唬人!”
“微臣一片忠心,岂肯大言相欺?那贱民早已设下圈套,聚集得数十刀斧手在此。就等着殿下口出孟浪之言!”
“孤王乃货真价实的殿下,只要揭穿得那贱民身份,就不信众士卒敢朝孤王动手!”
“殿下此言原是有理。奈何当时又是什么场合?众人又岂容殿下长言?只恐殿下揭露之词尚未出口,而刀斧早已临头!微臣之所以冒失者,正为救你我性命,不得不如此而已。”
柴宗让沉吟了一下,稍微有点明白过来了。
皇家的威严又岂容侵犯?众人只当那贱民是真殿下,自然不肯容忍他人质疑。一旦开的此例,以后上下尊卑还要么?
“即便此话有理。然则先生此次与其密议,又为何事?莫不是将孤王卖与彼等?”
“殿下休要多心!微臣之所以前去者,不过是欲安其心罢了!我等与那贱民相争,于我等而言,只要再无变故,拖延到今夜便可李代桃僵。于那贱民而言,只有杀尽我等一干知情人方能鸠占鹊巢。彼求变,我等求不变,优势尽在我手。微臣前往厚颜前往商议,只为以安其心,求得不变。”
“既求不变,先生何以日前将假冒金策玉碟赠送于彼?”
这个李守忠还真解释不清,只得胡乱应付:“不过是先设一招后手,以为应对罢了。”
其实也不是解释不清,而是殿下肯定听不懂。
那贱民要弄死自己一干人等,无非两种办法。
先擒拿在手,再加以罪名杀之,或者猝然杀之。
换句话来说,一种是先审后杀,一种是先杀后审。
这贱民又没有什么势力,唯一的机会,那就是借韩德之力。
韩德这人虽然忠诚,却也不是愚忠。
哪怕那贱民一再挑拨离间,只要没被逼到极处,例如今日大典之上这种情形,韩德必然不肯乱了法纪。
那贱民下令让韩德将自己众人抓起来,韩德肯定执行。
让韩德将自己众人不管不问直接斩首,韩德必定死谏。
自己献上假的金策玉碟,防备的正是第一种:先审后杀!
一旦被那贱民下令擒拿自己,便可以此为后手,证死那贱民的假冒身份。
至于第二种,先杀后审,倒是可能性极少。
还是那句话,只要自己同殿下不要做得太过分,韩德必然不肯动手。
自己倒是无妨,明枪暗箭都能防备,怕就怕殿下再一次冲动。
关键问题是这殿下不仅冲动,还不怎么听人劝。
李守忠又一次拜伏下去:“殿下,为人君者,当有包容天下之心。些许屈辱又算得甚么?文王拘于羑里,夫子厄于陈蔡,又几曾损其清名?若是微臣所料不差,这贱民自当再以言语激于殿下。愿殿下勿听勿闻,只要拖到今夜三更,我等胜数已定。”
柴宗让不以为意,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