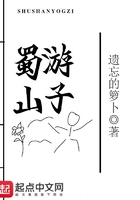1
天快擦黑时下起雨来,宅第四周的果园里一片单调、喧闹的雨声。五月青葱的草木经雨水一淋散发出的那种甜滋滋的沁凉的气息,打客厅一扇敞开的窗户内飘进屋来。春雷在屋顶上空隆隆作响,每当淡红色的闪电劈开天空时,雷声就骤然增大,发出哐啷啷的炸裂声,漫天低垂的乌云使得天光晦暝。不一会儿,雇工们就打田里回来了,纷纷在板棚前卸下沾满泥巴的犁耙,身上的高加索式上衣已经全都被雨水浇湿。后来牲畜也赶回来了,顿时整个庄园内响彻了哞哞的牛叫声和咩咩的羊叫声。村妇们掖起裙摆,光着两只闪闪发亮的雪白的脚丫,踩着青草,满院子地奔跑,驱赶着羊群;有个牧童戴着一顶大帽子,穿着一双破烂的树皮鞋,在果园里撵一条母牛。母牛噼里啪啦地冲进茂密的树丛,那个牧童也一头钻进了被雨水浇得湿淋淋的牛蒡丛中……天黑后,雨止了,可直到此刻,不见父亲回来,他还是大清早上田里去的。
家里就我一个人,可我一点也不感到冷清,因为我刚刚尝到做女主人的喜悦,刚刚过上中学毕业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弟弟巴沙在武备学堂学习,姐姐阿纽塔还在母亲生前就已出嫁,居住在库尔斯克。我独自和父亲一起,度过我乡居的第一个冬天。我那时健康、漂亮,连自己看着也情不自禁地要啧啧称赞,我甚至还欣赏自己在屋里跑来跑去处理家务或者差遣下人办事时那种轻盈的步态。在做家务事时我总是哼着自编的曲子,而且深为其感动。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容貌身姿,我就会不由得得意地微笑起来。我觉得我穿什么衣服都合身、都好看,虽说当时我的衣着是十分朴素的。
雨刚停,我便围上披肩,提起裙子,跑到牛栏里去,村妇们正在那里挤奶。几滴残雨打空中掉到我没戴头巾的脑袋上,但是高高地悬挂在院子上空的轻飘飘的雨云已在散开,而且当地五月的晴夜所特有的那种空明银白、朦胧奇特的幽光,已飘飘忽忽地弥漫在院子里了。从旷野里拂来一阵阵潮湿的青草的清香,同下房里炉烟的气味掺杂在一起。我顺路到下房里去看看,只见年轻的雇工们穿着白色的麻布衬衫,围坐在桌子四周,端着碗喝汤。他们一见到我都站了起来。我走到桌旁,因自己跑得气喘吁吁而笑了。我问他们:
“爸爸在哪里?他去过田里吗?”
“去过,看了看就走了。”好几个人同时回答说。
“乘车还是骑马走的?”我问。
“乘轻便马车,同西维尔斯少爷一块儿走的。”
“怎么,西维尔斯少爷来了?”我惊讶得脱口而出地问。因为我没料到他会来,但我及时意识到问这话是不相宜的,便点了点头,快步走出下房。
西维尔斯已从彼得洛夫军事学院毕业,正在部队服役。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大家就戏称我是他的未婚妻。为了这个,他当时看到我就老大不自在。可我从此却常常把他当作未婚夫看待。八月里他去团队途中,特意来我们家,穿着一身士兵的制服,佩戴着肩章,像所有的志愿军人那样,眉飞色舞地讲述一个小俄罗斯司务长是怎样讲解“条令课程”的。打那时起,我便决意要做他妻子。他谈吐风趣,脸晒得黑黑的——只有前额的上半部没被晒着,白得触目——我觉得他可爱极了,看着就满心欢喜。
“这么说,他请假回来了。”我激动地想,不消说,他是为我来的,这使我又喜又怕。我连忙回屋去给父亲准备晚饭,可我一踏进仆人室,就看到父亲已履声橐橐地在饭厅里踱来踱去。不知怎的,我此刻看到父亲大有喜出望外之感。他的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上,络腮胡子乱蓬蓬的,长靴子和茧绸上衣沾满了泥巴,可是我却觉得他现在这副样子正是男性的美和力量的化身。
“干吗黑灯瞎火的?”我问。
“塔塔,我这就要睡觉了,”他回答说,仍然唤我的乳名,“晚饭不吃了,我累坏了。再说,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现在通宵都是霞光,用庄稼汉的话说,晚霞跟早霞串在一块儿了。”然后,他漫不经心地加补说:“不过,牛奶我还是要喝的。”
我伸手去点灯,可他却摇了摇头,把盛牛奶的玻璃杯举起来,朝着天光仔细地察看了一下里边有没有苍蝇,然后才一饮而尽。夜莺已在果园里婉转啼唱,从饭厅的三扇西窗和北窗里,可以看到在春日线条柔和优美的紫罗兰色的浮云上边,一碧如洗的夜空向着远方伸展开去。无论地下还是天上,万物都显得飘忽不定,蒙着似轻纱一般淡淡的夜色,显得分外柔和。在不会熄灭的朦胧的霞光下,一切都清晰可辨。父亲问了我好些家务上的事,我平静地一一做了回答。可是当他突然说起明天西维尔斯要来我家时,我只觉得我的脸烧得通红。
“他来干吗?”我讷讷地问。
“来向你求婚。”父亲不自然地微笑着回答,“没说的,是个和善、英俊、聪明的小伙子,会成为一个体贴你的好当家人的……我们连谢媒酒都喝过了,要把你送掉了。”
“别说这种话,好爸爸。”我讲道,一阵泪水涌至我的眼眶。
父亲久久地端详着我,然后吻了吻我的额头,转身朝书房走去。
“早晨脑袋瓜要比晚上聪明。”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加补说。
2
正在酣睡的苍蝇,叫我们的谈话声吵醒了,在天花板上嗡嗡地轻声抱怨了一阵,渐渐又沉入黑甜乡。自鸣钟嘎嘎地响了起来,钟上报时的布谷鸟嘹亮而忧伤地啼了十一下……
“早晨脑袋瓜要比晚上聪明。”我想起了父亲这句令人宽慰的话,心头重又轻松了。但不知怎的,在感到幸福的同时,却有几分怅惘。
父亲已经睡着,书房里早已没有一息声音,整个庄园也都已入睡。在雨霁之后的静夜中,在夜莺袅袅不绝的啼啭声中,回荡着难以言说的欢乐,而在深远朦胧的霞光中则翱翔着难以捉摸的美好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收拾饭桌,生怕弄出声音,踮起脚尖从饭厅里进进出出,把牛奶、蜂蜜和黄油放进过道里那只冰冷的炉灶里,把餐具和茶具用餐巾盖好,然后就回我的卧室去。这并未使我跟夜莺和霞光分开。虽然我卧室里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可我的卧室是和会客室毗连的,会客室的门开着,隔着会客室,我可以看到荡漾在饭厅里的幽幽的霞光。至于夜莺的啼啭,则整幢宅第内哪儿都可以听到。我松开头发,在床上坐了很久,考虑着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后来我把两肘支在枕头上,合上眼睛,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时我清清楚楚地觉得有人俯下身来对我说:“西维尔斯!”我打了个寒战,惊醒了过来,我就要嫁人这事使我周身发冷,感到一种甜蜜的恐惧……
我迷迷糊糊地静卧了很久,什么也不想。后来我恍惚觉得我已经出嫁,庄园里就我一个人,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丈夫从城里回来,走进宅第,在过道里轻手轻脚地脱去上衣,而我赶在他进卧室之前,也轻手轻脚地走到房门口去迎候他……他见到我是那样的快活,把我高高地抱了起来!想到这副情景,我觉得我已坠入情网。其实我对西维尔斯并不怎么了解。在我的想象中跟我共度这个充满柔情蜜意的初恋之夜的那个男人,一点儿也不像他。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想象中的那个男人就是他。我几乎有一年没同他见面了,是夜使我觉得他更漂亮,更可爱。卧室里静静的、黑洞洞的,我躺在床上,神驰天外,失却了现实感。“没说的,他英俊、聪明……”于是我微微地笑了,隔着合上的眼睑,凝目望着眼前的一片黑暗,只见什么地方漂浮着亮晃晃的光圈和人的脸庞……
我感觉到夜已经很深。我想起了我的贴身婢女:“要是玛莎在家就好了,我上她屋里去,两人可以一直聊到天亮……”可随即我又想道,“不,还是我一个人静静思索的好……等我出嫁时把她也带去……”
饭厅里有样什么东西怯生生地咔嚓响了一下。我警觉地睁开眼睛。只见那里比刚才要暗多了,我周围的一切和我的内心也都随之发生变化,过起另一种生活来,那是一种独特的夜生活,是一种在早晨所无从索解的生活。夜莺已不再啼啭,只有今春栖息在凉台附近的那一只,还在慢条斯理地舒展着歌喉。钟摆在客厅里谨慎地、从容不迫地、准确地摆动着,宅第内索寞的氛围给人一种紧张感。我打床上欠起身,倾听着每一息声响,感到自己已完全被这个专门用于接吻、用于偷偷拥抱的神秘的时刻所主宰了,此时此刻即使是非分之想,即使是不着边际的奢望,在我看来也都是合情合理的。我突然回想起,西维尔斯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过,哪天夜里他要上我家的果园来同我幽会……要是他并非开玩笑呢?要是他正在慢慢地、悄无声息地向凉台走来呢?
我两肘支着枕头,凝神注视着窗外飘忽不定的清幽的夜色,想象着我怎样打开通向凉台的门,怎样用刚刚能听得见的柔声细语向他倾吐情愫,怎样甜蜜地失去意志力,听凭他带着我,踏着林荫道上湿漉漉的细沙,走向花影婆娑的果园深处……
3
我穿上鞋,披上披肩,蹑手蹑脚地走进会客室,在凉台门前站停下来,心怦怦狂跳。直到我确信除了自鸣钟均匀的嘀嗒声和夜莺余音悠悠的啼啭声外,宅第内没有一息声音,这才轻轻地转开凉台门上的钥匙。顿时间,响彻整个果园的夜莺婉转的啼声分外嘹亮,那种由寂静引起的紧张感消失净尽,胸膛舒展地呼吸着深夜湿润馨香的空气。
北半天上堆满了乌云,使霞光显得昏沉朦胧。我沿着两旁全是小白桦树的长长的林荫道,踏着路上湿漉漉的细沙,向果园的尽头走去,在那儿有一个由杨树和榆树掩映着的丁香蔓生的凉亭。周遭是那样清幽寂静,以致可以听到从低垂的枝头上偶尔滴落下来的雨珠声。万物都已入睡,沉醉在各自的梦乡中,只有夜莺还带着倦意唱着它们甜蜜的歌。在每簇树荫下我都觉得有个人影,我的心不时激动得仿佛要停止跳动,后来当我终于步入黑洞洞的凉亭,一股温馨的气息朝我扑鼻而来时,我几乎已经深信马上就会有个人过来悄无声息地把我紧紧地搂入怀中。
然而没有一个人。我激动得浑身发颤,伫立在那里谛听着榆树睡意蒙眬的絮语。后来,我坐到湿漉漉的长椅上……仍然在期待着什么,不时朝破晓时分天边吐出的鱼肚白迅速地瞥上一眼……我久久地感到有种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在我周围荡漾,这种幸福是可怕的、巨大的。我们每个人一旦跨过生活的门槛迟早都会与这种幸福相遇。这种幸福突然触摸了我一下——也许它这是做了应当做的事:触摸一下,随后悄然离去。我至今记得当初郁积在我心头的缱绻缠绵的情话,使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靠在被雨水打湿的白杨树上,像是在倾听什么人的抚慰似的,凝神谛听着树叶时起时伏的絮语,我默默地流着眼泪,我觉得幸福……
我潜心地观察着黑夜向黎明的奇谲的转变。看到苍茫的夜色怎样吐出白光,还透过樱桃树林遥遥地看到浮游在北边天陲的一缕纤云如何染成了红霞。晨寒料峭,我用披肩裹紧了身子,眼看着天空越来越明亮、深远、辽阔,金星像一滴明净、晶莹的水珠,在空中熠熠闪光。我已坠入情网,爱上了一个什么人,我的爱情无所不及,充溢在沁凉的寒气之中,充溢在馥郁的晨曦之中,充溢在绿荫森森的果园清新的气息之中,充溢在这颗晓星之中,充溢在万物之中……可就在我心驰神往之际,却传来了运水马车刺耳的嘎嘎声,马车从果园外驶过,向小河而去……后来,不知是谁用刚刚睡醒的喑哑的嗓音喊了一句什么话……我连忙悄悄地溜出凉亭,快步走至凉台,轻轻推开凉台门,踮起脚尖,跑进我温暖的黑洞洞的卧室……
西维尔斯一大早就在我们的果园内用猎枪打寒鸦,我却以为是个什么牧人闯进了宅第,在挥舞长鞭。但这并不妨碍我沉沉睡去。等我醒过来时,饭厅里已有人在谈话,还有杯盘相碰的声音。后来西维尔斯走到我房门口,大声地喊我道:
“娜塔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多难为情呀!睡懒觉!”
我的确感到难为情。我感到难为情,因为我要去见他,因为我要拒绝他的求婚——此刻我已经断然地拿定了这个主意——于是我匆匆忙忙穿好衣服,朝镜子里瞟了一眼我苍白的脸蛋,同时以开玩笑的口吻客气地说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声音是那么轻,他大概没有听清。
1902~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