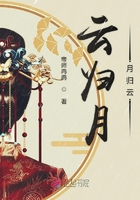檀香继续抽抽涕涕地说:“先前,孙公兴公的一个家婢与家奴私奔,两个人已经跑到泸州了,还是被人给抓了回去。后来……后来……那个婢女被判了凫水之刑,男的被乱棍打死……倘若被人知道我与浮生有了私情,无论夫人是否愿意成全我们,我们都难逃一死的……”
“凫水是个什么刑罚啊?”
檀香一边发抖一边说:“就是把人倒吊在水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淹进水里再拉出来,淹进水里再拉出来,反复几十回,直到那人端气。”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果然是万恶的旧社会,发明这个刑罚的人,肯定是个变态。
奔者,私通也。私通这种事情放在现代,一般指有妇之夫或是有夫之妇有了外遇。从道德和情感上来说,这样的人渣自然是怎么折磨他都不为过。可在东晋这个时候,只要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之间哪怕是两情相悦一下也是大逆不道的。这种情况下,女方往往还会被贴上“下贱”的标签,有了这样的标签,这个女人基本就算是完了。任何人都可以轻贱、欺辱她。更何况像檀香这种自幼就被卖给人家做奴的人,原本就没有人身自由,一旦与男子交好,就会被视为给主人家蒙了羞,总是要让她人尽皆知的惨死,才能保住主人的名声。
我在东晋生活了这么久,文化糟粕也接受了不少,可仍然想不明白为什么你情我愿的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我正要为檀香愤愤不平一番,却被她下面的一句话惊到说不出话来。
“夫人,您和四爷的事情,也万不可说的。”
檀香的声音很轻,但在我听来却犹如一声重雷。我在她眼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怒道:“我和他清清白白,你这些话从何说起?!”
檀香从未见过我发这么大的火,连连磕了好几个头,求饶道:“我不该胡说!不该胡说的。”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言可畏”这四个字的可怕之处。可是,我对她怒一场又能改变什么?她也是好心提醒。我拉起檀香,正色地告诉她,我与谢万之间什么都没有,我想离开也绝对不是因为他。她愣愣地点了点头,我实在看不出来她究竟信没信。于是,我又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檀香皱着眉,坚持不懈地不让我走:“夫人您即便放得下老爷,您放得下瑶少爷和琰少爷吗?他们还那么小,您忍心让他们没了亲娘吗?”
我略略想了一下,也许会有些舍不得。可我毕竟不属于这里,我留在这里一切都是错的。我想只要我回去了,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许再过几年,也许根本用不着几年,只肖几个月,我就连这里的花草树木都记不清了,再过几个月,我就连这里的人也记不分明了。往后我老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恐怕也只会当做是一场南柯大梦罢了。
几天后的晌午,谢安带着谢瑶和谢琰来看我。之前,我因为生病,没顾得上这两小只。后来,我又因为计划着要走,怕和他们待在一起久了会舍不得,于是故意疏远。仔细算起来,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过他们了。谢安牵着谢瑶,谢瑶牵着刚会走路的谢琰,他们三人就这么整齐地排在我跟前,可爱得就像一组俄罗斯套瓷娃娃。
我心里当然欢喜,笑问他们:“你们怎么来了?”
谁知稍微大些的那只小娃娃,突然就朝我飞扑过来,一边扑一边哭喊:“瑶儿……不想……娘……生病。娘……不要……生病。”
最小的那只也不甘示弱,左摇右晃地挪过来,紧紧住我的腿,因还不大会说话,急得咿呀乱叫:“不...走。”
我的心顿时就化了,一手抱将起一个,给这个擦擦眼泪,给那个擤擤鼻涕,好一阵手忙脚乱。我安抚了好一阵,两只方才安生下来,转头去看谢安,他居然盈盈笑着,袖手旁观。
我酸了一句:“安郎隔岸观火,倒是自在。”
谢安没有搭腔,自顾自地给自己找了个座儿,继续笑盈盈地看着我手忙脚乱。
谢瑶从怀里掏出了被揉成一团的手帕,凑到我跟前,小心翼翼地打开。我一瞧,手帕里竟然包了两块桂花糕。
谢瑶拈起一块桂花糕来就往我嘴里送:“娘,瑶儿特意带来给您吃的。”
我瞟了谢安一眼。既然他晓得,我也不必再装作自己不喜欢吃,于是一口就叼了过来。谢琰见了,伸手就要去抓另一块。谢瑶拍掉他的手,正色道:“这是给娘亲的!”谢琰撅起小嘴,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哥哥,眼中还泛着泪光。谢瑶又心软了,仰着头央我:“娘,我给弟弟吃小半块儿,可以吗?”我笑着点了点头。谢瑶于是掐了一小块桂花糕送去谢琰的嘴里。谢瑶砸吧了两下嘴,两撇淡淡的小眉毛忽的一皱,将糕全部呸了出来。我一看乐了,指着谢琰冲着谢安乐道:“这个像你。哈哈哈哈哈哈。”
谢安无奈摇了摇头,仍然没有说话。谢瑶急了,埋怨谢琰:“这么好吃的东西,你怎么给吐了!”我顺势将剩下的桂花糕往他嘴里一塞,“只咱们俩个喜欢吃,多好,没人和咱们抢。”
明月初升的时候,小小谢已然在我怀里睡着,小谢一边嘟囔着:“娘……不在,爹就……罚我……抄书……”一边抱着我的膝盖“磕头”。大谢同志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走过来帮我抱走了谢瑶。
我看了一眼困得说胡话的谢瑶,劝道:“别折腾他们了,就让他们在我这儿睡吧。”
谢安笑道:“也好,他们这几日想你想的紧。”说着便手脚利落地帮我将两只小的安置在了床上。
那一夜,我看着身边那两张熟睡的小脸久久不能入眠。檀香的话似在我耳边盘旋。
我真的能放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