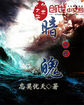我从床山醒来,下午四点,手机上好几条信息,是公司里催稿来的。
脑袋里一片涣散,是正在努力要整合起来的难受,嗓子扁桃体毫不客气地疼。眼下是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被子、床单,还有被子上无需怀疑的自己的气味,看窗帘,透进来黄光、热度、潮闷,这样的光线让我又警觉又害怕。
天气一天天地热,我对一切都倦怠了起来。换季的大风把我的世界吹得找不到边界,只听到树在整夜的摇晃、翻滚。昨天是我本职的工作,要交的稿子的deadline,最后交稿日,昨天下午写完后就忘记了。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把该发的邮件发了,好让自己继续倦怠。
我换了个地方躺,由房间转移到书房的沙发上。沙发上铺上了席子,凉意沁入我的毛孔,皮肤对这样的凉意渴望着,也抵触着,我明白了,我在发烧。
小兰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她愿意来,我还让她给我带点吃的,我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承受孤独。
小兰的头发看起来很不一样,新剪了个刘海,发色也重新染过了,棕黄色,有那种跳跃的光泽,像在阳光下,还带着微微的卷,她说这是她自己卷的。在我看来,刘海、发色、和卷,都不赖。
“你爸妈呢?“
“出去旅游了。“
“先吃个三明治,垫垫饥。“小兰从她的包里拿出三明治给我。
“新包?“我问她。
“是啊,鲶鱼包,让朋友从韩国带买的,比国内便宜两三千呢。“小兰说,“你发烧要吃得清淡点,要煮点粥,再煮点姜汤,我用一下你们家厨房。“说完她径自去了厨房里。
我在沙发上躺着,懒得去看她,也懒得让她别忙活。我头脑昏沉,四肢沉重,内心倦怠,正是适合被人照顾的时候。
不知道方晓刚有没有生病。
厨房里传来水龙头和锅子的声音,接着又啪啪几下拍姜片的声音。虽然发烧躺着,但是可以什么都不用干,躺着等待有人来照顾我。我不挑食,所以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给我喝什么我就喝什么,既然是躺着,也就不用烦恼穿什么出门,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既不用干活,也不用选择,这才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煮粥和熬姜汤需要时间,小兰来看我。她对我说:“你头发里有草。“
“昨晚没洗头,回家太晚就冲了冲水。“
“你洗个头吧,我来帮你洗。“
“这倒真不用,我洗澡的时候,顺便洗个头。“
“你昨晚跟谁一起吃晚饭了?“
“方晓刚。“
“你招得挺快啊。“她眨了眨眼。
“这没什么,不就吃顿饭嘛。“
“你还是洗个头吧,头绿了不好,哈哈。“小兰笑着说,“我要去上课,要走了。“
“上什么课?“
“画画,刚报的班,粥跟姜汤,我会在走前关火,你有食欲的时候自己吃一点。“小兰挎上她的鲶鱼包走了,我听见啪嗒啪嗒两声,随之是门砰地一声。她走后,我又回到了孑然一身,自力更生的环境,这让我感到怅然。
我知道我头发里的是水草。
昨晚我突然想往湖里跳,就跳了,风一吹,就受凉了。
我和方晓刚吃了顿晚饭。
他问我是否吃榴莲。我吃榴莲。
于是我们在一家连锁的快餐店里吃了榴莲披萨。
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可以看见人家身上漂浮物的事情。
“你能不能看见我身上的漂浮物?“他问我。
“我看见过一次。“
“是什么样的呢?有形状吗?“
“没有形状,也没有样子,是一种光与人的关系,我进行一种读取。“
“你说过你会误读?“
“会误读,但是大部分时候只管读取就行了,因为我无法证明我读的是对的,也无法证明我读的是错的。“
“那我的呢?“
“你现在还去教堂吗?“我转移了个话题。
“偶尔去过,但是很久没去了,说起来我们吃晚饭后去那附近走走?“
“好啊。“
又是在湖边,苏州就是这样。
方晓刚谈起他偶尔会来教堂是为了还愿,他不确定基督教里有没有这种说法,但是他骨子里有这样的传统。教堂红白相间,就算是晚上看起来还是秀美光鲜。这里我来过一次,是陪人来拍婚纱照。十字架矗立在湖水中,巨大的耶稣像在广场上张开怀抱。
他谈起了很多事情,他跟他爸妈的关系,他爸爸跟他爸爸朋友的关系,他爷爷跟他外公的关系,还有他的困惑,他困惑着人与人的关系。正如我读取着光与人的关系。他自顾自地讲,我跟他沿着湖走。他虽然看起来很瘦,但其实肚子上隐隐地突起。走过一座树间的拱门,他走在前面,我发现他的小腿也很结实,他穿着一条米白色棉麻的裤子,小腿上有种向外的鼓鼓的力量。
我们在湖边坐下,风云流动,可是空气里闷热潮湿,我觉得困乏,心不在焉。我恍惚想成为方晓刚,顶着一头短短的卷发、外突的后脑勺、外突的肚子、向外的鼓鼓的小腿,在风里坐着,闻见湖水传来的味道,湖水的味道跟太湖的味道没什么区别,嘴里仍然有榴莲的余味,还能闻见从我头发上传来的味道,我的洗发水是茉莉苹果味。而事实上,我总是问到方晓刚身上的味道,那味道很大程度来自他家的衣柜,若隐若现。
我问方晓刚:“你会不会游泳?“
“我会啊,蛙泳、仰泳,但是不会蝶泳。“
“我不会游泳,这水深吗?“
“不知道。“
“你说从这里跳下去会怎样。“
“你又不会游泳。“
我开始把鞋子脱掉,又脱掉了T恤衫,我看着湖水想往下跳,心里害怕极了。但是我假装自己不害怕。我假装自己是方晓刚,会蛙泳还会仰泳。我还假装自己很坦率,穿着胸罩站着不是什么害羞的事情。周围是紧密的矮树丛,极目四望,那是一片沉静的水域,连着黑夜,没有光,也没有星星。风吹着我的身体,像是在往我身上糊上一层层的水汽,黏腻。右手边不远处的十字架,是白色的,很惹人注目,它也在水里。我向它眺望着。我在从额到胸口画了个十字架,然后双手合十,举高,半蹲,起跳。
“上帝保佑。“
啪啦地拍在水里。
水很冷,冷飕飕地侵入我的身体,很快在全身走遍,然后把我包裹起来,无处可逃。我想就此消失掉,偏偏那种冷的感觉不断提示我身体的形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重,应该减肥,不然就不至于冷这么一大块。瞬间悲从中来,又感到悲极生乐。来自浮力,浮力使得我摇曳起来,我以为这叫轻盈,轻盈得有点痛。我意识到,不管我在哪里都无所适从。
哐啷啷,周围是水花、气泡,我像一颗被泡在汽水酒里的梅子。我的脖子被勾住了,我整个人被捞着站了起来,还是很轻盈。
“水很浅,你站着。“
我站着,水确实很浅。原来方晓刚也跳进来了。他没脱衣服,湿透了,我知道我也是。我看着他笑了,他也笑。
方晓刚脱下衣服,拧干,擦了擦头发,他头发真的好卷。
但愿这一切都没人看到,可是我看到路边有监控。但愿我们不在监控的范围,真像傻子啊,精神出了问题的人。如果要我解释说我们不是神精病,那就是端午节快到了,想起了屈原投江,纪念慷慨悲歌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