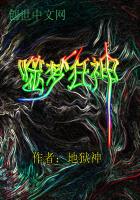“你这侄儿的事情办得不错,是个人才,待此次事了,让他进厂里办事吧。”一个沙哑的中年男人的声音突然传来,正是熊雠的声音。
懋修心中一喜,知道自己之前听到二楼还有一个人的声响,尽管那人没有说话,但走动的声音已足以暴露在懋修的耳朵里了。既然此人能与这邓娘子密会于此,那必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果然没有料错,且听听他们还会说些什么。
那女人大喜连忙拜谢道:“多谢先生抬举,这对我邓家是莫大的恩典,奴家真是不知如何谢您了。”
“无需如此,只要你尽心办事便是谢我了。”
“奴家一定为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只是这崔景贤在此情况下,突然与别的堂口起了冲突,莫不是中间有什么蹊跷?”熊雠自言自语道。
那妇人心中一惊,思量了一番后说道:“我那侄儿虽然年轻,但心思还算细密,听他与王三的来往经过,可见那什么威武堂必是想趁火打劫,惹恼了崔景贤,这才有了这一出,不过先生若不放心,待明日我再派人打听打听。”
熊雠闻之,亦觉有理。“不用,只要窦山在我们手里,任他崔景贤再怎么跳腾也无济于事,这次若不是黑五机警,查得窦山这老小子竟敢撕私掉粮包,先下手抓了他,否则让崔景贤先找到他,我们可就要前功尽弃了,你可要把他看好了。”
“先生尽管放心,那窦山被关在密室之中,一日两餐都是奴家亲自送的,除奴家之外也就只有先生您和贵属黑五兄弟知道,别人是决计找不到的。”那女人得意洋洋的说道。
“好,且先关着,待我得空了再审,你下去吧。”
女人“诺”了一声便下楼走了出来,轻轻掩上门,这才转过身来。但见她修眉微颦,沉思片刻,就悄然向旁边一所偏院而去,那不是她来的地方。
懋修视力极好,此时院中光线虽弱,却也清楚地看到妇人脸上的神色喜悦渐退肃色渐生,脚下步子越走越快,心中一动,忙示意紧跟其后。
只见那夫人来到一所高大结实,门窗紧闭的房屋之外,私四下里看看之后,这才掏出钥匙打开门上的铜锁走了进去,懋修早已觉察,此屋周围并无护卫,便堂而皇之的来到屋外,借着虚掩的门缝,将那妇人的举动看了个清清楚楚。
只见她扭动了某处机关,放在南墙之外的博古架就悄然滑向一旁,露出仅供一人低头可入的小门,门内有微光透出。妇人低头走了进去,博古架又缓缓划了过来,室内立刻昏暗下来,眼看到小门就要完全关上了,懋修身边的阿岩如电闪般跃了进去,一掌便抵住了木架。
懋修这才松了口气,赞许的看了看阿岩,阿岩心中得意,脸上却不显分毫,毕竟做事高调一些没什么,做人还是要低调些好。
这时妇人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窦舵主现在思考的怎么样了?那些漕粮现在藏在何处?”
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个虚弱的男人的声音应道:“邓妈妈你好狠的手段,想不到我窦山七尺男儿,却栽到在你这毒妇的手里。”
听到此懋修知自己所料不错,这密室中关押的果然是失踪的窦山。
三人心中大喜,今晚夜探翠红院,果实不虚此行。
那邓妈妈不怒反讽。“窦大舵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您仁义,不也背叛了待你如弟的郑大当家吗?”
听到此言那窦山惨了狂笑,“哈哈哈,这真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罢了罢了,我窦山落得这般下场,也是罪有应得,至于漕粮下落,你去告诉熊雠,我至死也不会告诉他的。”
之后任那妇人如何威逼利诱,窦山都是不发一言。无奈之下,妇人只好离去,阿岩忙松开手来,任那木架关上,之后三人快速的藏匿在院中隐蔽之处。
那邓妈妈锁好门,怒气冲冲的离去之后,懋修言道:“天予不取必受其害,既然我们发现了窦山的下落,就不能空手而归,免得夜长梦多。”
几日下来,景贤对懋修早已奉若神明,毕竟他来苏州月余,却是一筹莫展,而懋修才来了几日,事情不仅明朗了,连漕粮的难题也解决了。此时对懋修的任何决定,他都会言听计从。而阿岩更不用说了,她在懋修未说明之前便已打开了铜锁。是打开,不是撬开。开锁这种小手段,对魔教圣女而言自然不在话下了。
懋修进得屋来,稍稍观察了一下,便瞅准一个铜器,抓握起来果然纹丝不动,向左拧动没反应,向右扭动果然旋转起来,博古架再次打开。
三人鱼贯而入,拾级而下,穿过拐角,便来到一处密室之中,室中有床,那窦山背面而卧,有人进来也,不曾转身,更不言语。
懋修主动说道:“故人来访,窦舵主何以背身而卧,可是我等来的太唐突。”
那窦山果然清醒着,他冷笑一声。“此处是囚牢,不请自来者,皆是恶客,难道还要邓某以礼相待?更何况阁下的声音陌生,何谈故人?”
“所谓恶客,那是心怀恶意之人,我等三人对舵主却不见得就有恶意,至于故人之说,窦舵主不妨转过身来见一见,自然就明了了。”
窦山默然,这才缓缓转过身来,脸色苍白,神情憔悴,浑浊的目光从三人脸上扫过,无一人识的得,脸上不觉满是嘲讽不发一语。
懋修看了看景贤,景贤自见了窦山,恨意早已涌上心头,只是他对懋修敬重,不敢私自接话,这时见懋修示意,便狠声说道:“窦山,你不识得我现下的模样,但可听得出我的声音?”
窦山闻声眼睛瞪得老圆,结结巴巴的说道:“可是…可是二当家景贤?”
“原来窦舵主还记得我崔景贤,我还以为窦舵主攀上了高枝,早已忘了漕帮上下了。”景贤冷嘲热讽毫不留情。
窦山苍白的脸上涌起一片绯红,凄然一笑。“二当家是我看着长大的,又怎会不记得你的声音,只是我已铸下大错,二当家此来,是取我性命的吧,那便拿去吧。”
景贤想到自己当年幼小之时窦山也曾扛着他逛街市买玩具的场景,不觉有些恻然,可再想到师傅因他入狱,漕帮险遭大难,又恨上心头,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不知如何言语。
懋修见此情此景,便接过话来。“窦舵主,你既知自己犯下大错,愧对漕帮,其罪万死难除,但你究竟是死是活,却不是我等能说了算的,还需郑大当家决断。更何况玄远道长还为你求了情,现下你还是随我们出去,至于罪过容后再议。”
景贤知道懋修说的在理,也不反驳。“窦山,便如我三哥所言,出了此地,回到帮里,一切听凭师傅的决断。”
要说这窦山也并非群凶极恶之人,只是被一时的名利迷了眼睛,这才犯下大错,听到这里想到过往种种,更是羞愧难当,恨不得一头撞地而死,只可惜那邓妈妈给他下的毒药不仅让他午时三刻之时痛彻心扉,更让他全身疲软提不起劲来,此时连翻身坐起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自杀了。想到这里不觉万念俱灰,情知自己所作所为百死莫赎,倒不如就死在这里,也免得见了大当家和帮中众兄弟无颜以对。
放下了生死的窦山,不觉恢复了昔日的豪情,神情间不再颓丧。“二当家,窦某今日落得这般下场,也是罪有应得,万不敢再让二当家受累,也实无颜面再去见大当家和帮中兄弟,刚刚听闻这位壮士提到玄远兄弟的名号,想来漕粮的下落你已知晓,也算恕了我几分罪过,其余的就让我来世变成漕帮的一条看门狗,再行弥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