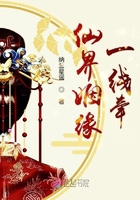“站住!你们是哪里的兵,岂敢在此放肆?”
暮色四合。天云山的半山腰上,不知怎的来了一大群穿着亮银色铠甲,手持火把的兵。漫长的队伍顺着山间小道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像是为群山盘上了一只巨大的火龙。在他们的前方,是一座朱红色的山门,墙上“未央阁”的匾额虽已褪色,却格外亮眼,而就在这貌似破败的匾额之下,站着一位绛色衣冠,须发皆白的老头。
“你们要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老夫就再提醒你们一下:这是敕造未央阁,是先皇赏给内阁首辅大臣左文忠左大人的别墅,也是当朝左都御史左星的私宅!谁敢乱来,满门抄斩!”老者指着头上的大匾,声色俱厉地喊道。然而在场的士兵并没有后退的意思。
“来了,来了!”忽然只听见人群里有吵嚷声。远远望去,一顶细软小轿在几名轿夫的簇拥下从山下箭步奔来,挤过山门前的人群,径直停在老者的面前。里面的人不下轿,也不抬帘子,就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腔调温温吞吞地说:
“圣上有旨:左都御史左星,风闻言事,祸乱朝纲,常思己之清誉,以误国家之急。内监黄门,朕之肱股,尔等逆天而行,是直欺君罔上,大逆不道。著:左星凌迟,族中男皆处死,女没为官奴。有抗者立斩。钦此。”
“你……你假传圣旨!你们这些阉党,趁着皇上不上朝,就作威作福,残害忠良,是何居心!”老者的脸上已经变了颜色,他一边高喊一边后退,然而还没走出三步,轿子里的人便一把掀开帘子,大踏步走出来,掏出一把镶金边的西洋手铳,冲着老者“咣”的就是一枪!
“小姐,小姐……”伴随一声巨响,老者应声倒地。他孤独地躺在地上,像鱼一样在腥甜的液体中扭动着——他的喉咙被打出了一个大窟窿。
“还愣着干什么?都给我杀了!”开枪的人把枪丢在地上,拔出身边士兵的刀,一声令下,所有士兵便风一样地涌进来,只几下便撞开了狭小的山门。
“什么声音?刘叔,刘叔!”此时此刻,阁楼上的女孩坐不住了。她起身就像往楼下跑,却被门口的侍女一把拦住。
“不行小姐你不能下去!现在外面很危险!”侍女跪在女孩的脚边,却被女孩一脚踹开。
“你混蛋!难道咱们要在这里等死吗?”她抓起一把墙上挂着的腰刀就往楼下冲。然而没走出几步,女孩便被几柄寒光闪闪的利刃逼得节节后退,一直退回到阁楼之上。方才还在山门的兵,不知用了什么神力,须臾便逼将上来。
“哎呀真香。”女孩喃喃道。
“过来,姑娘。”最前面的人正是领头的人。他眯缝着浑浊的双眼,脸上发出狞笑。即使他的官服再亮眼,也丝毫掩盖不了新靴子上的血迹。
“你想干什么!”女孩吼道。
“送你去见你爹。”男子带着兵越逼越近。
“放心,一点也不疼。我下手很有分寸的,不信你看。”男子的声音阴郁而冰冷,还带着蛇吐出信子沙沙声般的毛边。“不,不,不要!小姐救我!”方才地上的侍女,转眼已被拉到男子跟前,男子一脚把她踢向女孩,霎时间,手起刀落,人首相离。
“你你你你你您……”女孩被吓得连话都说不出,连刀也吓掉了,只得一个劲后退。
“大人,咱们拿她怎么办?”一个小厮问。
“先让弟兄们玩几天,然后杀了就是。这真是,皇恩浩荡啊!——来姑娘,不要怕!到我这里来——来呀!”最后两个字,男人几乎是在咆哮。随后便有好几名士兵拔出刀冲向女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女孩愣了一下,便猛一转身,用尽全身的力气向窗外跑去,撞开她曾经最爱的雕花窗棂,接着纵身一跃,消失在山间的烟雾迷蒙之中。
“这……怎么办,大人?”
“杀了,都杀了!——你,去把我枪找回来!”男子定了定神,反手就给了说话的人一巴掌。
……
“——你醒了?”
姑娘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信息如海啸般涌进她的脑海:首要的问题就是,“我死了吗?”从这么高跳下去还不死,是开玩笑吗?她试图起身下床,却被巨大的疼痛感击倒——看来确实没死,真是见了鬼了。另外,她还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父亲应该是被杀了。要杀她的男人穿着官服,一看就是朝廷的人。可是,朝廷为什么要杀他呢?
左茗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她的父亲左星,是当朝的言官领袖,素以言辞犀利闻名于世。如今皇帝久不上朝,名为养病,实为修道,朝政由司礼监的太监把持,已是天下皆知。他们贪赃枉法,党同伐异,鱼肉百姓,搅得天下不得安生,而官员又往往惧怕他们的力量而不敢行动。正因为如此,像父亲这样敢于同宦官抗争的人,才极为少见。
所以,父亲是被那些阉人杀死的吗?
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实!
可是,面前的这个救自己的人又是谁呢?
左茗眯着眼睛,静静看着面前的老大爷。大爷的脸上满是皱纹,显得十分苍老,但从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的人。他似乎很久没有刮胡子,也不洗脸,身上飘来淡淡的臭味和药味,一双手却特别白皙柔滑,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男人的手。见左茗不说话,大爷站起身,也不理她,就蹲在一旁的炉子前煎药。一股奇异的药香带着浅浅的绿色,萦绕在房梁之间。左茗顺着这抹绿色望去,才发现:这座房子远比她想像的大,似乎一眼望不到尽头。更神奇的是,房子的横梁之上挂着一个个精致的小木盒子,比寻常的首饰盒大不了多少,然而做工却异常考究,上面还拴着布条,布条上似乎还写着字。
“这是在一座寺庙里吗?”左茗纳罕。然而她并没发现屋里有佛。
“大爷,我……”左茗几乎用尽全身的力量在喊,然而声音依旧微弱。
“嘘。”大爷做了个手势,然后从黑乎乎的锅里盛出一碗更黑的汤药,端来示意左茗喝下。
左茗喝了药,又感觉头晕了起来,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再醒来的时候,又不知道过了几天。大爷坐在火炉边,一边取暖一边烤一只散发着诱人香气的鸽子。“不好意思哈小姑娘,你才醒我就又把你弄迷糊了。不过没办法啊,我要换药,要不然就太疼了!这次换完药,你就好得差不多了,摘下纱布就可以了……”
“你呀,是真命大。”大爷还是絮絮叨叨得没完,“那么高的悬崖,你从上面摔下来,居然还没死——小姑娘家年纪轻轻为什么要跳崖呀?有什么想不开的呀?何必要像现在这样呢……”
“……你是谁?”左茗气若游丝。
“我是……算是一个大夫吧,所以我能把你救活。”大爷走了过来,把板凳搬到左茗的床前。“你呢?你是怎么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呢?”
左茗一时语塞,大爷却并不意外。“你是……失忆了?”
左茗见状赶紧点头。
“哎……能跳崖的话,一定也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吧。与其这样,不如忘了。”说罢,大爷转头起身拿酒。“你真的……只是一个大夫?”左茗问。
大爷取了酒,面向左茗耸了耸肩,“不然呢?”
“我没见过会调麻醉药的大夫。”左茗显得有点紧张。
“那是你见过的大夫太差了。”大爷重新坐回了左茗面前,把鸽子递给她,“吃不?”左茗动弹不得,只微微张开嘴,他便把鸽子胸前和腿上的一些细皮嫩肉撕下来,一点点喂她吃。
左茗吃了鸽子肉,只觉得香气四溢,妙不可言。“我们在哪?”她问。
“天云山。这是我的一个仓库。”
“是存放挂在横梁上的那些盒子的吗?它们是什么?”
“别问,问了也不会告诉你。”大爷只顾着给左茗撕肉吃。
夜阑人静,大爷在墙角睡下了,独自躺在床上的左茗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想到小时候父亲教她读书写字,带她在未央阁避暑的情形,她的泪水就不禁一阵阵地上涌:现在父亲死了,家也没了,她该上哪里去呢?她也不认识父亲的同僚,自己又是死里逃生的“朝廷钦犯”,人人避之不及,又有谁会收留她呢?
她就这样沉沉地睡着了。
翌日清晨,天色正好。老大爷一大早就起来准备拆纱布的器具,待左茗起床时,一切工作已经完成。大爷拿出一把剪刀,像是侍奉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先剪开一个小口,然后把左茗脸上的纱布一点点地解开。他光滑的指尖微微触碰着左茗脸上新生的肌肤,让她既熟悉,又陌生,并有了一种奇怪的心动感觉。
就这样磨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来,看看!看咱的医术,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你受过伤?”老大爷显得十分自豪,他拿出一面铜镜放在左茗的面前。左茗张开眼,面向铜镜,仔细打量着镜子里的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却霎时如蜘蛛般爬遍了她的全身。
这玩意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