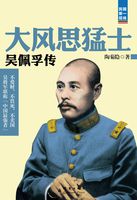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入夜依然未停。
无双人在榻上,蜷起双腿,额头抵在菱花窗上,细听雨滴噼噼啪啪敲打屋檐。
半月前,出了那桩事后,爹爹君恕立刻做主把她送入家庙暂避风头。
自那时起,无双便与外界断了联系。
自称与定情于北巡时的羽林卫下场如何,家人以及楚曜兄妹对此事态度如何,何时能接她回去……
种种与她切身相关的问题,她一概不知。
无双曾经写信给楚曜,最后只得了个信安全送到,郢王爷正在忙,回信暂缓的口信儿。
厨房里养来捉老鼠的大花猫沿着檐廊慢悠悠地散步,不时懒散地就地打滚,不知为了什么喵喵叫声不断。
那叫声凄凄惨惨戚戚,如同无双此刻的心情写照。
她明明对付过蔺如清,改变了他的命运。偶尔与杨家表哥通信时,也听他们提过蔺如清功名被夺后穷困潦倒、被人不耻,只能在店铺做杂工。
为什么害她的人远在千里之外,害她的事却还是发生了?
女儿家的名声比命还重要,爹娘是不是不相信她了?
不然怎么一句话就把她送到家庙来,之后不闻不问呢?
无双一直坚信,若是前世爹娘没有早亡,她就算遇到再多灾祸,命运也会不一样。
难道她根本想错了?
爹娘也嫌弃她丢人现眼,所以打算一直把她关在这里?
不会的,无双摇摇头,爹娘明明那么疼她。
不会的,她反复在心中念叨。
不要那么急着怀疑人,要多些信任,多些耐性,爹爹不会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
然而无双活了两辈子,加起来足有二十五年之多。就算今生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宠爱之下长大,对于她来说,也是心理年龄十六岁之后的事。真正奠定她性格基础,还有看待人与事态度的关键,还是前世没有父母照拂时的成长过程。
于是她无可避免的比一般女孩子敏感,没有安全感,为了保护自己,待人警惕心也过大。
无双很努力地说服自己,却始终难以真正相信,她还会被家人接回去。
饶了一大圈,竟然还是回归原点。
上辈子没人可以依赖,不是也靠自己逃出去了吗?
这辈子又有什么不可以!
无双毅然抹掉眼泪,爬下榻,从被筒里摸出前几天借口少带了换洗衣物,从小师太那里借来的灰蓝色粗布僧衣换上。
门后挂着从家里带来的帷帽,她取下戴上,天黑,撩起面纱才能看清路,待天亮时再放下,像陆先生那样挡住容貌,便没人能认出她是谁。
这回她不打算逃命,她要进城去,找出在背后谋划算计她的真凶来,不报此仇,就算死也不瞑目。
君家人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到家庙来祭祀祖先,由此进城的路,无双闭着眼睛也会走。
只是深更半夜,到处漆黑一片……
无双目光落在挂在床头的羊角灯笼上,拿起,又放下,蹲下从床地扒拉出一早藏在那儿的小包袱,包袱里还有用膳时省下来的两张芝麻饼,足够她撑到明天早上进城。
准备这些东西时,无双完全背着人,连跟到家庙里照顾她起居的乞巧和朝华都没发现。
她背好包袱,抱起熄灭的羊角灯笼,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门。
回廊有檐,淋不着雨,但冷风没有遮挡,一股脑往身上吹,无双哆嗦着拢了拢单薄的衣裳,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一路来到后院。
后门酉时便上了锁,出不去。但无双观察过几次,门旁有棵大树,枝繁叶茂,枝桠旁伸到院墙外,她可以从这儿走。
爬树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树皮粗糙,不几下就磨破了手心。
偏偏树干挺直,缺少以供脚踩的枝节。
无双上臂力量不够,脚下又没有落点,爬几步就跌落下来。
还好背后有包袱垫着,摔得不太疼。可惜插在包袱结里的灯笼杆滑了出去,羊角灯笼摔碎了。
冰冷的雨点拍着脸上,衣衫也渐渐湿透。
无双咬咬牙,重新系好包袱,再次行动起来。
有了前一次积累的经验,这回顺利许多,她忍着手心的疼痛,慢而稳地向上攀爬。
一步,两步,三步……
渐渐数不清。
视线终于越过围墙。
无双欢心雀跃,她看向大树旁伸向墙头的枝桠——最粗最结实的那一枝,她数过许多回,摸黑也找得到。
雨似乎停了,月亮隔着云层透出微光。
有一团奇怪的黑影在她打算经过的树枝上。
山猴?鬼怪?
无双打了个冷战。
她胆怯,迟疑。
那团黑影一动不动,似乎不是活物。
无双长舒一口气,说不定只是个新搭起来的巨型鸟巢而已。
她手脚并用攀上树枝,抱着鸟巢绕过去,应该可行吧?
月亮猛地从云层后面跃出来,清冽的月光照亮那团黑影。
那是一个人!
一个陌生的、满脸络腮胡的男人!
几乎在无双看清这些的同时,一把粉末夹着幽香扑到她脸上,她立刻感觉头脑发昏,眼皮发沉,连挣扎抵抗都来不及,整个人便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无双猛地睁开眼,呈现在她眼前的是碧蓝的晴空。
天亮了——她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身下的地面有节奏地晃悠着,不对,这不是地面,她好像是在车上。
马蹄哒哒,车轮辘辘,不徐不疾地传入耳中。
无双愈发肯定起来,她在马车上,一辆没有顶棚的马车。
是楚曜吗?
她有点不敢爬起来看个究竟,怕失望。
轱辘压在碎石上,马车猛地一颠。
无双被抛起,又重重落回去。
昏睡前的记忆潮水一般汹涌着回到脑海里……
她霍地坐起,扭头去看,赶车的人是个男子,因他坐着,只能看到上身,魁梧强壮,不是楚曜,倒更像蹲在树上的那个人。
“睡醒了?”那人适时开口,仿佛脑后长眼看到无双行动一般,“后面有食物和水,你要是渴了饿了就吃点,别客气。”
无双目光转动,果然看到脚边摆着一只大铁壶,还有一盘馒头。
可是那馒头连笊篱都没盖,他们走的又是土路,早不知落了多少灰尘。
无双撇撇嘴,问那人:“你……你是谁?你要带我去哪儿?”
“俺是个农夫,住在大山里。”他道,语调里添多几分乡气,“现在带你上山,给俺兄弟做媳妇,生娃娃。”
无双愕然退后几步,马车又是一颠,她一下子坐倒在地。
“别乱动,这车不牢靠,小心把你掉下去。”那人又道。
对,她就是要下去。
“停车!”无双大喊,“我不跟你去!”
那人根本不理她,连头也不回,还扬鞭催马,加快了速度。
是她傻了,一个人口贩子,怎么可能听她喊几句就放人。
无双轻手轻脚地站起来,拎起铁壶:“哎,有杯子吗?我要喝水。”
她用说话声掩饰脚步声。
“俺们山里人豪爽,喝水不用杯,直接对壶……”话没说完,就觉脑后有邪风袭来。
他猛地转身,无双手中挥动的铁壶已到脸前,他迅速后仰,手臂前伸,大掌握住壶嘴,不过一眨眼间,铁壶已被抢了过去。那力道带得无双向前踉跄几步,耳中听得他喝骂:“好家伙,你还真打啊,把我打死了你知道怎么回家么,不是说王妃么,行为粗鲁,脑子也蠢!”
大约是骂够了,他一扬手,抛开铁壶,举起右掌,往无双打来。
可怜无双看得到,却躲不开,后颈中掌,身体晃了晃,又晕了过去。
无双一骨碌坐起来,打量四周。
她现在身处一间布置简陋的房间中。
昏迷时睡的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架子床,床前几步远的方桌上点着一盏油灯,再过去几步是对开的窗户,窗前摆着竹椅与边桌。
难道她真的被带到大山里了?
还是趁没人赶紧逃吧!
无双跳下竹塌,满屋子转悠一圈,没找到自己的包袱。
她在包袱里放了半幅身家——全部的银票和值钱却低调的首饰。
原想着若有什么变故,可以充作盘缠,甚至往后的生活费用。
若是找不到,还怎么回上京?
无双摸摸头发,本想摸出个发钗步摇之类的头饰,动作做到一半忽然记起准备逃走时把自己打扮成了带发修行的出家人……不对,她现在穿的不是灰蓝暗沉的尼姑袍!
无双看着身上淡绿绣兰花纹的棉布襦裙,是谁给她换的衣服,男还是女?
该不会……该不会……
正欲哭无泪时,听得脚步轻响,门帘挑起,走进一名女子来。她约莫二十来岁年纪,生得明艳照人,梳妇人发髻,衣服与无双穿的同色同款,不同的只是绣了竹纹。
“这位嫂子,”无双想也不想便扑过去跪在她面前,“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不能嫁在这里,我在上京有家人,有未婚夫婿,我……”
那名女子将手中端的甜白瓷炖盅放在桌上,一脸困惑地打断她:“怎么回事?谁说要把你胡乱嫁人的?”说话间,她面上闪过顿悟的表情,顿足笑道,“这些年,你长大了,我可没什么变化,就算他没说,你难道还认不出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