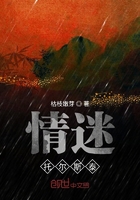我后来告诉他,你住在美国南方这片富丽家园,拥有所有我可以想到的生活乐趣;你到广州来,我能让你如何欣赏我们的生活?那里的城市,一千个人拥有的绿荫没有这里一家人拥有的大。一位美国教授到中国北京,朋友好不容易挤车带他去香山,指着远方说,那就是著名的香山红叶。该教授说,我的天,这就是咱们长途跋涉的理由?在美国俺家后院就是一片红枫树。在我家广州,河流是黑色的,城市充满噪音。无数的机动车堆积在桥梁上,人们习以为常;哪像美国,稍有堵车,车里的人就做婴儿状。我总不能让你欣赏这些吧?如果你对城市百姓唯一的生活享受—吃都毫无兴趣,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一位香港教授到苏州开会,后来写文章说内地人请客如何浪费。我到香港也被朋友招待过,主人一般都不多点菜。不像内地人,从餐前小食、酒水、正菜,到餐后甜点、水果,一定是一道道都叫齐了,才算请客。我这里说的不是公费花销,只想解释一下普通中国人请客铺排的心态。富贵的客人不领情,活活把咱好心当了驴肝肺。
我在美国人家做客吃饭,发现他们是真的不讲究。早上起来烧壶水,煮咖啡冲茶,冰箱里随便拿点面包牛奶水果,也不一定全家等到一起。中午上班的人带块三明治,回家的人切点番茄、洋葱,面包上涂点抹点,就杯冰水或果汁,这又是一顿,连火都不动。晚餐时主妇也许做个浓汤,切上生菜,再拌个面条、通心粉之类,或者现烤个面包,那就很正式了。美国人不劝酒,不给客人夹菜,就餐的方式是中国人最禁忌的那种—端起盘子往自己碗里赶;想吃什么自己拿好了,不用瞅旁人。
我们中国人要十个盘子八大碗才叫待客,家常便饭可不敢让客人吃。那叫不懂礼、小气。好东西留来待客,本来也是美德;物以稀为贵,互相分享嘛。可是从前的过年饭菜现在也很寻常了,中国人的胃口却日新月异。摆宴席公款吃喝这还不算,进嘴的东西是称奇斗胜。
美国人也有吃鹿肉的,那是在法定的时间和地带,有许可证的人才可以猎鹿。不仅虐杀动物犯法,把山上的野花挖去卖钱也违法。小朋友踏春看花,都是举着放大镜,绝没有折花枝、揪树叶的。这是人家的习惯,再加上法律的规定。家院前绚丽的玫瑰、满大街的郁金香,自管开放,没有人去碰。我路过一个田家,那主人自己圈了一片地,在里面养了些他喜欢的动物。我经常看见高高的鸵鸟在那里走动,而它的中国家族的鸵鸟蛋,正被标价55元一个卖了给人炒着吃。友人达格玛开车外出,不仅给鹿让路,发现一个乌龟在路上爬,她也要停下车,把乌龟拣起来,送它去树林里。我在新奥尔良的公园里看见,水池里有两只手掌大的小野鸭。它们见了人就游过来,像孩子见了妈要吃的。游人爱怜地看着它们,还要说:啊,baby,不知道你在这儿,没带什么。从水池边走了好远,进到树林里,我才发现,两对鸭夫妻正趴在那里晒太阳,毫不担心自己的孩子。湖面上,浮动着成群的野鸭和天鹅。
两相比较,我就不好意思再跟美国人抬杠,说你们也吃肉。中国现在没有饥荒,为什么人们如此贪婪,不仅是逮着什么吃什么,而且是吃它个穷凶极恶,山珍海味亦不满足,山穷水尽也不在乎。为了眼前吃饱喝足,整条整条的河流污染,整个城市的水源面临威胁,青藏高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黄河壶口瀑布萎缩……类似的报道有多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过这样的城市噩梦,有两个城市已被垃圾包围,每个城市都极力把自己的垃圾推向对方,很快这个比赛就要见分晓,一座城市的垃圾将掩埋另一座城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教授彼特·辛格提出,把人的利益放在其他物种的利益之上,这叫“物种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一些保护动物组织的成员甚至到大学的实验室里去解救兔子、老鼠。还有的人要求说,拿动物做实验时,必须尽可能减轻它们的痛苦,因为动物也会喊疼的。这些人说的动物权利,和我们中国人说的保护环境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所说的,依然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人这样残杀动物、虐待环境,叫做人欲横流。我们不仅正在灭绝其他物种,而且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种贪婪和残忍里,并终将被这种贪婪和残忍所毁灭。
美国人也有好战的时候,打朝鲜、打越南,打到别的国家里;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冲突以及近年来的校园枪击事件一直没有断绝。但是相对来说,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南北战争后一个多世纪,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有些老城的街区,一些巴洛克风格的住宅坐落在花园里,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试想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多少战乱?如果有一百年的和平建设,中国又将如何?战乱是恒常,和平是短暂;捞一把算一把,苟活于乱世。给下辈人留条干净的河、留点地方种树?这辈子怎么过还想不过来呢。
最后我要回到中国人的吃和环境伦理的话题上。观察了美国人对待动物和环境的态度,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从现今这种嗜杀成性的饮食风气转变到给乌龟让路这一步。
事实上,我们历史里一直都有着极端的荒唐野蛮。把过去的文化看作一座静止的文明宫殿,这是把历史孤立起来,并且理想化了。在这一点上,鲁迅真了不起,因为他敢打开天窗说亮话,把中国的历史叫做吃人。《狂人日记》虽然是篇小说,但那故事和史实是孔孟书里看不到的。它实在应该成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入门书,而今天的中国人更该时时反思。
我们的历史早有吃人的记载。《左传》上提到,公元前488年,被包围的城民曾“易子而食”。
这不叫惨无人道,在封建传统道德里,吃人者可以是美德表率。公元前七世纪的易牙是齐桓王的奸臣和他最喜欢的厨子,齐桓王说他没吃过小孩肉,易牙把他自己的儿子煮了给国王吃。
吃人作为惩戒和效忠行为,一直延续到21世纪。几年前我在《羊城晚报》上读到一个报道,实在骇人听闻,我一直希望有人证明它是虚构的。文中说道,记者去一个林区养殖场,那里人工圈养着熊。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举着粗大的针筒走近笼子时,所有的熊都开始哀号。这里的人就这样活活抽取熊的胆汁,被抽过胆汁的熊摊在地上,缩成一团。美国这里,有些保护动物组织的成员寄出抗议信,那些拿动物做实验的科学家打开时,信里包着剃须刀片。这般活抽熊胆汁的人员真该庆幸,他们离美国远着呢。
美国学者讲到中国文化、中国宗教,总会说到孔孟老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永世的中国文化,对活的中国,他们并没有兴趣。我听到如此的中国,总有种要发疯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算哪门子中国人,也不知道咱们怎么就把那个天人合一、沉思冥想的中国丢失了。
当我说道今天的中国时,我知道自己也是不领情。人家好不容易在咱们中国里找了点玩意,你还要去扫兴,像个卖国贼。我问我自己,中国传统里就没有好东西吗?当然不。我爱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诗词,中国古典文学艺术,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飨宴。
某个冬日黄昏,我从图书馆里出来。教堂钟声在暮色里回荡,古老的石头建筑底层,灯光一片橙红。一棵棵高大的白橡树举手向天,这景色仿佛持续了一百年,还会持续下去。而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回国了。这个地方,也许我一生都不会再来。想到这里,顿时感觉时光变幻。树叶是敏感的,到了季节它就一片片落下来;像我这样一个中国人是敏感的,看见月亮就不免想到羁旅、客栈、床前明月。可是时间是不敏感的,它一路流逝,不介意谁的伤怀。我周围的美国朋友似乎也是不敏感的。圣诞前一个月夜,他们约我到附近的中国餐馆吃饭。回来开车上山,好一轮明月当头,堂堂辉映道路。我说,在中国,月圆就是团圆的日子。美国朋友说,你知道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吗,因为今天是月亮运行轨道离地球最近的一天。瞧,美国人的思维是这样的。
我教一位教授学中文,也能感到中英语言文字多么不同。我们每一字都是一幅画、一个故事,字里有字,虚实不定。还有,中文教科书里启蒙的句子非常热情:欢迎你,很高兴见到你。正像我们中文里“亲爱的你”,每一个字都有极深的感情。而在英文里,dear常常是个客套,并无特殊意味。英文课本开篇里,我们学的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实实在在:这是书,那是笔。
我们的感情被语言琢磨得多么细腻啊,看见落叶和月光,那是一定要想到春花秋月、想到故国不堪回首的。每个热爱汉语言文学的人,都能一丝一缕地体会到人生的愁绪。汉语的美尽在这种生命有限、时光无穷的浩叹里。这样一种哀痛,化做对生命里许多细节的精雕细琢,于是乎有美食,有感伤的诗词曲赋。为推敲一个字,诗人不惜琢磨一辈子。中国什么都不发达,唯有语言,数得上是世界之最。
我在电脑前打字时放一点音乐,以压倒电流轰轰响的声音。有时我反复听一段西人的弥撒,那也很美,是人间向天国的倾诉。由此我想到,西方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感伤,他们有上帝。他们的信仰是,天堂里生命更美好。看见今天的落花、此世的月亮,为什么要伤心呢?天国的玫瑰远胜过人世。可是,中国人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今天的月亮明天不会再有。今天的相聚可能就是永别,今天的黑发正在变成白发……我们活在有限的此世,不相信来世更好。中国人对生命的感知,处在现世这个致命的刻度下。问君能有几多愁,如此旷世的疑问,真是要多少有多少。当我换上中国音乐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那里面全是眷恋。哪有什么天国?天上云雾雨雪,都是人世缠绵。
当我教外国人中文时,我不知道怎么能教出这种中国人的愁肠百结。或许,这是不必要的;可是没有这样的情怀,怎么能明白中国古典诗词之美?那种对山河岁月的感叹,全是因为这一切都不再有。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语言艺术是登峰造极,它志在穷尽有限人生和无限时间的冲突,它的中心是缅怀和记忆。所有的诗篇都向着过去、无限留恋过去。在这梦想的诗学世界,过去的一切得到美化。中国人的伤痛和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得到安抚。
所以我们不乐意把自然和个人感情分开,自然是感性的自然,月亮是风花雪月。个人生命如此短暂,谁愿意献身自然的奥秘、科学的发现?读书人被这样的天人合一观念陶冶,理性思维残缺不全。我们缺乏把自己和自然分开的态度,缺乏精确地表达事物的习惯,缺乏探索自然的意志。一不是一、二不是二的修辞想象有利于诗人作惊人之语;用在日常生活里,人人学会诡辩。这种内心和现实的分裂,这种自我麻醉和化解的能力,是中国人普遍的生存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