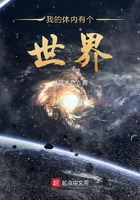连祺捻手捻脚的闪进天音阁,他知道舅父放置灵丹妙药,有一个翡翠玉柜,在一个木色的屏风后面,连祺在侧殿,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屏风,后面的翡翠玉柜,高约二十尺,宽约十五,每一个暗格内都放置几个丹瓶,颜色、形状各异。
看着这玲琅满目的各色小瓶,连祺欲哭无泪,到底哪一个是空青丹......眼看时间所剩无几,却遇到这样棘手的一件事,连祺忽地想到一个办法,空青丹舅父这里只有两颗,将只装有两颗药丸的药瓶找出来,不就好了。
他开始摇晃掂量起每一个药瓶,听声判断,确定不了,就打开塞子瞅瞅,半个时辰过去了,他找完柜上的所有药瓶后,筛选出三四个仅盛有两个药丸的瓶子,连祺又打开每一个,看里面药丸的颜色,空青丹是墨绿色的,这一点他还是知道的,两个琉璃珠大小的药丸,只要颜色符合,那就能确定,哪一个是空青丹了。
连祺找到了一瓶差不多的,照着样子,随手变幻了一个颜色大小与之相同的假空青丹,放进了瓶子里,将一颗真的塞进了袖子里,将所有东西都物归原位后,连祺飞速跑出侧殿,刚走到侧殿花园门口,就看到天帝被众仙侍簇拥着,往这边走来,情急之下,连祺展翅而起,飞越院墙,背紧贴墙壁,看着天帝一行人走进去后,连祺赶忙一溜烟的逃跑了。
七个时辰,待连祺赶回山洞,还余一个时辰,连祺一口气都没来得及歇,赶忙将空青丹塞进了夜北溟口中,空青丹一入口,就散发出幽幽蓝光,可以清楚的看到它顺着夜北溟的喉咙滑入腹内,一会儿,光芒就消失了。
原本笼罩在夜北溟身周的艳红色光芒,也随着空青丹的入体,化为了幽蓝,在夜北溟体表耀熠半饷后,光芒散去了,一切都暗淡了下来,连祺眨巴眨巴眼睛,紧张而又期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四周沉寂片刻后,置于夜北溟双手间的金莲,忽地腾空而起,漂浮向空中,围绕在它身周的金色光芒,像是萤火虫般的,一闪一闪,而后,六瓣金莲分离开来,缓缓落下,接近夜北溟身体的那一刻,蓦地,融了进去,不见了踪影。
在那一瞬间,夜北溟猛地深吸一口长气,突然有了气息,背部高高抬起,抬起到极致时,忽地重重落下,随着身体落下,浑身上下突然发出一道强烈的白光,连祺下意识衣袖掩面,别过头去。
光芒十分的刺眼,就连洞口的瀑布都遮挡不住这亮如白昼的光芒,待白光渐渐暗去,连祺才缓缓回过头,一看到身后的景象,不禁惊呆了,只见寒冰床上,已不见了夜北溟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灵巧的美丽白狐,正安静乖巧的蜷缩成一团,呼吸均匀,安静的睡着,通体雪白,没有一丝杂质,这绝对是连祺此生见过为数不多的白狐中,最完美无暇的一只。
它首尾相依,长长的睫毛轻柔的搭在一只前爪上,安静的卧着,连祺轻轻探了探,直到在它的鼻尖感受到均匀的呼吸,连祺这才松了一口气,只是,观现在这般模样,若要恢复人形,可能还需些时日。
忙活了一整天的连祺,伸着懒腰走出山洞,一屁股坐在岸边的草地上,坐了一会儿,缓缓地躺了下去,长长舒出一口气来,惬意而慢慢地合上了眼睛。月明星稀,伴着阵阵秋风,身心也跟着慵懒了下来,一件压在他心头的大事,终于完成了,霎时感觉,这风,都香甜了很多。
在这片相同的夜空下,有的地方,安静惬意,而有的地方,却是千钧一发的万马奔腾,死寂林谷之中,白夜和千浮雪二人,还在与五雷兽做着斗争。
二人观四周,无论如何也得在天亮之前出去,这里满是瘴气,待的时间愈久,就愈是危险,更何况,瘴气入体已经很久了,好在二人都是修仙之人,若是凡夫俗子,恐怕早已命丧黄泉。
五雷兽不断的嘶吼着,也没有停止过挣扎,白夜在满是瘴气的地方,灵力被大大束缚,九连索也支撑不了多久,千浮雪在四下寻着契机,看有没有能吸引它注意力的方法,好去到对面的崖壁上取下偃魔杵,二人早在藏身时,就发现了卡在对面崖壁上的偃魔杵,只是,下面那家伙,一直在挣扎,且越来越暴躁,只怕有人落下,会刺激到它,使它更加的亢奋。
对面崖壁地势也十分不利,他二人藏身的这面崖壁有四五棵倒栽岩松,而对面的崖壁,却是光秃秃一片,那偃魔杵卡在两颗凸起的岩石之间,周围生了些杂草,将它牢牢兜住。
白夜思虑了一会儿,决定先发制人,以身探险,小声对千浮雪道:“我下去......”话还未说完,心急如焚的千浮雪就已经一跃下了岩松,现在的她,已经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任何话语,那一切的背叛和刺激,使她完全变得刚强、叛逆,且倔强,说一不二,当时入谷时说了不需任何人帮忙,就不要任何人帮忙,尤其是白夜。
白夜观之惊恐,赶忙随着她一起落下,千浮雪的落下刺激了五雷兽,更加的狂躁不安起来,嘶吼声彻天动地,白夜感受到灵力在急速锐减,九连索已经困不住它了。
千浮雪利用自己的轻功优势,放在平常,无论跃上多高的地方,都是轻而易举,可现在,拖着这具被瘴气大量侵入的身躯,动作不再轻盈,行动也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她拼尽全力,也只是落在了距偃魔杵还有三十余丈远的地方,区区三十余丈,对她来说根本不在话下,眨个眼的功夫就能及,可现在,于她却仿佛远在天边。
千浮雪不屈不挠,十指死命的找扒崖壁壁缝,双脚拼命的踩住每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凸处,崖壁上缠缚的丝丝雷电,沿着她的手臂钻进她身体里,每往上爬动一下,每扣一处,手就像生生按在荆棘上似的疼痛,身体疼的她几乎无法使力,全凭意念在支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