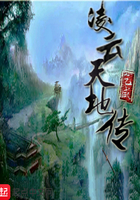张白圭捡起龙骨铁扇递给赵乙,“赵兄,此战我兵刃断裂、精疲力竭,再无一战之力,而赵兄兵刃完好如初,内力依旧,理应是赵兄胜出,我张白圭虽然惜命,却也一诺千金尊崇礼法,输了便是输了,张某这条命,你拿去吧。”
按照大元律例,但凡签署天诛令者挑战失败,立刻授首。
赵乙没去接龙骨铁扇,转身向着皇城方向遥遥一指,漠然道:“张兄,你看那皇城。”
张白圭不解其意,赵乙继续说道:“那皇城看似固若金汤,但在五十年前却是被胡人践踏,人皇被掳,贵妃牵羊,可谓是国之大辱,五十年以后,我大元虽然仍然风雨飘摇,但也有了一批能征战、善杀敌的武官和将士,这是为何?这乃是我大元人皇开言纳谏重用良臣之果,不管是乾元宫还是离元宫,都属于国之重器,是我大元军民的保障之所,还有那山钟,你当真以为敲响之后便要与我大元整个朝廷为敌了吗?”
“莫非其中还有深意?”
波涛翻涌,张白圭只觉脑中轰然,他有种感觉,赵乙接下来的话会完全颠覆他的认知。
“深意自是没有,但绝非是寻常之人想的那般复杂。”赵乙目光深邃,依旧盯着皇城所在,笑道:“世人只知道敲了山钟便是宣告与朝廷为敌,与天地为敌,与全世界为敌,故而将敲山钟称之为签署天诛令,意为被世人被朝廷所遗弃,苍天可诛,厚土可灭,实则不然,在为官者眼中,敲山钟就是敲山钟,只是胸怀大志而不能施展拳脚者向世人宣告自己存在的一种手段,无论是挑战离元宫,或是挑战乾元宫,朝廷并非会拼命地去为难,胜了便可继续向前,败了亦是要授首。
而胜负之说也并非分出你死我活,按照市井斗殴的规则,一方认输,另一方便是胜者,而传言中入离元宫挑战必须你死我活方能分出身负乃是当地离元宫为保全官府的声誉而凶狠将挑战者诛杀,亦或受挑战者不服被挑战者所杀才分出胜负,故而流传的谣言罢了,试想,若朝廷当真想要敲山钟之人的命,直接杀了便是,甚至不去设置山钟,不是更加万无一失?
说到底,朝廷设置山钟,实则是为了为朝廷选拔可用之才,莫说是与天下人为敌,敲钟之人在未入品之前根本属于末流,入不得九品武官的眼,更何谈与整个朝廷为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赵乙侃侃而谈,张白圭听得目瞪口呆,许久才回过神来,神色古怪的盯着赵乙,“照你所说,这敲山钟乃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为何数十年过去,敲山钟者却是寥寥无几,记录在案者也都身首异处,死于非命?”
“所谓敲山钟,虽并非与朝廷为敌,却也触及了离元宫与乾元宫的底线,大多敲山钟之人其实都并未闯过离元宫便被离元宫军士所斩杀,以彰显离元宫的高不可犯,剩余的则是在入品之后被朝廷施以悬赏,而后被同阶之人所杀,从而被取而代之,故而这敲山钟并非是无用之举,反而优胜劣汰,给朝廷选拔了不少优秀的武官,纵然敲山钟者大多死于非命,但将其取而代之的武官却都是成就非凡,也正是如此,大多武者都会通过离元宫入仕,而不是通过敲山钟此等剑走偏锋危机重重的冒险之途。”
“那赵兄又为何让在下赢?如此岂不是落了乾元宫的威名?”张白圭问道。
赵乙深邃的眸子闪过两道精光,长袖一挥,霸气道:“我乾元宫何须他人认可,又哪轮得到旁人品头论足?有人若是不服,尽可前来一战!”
春风吹动衣衫,发出猎猎之声,赵乙的身影在此刻与乾元宫化作一处,成为了皇城最坚实的壁垒,坚不可破。
这一刻,这片天地属于赵乙。
张白圭默然躬身一拜。
夕阳斜坠,赵乙将张白圭送至乾元宫门口,两人依依惜别。
“张兄,当真不入我乾元宫读几本秘籍?”
“赵兄已然高抬贵手让在下胜出,在下哪还有脸面去修习乾元宫的功法?”张白圭叹道,“此事莫要再提。”
话已至此,赵乙也便不再多言,挥了挥手,后面一个军士双手拖上一个由红布遮盖的长条锦盒,赵乙掀开红布,里面显露出一把寒光闪烁的三尺长剑。
“赵兄,你这是……”张白圭惊愕。
赵乙笑道:“张兄高风亮节,不肯进我乾元宫修习,在下也不能让张兄空手而归。”
赵乙说着便提起长剑,手一抖,发出一阵清脆的剑鸣,夕阳斜照,剑锋上反衬出昏黄的冷光。
“这把剑乃是由精铁为基础,经京师最好的匠人打造七七四十九天方才炼制而成,虽然比不上紫电清霜之流,但也能当个应急的兵器,还望张兄收下。”
赵乙挥手令来人退下,马上又有第二个军士从乾元宫走出,手中拿着一个油布包裹。
“方才一战,张兄最后三剑威力虽强,却极为依仗下盘功夫,我观张兄下盘虽稳,但亦是勉强支撑,这是我在七花宫习武之时所修习的腿上功夫,张兄可借鉴一二,或有所用。”
一连两个惊喜,令张白圭感慨不已,只得对赵乙拱手再拜,赵乙笑盈盈的扶着张白圭的手臂,神色郑重道:“张兄不必客气,这是你应得的,你若不要怕是外人会说我乾元宫不懂礼数仗势欺人,另外,张兄既然闯过我乾元宫,下一步便是要去太学院武院了,有些事我须与张兄交代一二。”
“还望赵兄赐教。”张白圭虚心请教。
于是赵乙便将太学院武院的见闻与张白圭一一道来。
凡挑战太学院武院的武者,面对的并非如同前两关一般的太学院武院举人,而是要经过太学院设下的关卡挑战方能破关成功,而传闻太学院的关卡为十八个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行当的人,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均是将自己的行当做到极致之人,因此十八人衣衫不尽相同,因此被太学院称之为“十八衫”。
正所谓十八衫,十八衫,十八衫来十八关,敲山钟之人若想过关,便需要从最底层的衣衫开始挑战,层层递进,直至十八关全破,方才算是破关。
如若途中一关失败,等待他的便是身首异处。
赵乙又将十八衫的各方情况与张白圭讲述,张白圭心中也才有了不小的底气。
至于赵乙所赠的秘籍,则是顺理成章的被送到了狂九刀的手中,有了这本秘籍,狂九刀九刀全出指日可待。
张白圭打了个翻身仗,京师中顿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向,对张白圭的褒贬也各不相同,谁能想到,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真的打败了身经百战的掌军校尉?
有关张白圭的童谣少了,说书人的台本却是厚了,一波三折之后,那不自量力不思进取的软弱书生摇身一变,又变成了奋发图强砥砺前进的青年标榜。
闹市里传唱着张贡士卧薪尝胆的英雄事迹,茶馆中颂扬着张贡士投笔从戎的壮志情怀,整个京师犹如狂风过境,换了一种态度。
唯有太学院武院对张白圭依旧嗤之以鼻,直言毛头小儿只是逞一时之厉。
春风送暖,院内的枯木生出嫩芽,偶有剑光闪烁,斩落一地翠枝,乌茜宛若一席春燕,辗转腾挪,手中持铁剑挥洒,剑法越发行云流水。
距离张白圭独挑乾元宫已经半月有余,乌茜心头越发沉重,压力也越来越大,半个月以来她每日几乎要练剑八九个时辰,有时直至深夜还能听到同院内剑风呼啸的声音。
对此,张白圭也颇感惊讶,未曾想,一个女子竟是有如此大的魄力与坚韧的毅力。
张白圭这些时日也未曾闲着,整日出没于闹市之中,或观屠夫卖肉,或赏小二斟酒,每到一处都认真观察,体验日常生活的同时更能感受江湖的别样魅力,最主要的是能够知己知彼,为闯十八衫做准备。
一声锣响炸开,引得街巷中人齐齐看去,只见在那闹市街头,一乘紫蟒锦缎八人大轿应声而来,轿子前方有数名兵头开路,皆是昂首挺胸器宇轩昂,只片刻,这乘八抬大轿便平稳的进入巷子,走到巷尾一个杂货铺处方才停了下来。
为首领路之人再次敲锣,紫蟒八抬大轿方才被小心翼翼的落了下来。
与此同时,一个身穿蓝色锦缎道袍,头顶金钗龙冠,手持洁净拂尘的三寸须道士巍然走出。
目光巡视,领路人立刻上前点头哈腰,万般讨好的对着道士说道:“王天师,就是这里了。”
被唤作王天师之人点点头,也不说话,抬手抖动拂尘,身后几个兵头瞬间一拥而上,骂骂咧咧的锤着紧闭的大门。
“还敢跟道爷玩儿闭门不见,给我把门砸开!”
王天师神情冷漠,一声令下,几个兵头闻言有了底气,周身一震,一脚便踹翻了那本就不大结实的木门。
门内,一个形容枯槁的老汉手持锄头,颤巍巍的瞪着那群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