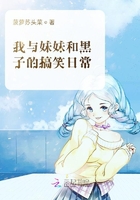第34章
沈霍寅与她四目相望,忽然凉涩一笑:“对不起”。
她的呼吸微乱,背抵在冰凉的金属壁上,墙体凉飕的寒意渗入她的脊背。
沈霍寅颓唐的低着头,微乱的碎发让整个面容变得不再清晰。
子夜对于这个意外之吻还未想好开口,突然电梯一阵摇晃,墙角的灯光瞬间熄灭,她惊恐的尖叫一声,沈霍寅立即跑过去揽住她。等平静下来后,整个空间昏暗空洞,只有墙壁上红色的指示灯零星闪烁。
子夜呼吸困难,浑身瑟瑟发抖,沈霍寅感受到她的惧意,安慰的将她搂紧,脸贴着耳侧,柔声说:“乖,不要怕,有我在。”
这句话仿佛将她带回旧日纯白的时光,记忆里那个笑意暖暖的白衣少年与此时此刻的沈霍寅渐渐重叠,子夜微微抬起头看他,难明的灯光下,那明晰的脸侧有种奇异的温柔。他的声音有蛊惑心神的能力,奇异让她安静下来。
等她身体渐渐放松,他轻轻放开她起身,还未迈开脚步那双小手就紧紧抓住他的衣角,“你要去哪?”声音里透着清晰的无助和惊恐,沈霍寅只觉得心疼,蹲下身,抚着她的发说:“电梯应该出故障了,我去看看应急铃好不好使?”
听言,子夜只得迫使自己放开手。
沈霍寅柔软的笑了一下,去翻看电梯线路,他对着话筒喊了几声,没有任何回应:“大概线被烧了,等一会儿应该就会有人来。”
重新坐在子夜身边,手臂紧紧揽着她,子夜微微一滞,又顺从的放松身体。
时间就这样安然的止步不前,他们贪恋这样的温存时光,仿佛可以暂且将那些怨怼的过往放下。子夜脸贴着墙壁,困倦的闭上眼睛。虽是初夏但电梯里的凉气深重,沈霍寅手掌温热摩挲她的手心。
子夜睁开眼睛,弯着头突然问:“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回来找我?”她眸子霎时迸发出流光溢彩,眼角末梢流转着顽意,聪慧如同一只慵懒的猫。
沈霍寅浅淡的笑,手指穿过她的发,“是我一直记得你说过的,你在这里等我。只是在刚回来的时候也会害怕也会忐忑,只是比起那小小的不确定,我更怕与你错间而过。”他扬起眼角凝视她,“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没有信心,害怕时光和距离,那样强大的力量足以改变太多。”
这是第一次他将他的感受告诉她。年少记忆中他一直都是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带着天生的卓然和自信,她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一方,面对他水滴不露的攻陷渐渐的沉沦。她抬眼看他,认真想了很久才说:“其实你不回来我真的打算忘记你的。”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有无限的时间和豪言壮语,将爱情视为至上,而长大后这种勇气反而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对时间妥协。
沈霍寅静默的抿起嘴角,他同样了解那种心境,所以无话可说。
“你当初突然不回国的原因是什么?”前几次子夜不打算问,恨恨的想无论是什么样的借口都不可原谅,可从方才那意外之吻,她感受到太多的痛楚,不甘和酸涩。
他身体一滞,没有说话,那些血腥黑暗的过程在他眼前崩折,面对父亲突如其来的死亡,和轰然倒塌的世界的恐惧依旧让他颤抖,可眼前这个如花笑靥的女子一如过往澄澈清透,他突然觉得自己来找她是个错误。
了夜在他沉默中渐渐死心,嘴边的一句“混蛋”都无力说出。
正在此时,电梯的门徐徐打开,门逢中透出万丈光芒的清辉,宛若拨开蔽天云层,墨色凝浊的空间瞬间亮如白昼,时璐和其他工作人员逆着光杵在电梯口,脸上皆是如重释怀的微笑。
子夜忙不迭挣脱他,趁其他人还未反应过来便匆匆离开。
恒远的一期工程楼房已经开盘,短短七天的预定就已经销售一空。而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工,一排排的平房被推倒,尘土飞扬、烟灰满天。施工场地的外墙上挂着大幅美仑美奂的宣传画卷,在竣工后这里将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唯美的画卷上,高楼耸立,车流不息,绿荫盛盛。一位美丽的少妇牵着孩童漫步于花园中,脸上扬着幸福的笑容。
子夜脖子上挂了好几个单反相机,她不断按着闪光灯,将这里所有的情况都据实拍下来。
算是逃避吧,事后她只把采访稿以邮件形式发给沈霍寅,再也没有一次出现在恒远大厦,此时,她站在工地的一旁,认真听工人给她讲这栋楼层的大体规划,晚间只需将这些资料整合成文章就大功告成了。子夜正低着头翻看相机里照片,顺便调出来让他们帮忙选最合适的几张。
十几个人浩荡的脚步声渐行渐近,子夜还未抬头,便听周围人立即起身恭敬的声音:“沈总”。惊讶的抬头,正好与沈霍寅眉目相对,今天的他与前几次见到不同,身上穿着工装和戴着土黄色安全帽,看起来与众不同,他应该是来查验工程进程的,子夜看着他,他工作时,原本清淡的眉眼愈发深沉,深邃的眼神让人琢磨不透,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
旁边的人为她和他作介绍,彼此如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样互相点了点头,然后错肩而过,朝背离的方向各自延伸走远。
晚上子夜在报社里加班,她写稿子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必须用手写,直到满意修改完成后再打到电脑上,即使第二天编辑火烧急撩的催稿,她宁愿不睡觉也不在电脑上写。以前他总笑她做多做了一份无用功,她只浅浅听着,却难以改变。有些习惯她坚持到近乎偏执的地步。
许致远来找她时,她还在伏案工作,暖黄色的灯影在她身上勾勒出清柔的淡色。他走到她桌前,她还未发觉,精巧的笔记本屏幕上正放着她白天拍摄的相片,因角度的问题,只看翩翩轻扬的背影,正指着楼房,神色卓俊清然,而凭借这么多年的熟识,他早己看出照片上那个指点江山的人是谁。
子夜抬头时终于看见许致远,发现他的视线厚脸颊不期然泛着点晕红:“师兄,这么晚了,你找我什么事?”
许致远敛了笑意,温雅眉宇间一闪而过忧色,他把方才看见的稿件递给她。子夜疑惑的接过,扫了几眼后大惊失色,抬头直视他,“师兄,他不是这种人。”她脸上满满的坚毅与信任让许致远微怔。
那份稿件是今天下午许致远审核作者投稿信件中发现的,里面指责了恒运公司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给拆迁户足够的赔偿金就被要求强制撤离,有的甚至受到了恐吓威胁,其中出示了恒远公司开的票据以及几张贫困艰苦拆迁户的照片,证据凿凿。
这样强烈的社评若被发布,后果将不堪设想。
多年的兄弟,许致远又怎能不了解沈霍寅的人品:“现在关键不是我相不相信他的问题,而是该如何找到发这封信的人和查明事情的真相。既然他们有心抹黑恒远,断然不会只投给我们这一家,如果这份报道被流传出去,无论真假,恒远必然会受到冲击。”
子夜点点头,放下手中工作,利落的打电话给相识的报社,和他们的协商这份报道先按压不发,许致远则打电话给沈霍寅。
而沈霍寅那边比他们早一下午就知道消息了。
宽敞的办公室笼罩着一股低气压,他长身而立站在落地窗前,艳阳高照,临街的街道树木早己苍盛盎然,他居高临下俯视,往日安静的广场此时人头攒动,聚集在一起如小小黑的蚂蚁一样。他挽高衬衣袖口,疲倦的抚额,侧首站在窗边。在他身后的房门传来敲门声,助理站在门口,声音低低的:“沈总,那些拆迁户在门口聚集闹事,要求增加赔偿款”。
沈霍寅淡淡转身,眼里浮起冷酷清辉:“你准备好先前他们签的合约,然后联系周律师,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秘书应了一声“是”离开。
而后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喂,张局长,对,我想麻烦您些事……”
放下电话,突然心生疲倦,仿若多年前那段黑暗时光,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只短短几天便看透世态炎凉,而今当他一点一点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时,难道命运又再一次重蹈覆辙再予他一击吗?
他站在高处,一种难以言喻的寂寞袭满全身。那次意外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和母亲的双腿,以及丢失了他的爱情,而这次他当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失去的。
第二天子夜如期发出恒远二期工程的专题,出人意料的,许致远之前截住的那篇不刊之论还是被发出了。只短短一天,恒远的销售额就大幅度下降,之前买完房的部分消费者也伺机而动,要求退房。这次风波还未过去,报纸上又传出恒远的保安殴打动迁户者的事情,一时间,恒远名声极为恶劣,股票也频频下降。
报社里,几个小姑娘喋喋不休在谈论今早的新闻,言语难听,子夜没有说话,悄然抿紧了嘴角。直到“他们干这缺德事也不是这一次了,你们知道三年前那件事吧,那时候恒远公司老总的父亲不是也克扣工程材料费吧,最后好几个工人受伤,而他自己也没得到善终,听说最后出车祸死了,公司都破产了……”
话还未说完,子夜如遭雷击,“嚯”的站起身,那个说话的女子立即噤声,子夜还陷在刚才的话里,下一秒桌上的振动声将凝滞的气氛打断,子夜怔然接起电话竟是时璐。
时璐的语气舒缓温柔,“子夜,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说话。”
子夜犹豫了片刻,才轻声说:“好”。
她站在街道旁,没过几分钟,一辆黑色车在她眼前徐徐停下来,拉下车窗,时璐摘掉墨镜,向她招呼:“子夜,这里。”
她们一同坐在后车座,时璐精致脸庞略施薄脂,面容较好,眼眸盈转间带着妩媚风情,想了想,子夜还是说:“师姐,我做完这段的工作就离开这里,如果这段时间给你造成困扰我很抱歉。
时璐眼波一漾,突然叹气说:“子夜,你知道吗?就因为这样我才从来都没法讨厌你。”
她足够率真、真诚,如同一汪清透的水涌,看似涓涓平澜,却无意中驻入心田,再难割舍。
时璐自嘲一笑:“我这样大度,好像都比不上你。”侧头看她,“你误会我来找你的意思,我和霍寅不是你想那样。”
子夜目光澄静,“是因为车祸”?
时璐一顿:“是他告诉你的?”又否认摇摇头,见子夜疑惑的眼神,淡淡的微笑,“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吧”。
车子缓缓在一个白色庄园停下,藤蔓缠连在栅栏的缝隙中,郁郁葱葱的树蔓勾连在一起,反射着欢悦的白光。
时璐推开铁艺大门,蔷薇清香扑面而来,一位妇人坐在轮椅上,背靠着她们坐在藤架下,听见声音,缓缓转过身,见是时璐,暖暖一笑,“小璐,今天怎么来了?”
时璐走到她身边,“沈阿姨,今天我可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喔。”
子夜眼睛闪过一丝了然,那样熟悉的轮廓与沈霍寅如出一辙,唯一不同是脸侧线条,他的母亲更添了几分柔美。
沈妈妈早就注意到子夜了,“这位小姐是……”?
时璐俯在沈妈妈耳朵旁轻轻说:“她就是子夜”。
显然沈妈妈早就知道她了,脸上闪过一丝欢喜,热络的招呼,“来,快坐下,快坐下。”她的心情有些激动无措,看着子夜的目光里慈爱万千,让人心生亲近之意。
子夜坐在另一张藤椅上,清柔的微笑:“伯母,您好”。
简单的聊了几句,沈妈妈说:“你们坐着玩一会,我去给你们做点东西。”说完也不听她们的劝阻,一意的喊着陈嫂推她进厨房。
时璐浅浅笑了笑:“很长时间没有看见伯母有这么好的精神了。”目光投向子夜:、,“我不知道那次事故你了解多少,只是报纸上的那些舆论一点都不可信,也着实让人心寒。”
阳光慢慢沉暗下来,几缕轻悠的光线透过叶脉疏影错踪落在时璐脸上,眸光盈盈,虚晃出一抹恍惚。
“那根本不能算是意外,而是蓄谋己久的谋杀。那个人剪了刹车线,最后车撞上护城杆发生爆炸,结果却是同归于尽。”
子夜不可置信抬头,表情惊骇。
那些旧事时璐并未亲眼见到,却还是觉得惊痛,“在最后的关头,如果不是沈伯泊护住了沈阿姨,只怕现在……”只是活下又如何,一辈子在丈夫死亡阴影下生活,还要承受双腿的疼痛。如果不是挂念在国外的儿子,只怕连最后生存的意志都涣散。
她还记得沈霍寅刚接到电话的一刹那,全身失去了力气般重重摔倒在地,脸色惨白。他们乘了最快的航班回去,赶到医院后,警方带他们去太平间。寂静空洞的甬道,满是苍白的肃穆,缭缭不绝的寒气,沉重的消毒水味让她呕吐,他大抵看见了她的颤抖,拍拍她的肩说:“你在这里,我一个人进去。”他分明也感到恐惧,那双手几乎没有温度,凉如冰铁。
其实连尸体都不是完整的,那辆车上整整装了三箱的汽油,车子最后都化为了灰烬,后来只残余一些衣服碎片和贴身遗物,沈霍寅进去时间并不久,却恍若过了几个世纪,他一言不发的听着警方调来的信息。
“说来也是冤枉,沈伯伯公司的下属挪用公款,后来钱都赌输了,无力偿还,便买粗糙的材料拿来充数,结果有几名员工从升降机上掉下来,大多都终生残疾,虽然后来按国家规定给了工伤的赔偿金也是杯水车薪,那个人的家庭贫困,唯一的儿子也进了监狱,这辈子也算没了出路,伤残之后来公司闹事,那些高管把事情压了下来,就算汇报也是只言片语,最后将人逼到绝路,以那样惨烈的方式进行报复。后来报纸极力渲染这件事,沈伯伯这一世清名也算毁了。上面的专案组派人调查,但连凶手都死了,又找谁去追究。”时璐凉凉一笑,“而那个高管也不过被革了职,可是身家性命还都在。可沈伯伯一家受害者还要赔偿填补原料费和高额违约金,结果厂子倒闭,财产被冻结,房子也被拿去抵押。当真是一贫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