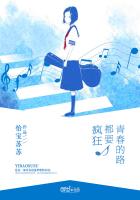潮湿的水汽和腐败的霉味从地板的缝隙里蒸发出来,在地下室狭窄的空间里弥漫发酵,赋予了这里一种阴冷滑腻的触感,就好像是溺死的女鬼,湿湿哒哒地找不到出口。
而上头的餐馆里,正是热闹的时刻,男男女女高声大笑,跑调地唱着一首首下流的小曲,酒杯互相碰撞,牙齿用力地嚼碎坚果,还有人兴奋地跳着舞蹈,使整间屋子都在跟着旋律一起摇摆。
他妈的。
酷迪亚斯半躺着倚靠在身后的酒桶上,恼怒异常。方才遭受的殴打此刻已经完全转化成了凶猛的疼痛。他咬紧牙关,努力不叫出声来,但好几次,痛感越过了忍耐的阈值,从紧咬的牙缝里冒了出来。
欢喜和苦痛往往只有一线的距离。酷迪亚斯深知这一点。在桑达找寻自己,说是联系了个对货物感兴趣的大方买主的时候,他就是如此欢快的,毕竟,没有什么比金币更可爱,更值得依靠了。
但没想到……
这些该死的杂种,竟然敢背叛我?谁给他们的胆子?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酷迪亚斯恶狠狠地想到。他的表情因此变得狰狞起来。
“你还疼吗?”
劳拉见状,关切地问道。她用一块干净的手巾裹着五六个冰块小心地敷在酷迪亚斯的脸颊上,想要用低温减轻他的疼痛。
“小问题。你不要担心。”
酷迪亚斯把手巾朝脸庞用力压了几下,他的脸庞太过肿胀,此刻已经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
真是够凄惨的。
酷迪亚斯自嘲道。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重新回顾一遍自己惨绝人寰的人生,悲惨的童年,混乱的成年,偷盗,挨打,挥霍,大醉,然后周而复始,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淹死在自己的呕吐物里,或是被像是一条狗一样吊死在绞刑架上。
他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他需要改变。
可是,竟然把希望放在一个来路不明的炼金术师的身上,希望他来拯救自己。
这也太过可笑了吧。
但酷迪亚斯是真的想要一个机会,一个能够从中解脱,重新开始的机会。
只要一个就够了。
他希望加入联合商会,从此转折,开启一场盛大的冒险,他将把它牢牢抓住,绝不让其溜走。他不会错过,不会犯错,他将用尽所有的努力……
哈勒神,米特神,米尔拉菲神,不管是谁都好,请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但没有回应,空气在流动,呼吸在照旧。没有变得有一点好转,也没有变得更糟糕。平静如常,恒定不变,好像它一百万年前是这个样子,一百万年后也还是这个样子。
这才是最让人感到绝望的,一切就像是已经被规划好了的一眼,在预定好了的时间,发生应该发生的事情,精确到分秒,精确到话语的每一个标点和停顿。
每天看起来都不一样,但实际上改变的只有日历上的数字,你在无止境地重复着,重复着,也许只有死亡才能将其终结。
酷迪亚斯长长叹了口气,他抬起头,望了望那根已经快要燃尽的蜡烛。
他的人生也同这根蜡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曾被生活那灼人的烈焰无比残忍地烤炙,现在也都已经无能为力。那原本坚实的身躯和意志都已经软化,变成了一坨软烂的物质,很快又会化为一滩脓水。
“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到外面走走吧,这几天天气还是很暖和的,我们可以采些果子,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
劳拉为了让酷迪亚斯振作起来,不断地找着些话题,说着安慰的话语。
但是酷迪亚斯不在乎,他只想改变这一切,他受够了这样。
他当然要笑,要装作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以此疯狂地嘲弄这个世界,以此假装自己无所畏惧。
但他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又丧又恼,他只想往上爬,他想变得有钱,他想没有烦恼。只要能够实现这个愿望,那些该死的神灵想拿走什么都可以。
可这是不可能的,神灵从来不会听取人们的心愿,他们只会看着自己的造物自生自灭,心里却连一丝歉意都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创造这个世界呢?
“走吧。我们回家。”
酷迪亚斯摇了摇头,他已经放弃了那不切实际的梦想,人生根本就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在你还是一颗滚烫的精子的时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下来。
你所能做的,就只有随波逐流罢了。如果你心怀不甘,想要抗争,那么当然可以这样做,你会怀着雄心壮志,会泪流满面,会有一种无限接近于改变现状的错觉,最后却还是同样的结果。
残忍吗?残忍。
可是能够改变吗?不能。
酷迪亚斯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而现在他需要考虑的是些更实际的问题,比如明天的面包,比如冬日将近,应该给劳拉买上几件御寒的衣物。不能再让她琢磨着采摘那些水果充饥了,她得和别的女孩一样**烤的面包,吃肉,喝葡萄酒。但不知怎的,蒂尔斯最近有些萧条,没有什么商机,他想,是不是应该到城里寻觅一下机会,那里有钱的大老爷多的是,少了十几二十个金币,也不会感到心痛……
算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酷迪亚斯苦笑,但这悲伤的表情又牵动了那肿胀的脸颊,麻木和屈辱的感觉,使得愤怒再一次爆发。
妈的。
他飞起一脚,踢在酒桶上,木桶沉重地落地,从里面吱吱跑出了几只肥硕的老鼠。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从上方传递了过来。说来奇怪,周遭的环境是那么的嘈杂,但从脚步声一出现,酷迪亚斯就精确地将其锁定了。
好像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东西,是命运之神给他的信号。
酷迪亚斯咽了口唾沫。他有一种预感。
一种强烈的预感。
果然,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穿过了桌椅,穿过了吧台,他停了下来,是在询问地下室的方位。
他又开始走动了,他打开了门,长长的回音降落下来,惊起了堆积的灰尘。
“是谁?”
劳拉警惕地问道。
酷迪亚斯没有答话,满心都在倾听,他兴奋得浑身都在颤抖。
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它一阶一阶地向下走来,靴子的后跟在敲打着腐烂的木质楼梯。
他来了。
他来了。
一秒,两秒,酷迪亚斯已经很久没有感觉过时间如此漫长的流逝了,它被放慢,被拉长,好像没有终点,好像是个被抻长的口香糖。
终于在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之后,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
弗莱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