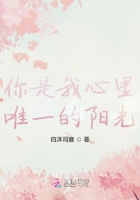【孙鹏】
2015年5月10日波兰科沙林天气多云,夜晚有雨。
海上飘了一个月,逐渐习惯了船上的作息,波罗的海的西风依旧凌冽,海面上拉雾频繁,很多时候我都辨别不清船的驶向,上船前就听闻这片海域冬季容易结冰,于是思维惯性后以为真的被困在了海上,思维世界里我们被困在原地没有前行。
倒是跟海员们混的很好,船员大部分是丹麦人跟,瑞典人,少部分波兰人跟德国人,而我是船上唯一的黄皮肤。开始他们以为我是商人,后来简单的交流几次明白过来我只是个游客后来关系熟了以后就跟他们称兄道弟,抽烟喝酒玩扑克。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波兰人,大家称呼为‘A’,因为他扑克玩的极好,船上的能赌得东西除了钱还有烟、酒和女人。大伙的好烟跟私藏的酒全都输给他了,他就全部分享出来,每天大伙都醉醺醺的,宛如刀口舔血的海盗,只为这一晚的快活。
货船上很少有女船员,我们船上就没有。打牌的赌注之所以是女人,无非等上岸之后输家能带着大伙逍遥快活。
船员们都很照顾我,无论谁输谁赢我都有烟抽、有酒喝;可他们不让我碰牌局。‘A’将他的手竖起来说,“知道为什么我的小指少了半截吗,我在米兰赌输了,数额太大,只好切掉半截小指才能作数。”一旁的波兰人取笑道,他听这个缘由已经到长出耳屎的地步了。
其实我也没想玩他们的牌局,其一是本身对牌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他们的局我也不会,你让一个玩斗地主都不怎么熟练的九零后跟一帮赌徒玩牌就好比一个没驾照的骗子跟职业赛车手谈笑风生,等到真的上场会输的尿裤子。
再者,我厌倦赌博,因为长这么大好像从未赌赢过。
烟抽完了,酒喝完了。娱乐的措施好像都没了,但是还有一个星期才能上岸,我不禁发愁起来,为他们。
说实话,我是一个耐不住性子的人,可能是心里的包袱一下子没了后反而清净了许多,像一位无欲无求的苦行僧,发呆是最好的修行。相比之下船员们不一样,海上的日子过的久了,思考反而是一种痛苦,毕竟懂得道理越多,人生也未必过得很好。
于是大伙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一个个饱经风霜的男人交谈起来却并不严肃,谈论最多自然是女人,在这儿风雨漂泊的航线上,似乎聊起女人便充斥着温暖。
德国人莱特说,“女人是毒药,好在国家没有将他们禁止。”
我听到不怀好意的笑声,本来只是偷笑,不知谁没忍住,大伙也都笑了起来。
“可快算了吧莱特,你这可怜的穷鬼,会有女人看上你?”说话的人是‘A’。
“你一个波兰的穷鬼也好意思嘲笑我?你让大伙看看,论长相我哪点比你差。”
“哈哈哈莱特,你难道有很多相好吗?”
一旁的查理连科插嘴,“那可不,据我所知莱特的儿子遍布整个欧洲呢。”
大家哈哈大笑,莱特骂了一句脏话后也笑了起来。我也跟着咧嘴笑,这时候要有酒就好了。
“D,你有过女人吗?”我在这被称呼为‘D’,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这样称呼我。问话的是查理连科,他虽然是大嘴巴,喜欢乱开玩笑,不过不带恶意,只是调侃。
我还在组织语言,准确的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但在这方面我只是毛头小子,只听过见过没做过。
‘A’说,“怎么着,查理连科,上岸之后你打算带他开荤?”
“有啊,还不止一个呢。”我装腔作势,额头抬得很高,下巴跟查理连科的大鼻子齐平。
人群中爆发出哄笑,自发的,无组织性,笑的我心里发慌,海上的雾气包围了我,潮湿的感觉萦绕全身,我想吐;胃里好像都是水,惊涛骇浪。
这粘稠感让我想起了2014年的夏天。
“孙鹏,抱着我。”李瑗馨在我大学附近的旅馆里开始脱衣服。她裸露的皮肤上我看不清毛孔,跟白纸一样,我不敢碰她,白纸揉皱了可就无法舒展了。
夏季的广州炎热潮闷,此刻我全身上下冷到极点。后来这个毛病一直留到现在,只要紧张,全身就不由自主的颤抖。
面前的女人已经开始解她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扣子,理智使我冲上前抓住她的胳膊。彼时我俩离得很近,她白白的,像一块从水槽中取出的豆腐。
我似乎用力过狠,被我握紧的纸片染出了血色,我想卸下手中的力,可是不知道是大脑不听神经使唤还是神经不受大脑控制。
“别这样。”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下意识的咽了口水,样子想必十分滑稽。
她没有说话,摇晃着脑袋笑着看我。我被盯的心里发慌,额头的汗也兜不住了。
“把衣服穿上吧,我出去抽根烟。”
“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以前也是,现在也是。”
“什么怎么想的?你觉得我只想跟你上床?”我皱眉头的样子很凶,好多人都建议我别皱眉。
面前的女人双手支撑在床上,“至少我觉得你不应该拒绝我。”
“你说话的语气搞的我是女的、你是男的一样。”
“哈哈哈哈”李瑗馨的笑声跟被刻意摇响的铃铛一样,做作、愚蠢。
“别笑了。我回去了,明天有实验课,不能请假,你自己去火车站吧。”
“一天的实验课?”
“嗯,一天的实验课。”
“好吧,那你走吧。”
真痛快,不拖泥带水,即使你知道我说的是谎话也不拆穿。
“真让我失望,上大学后很多人想法设法的睡我,我没有给他们机会。现在我送到你面前了,你却要逃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比我能洗脑?有那么几秒我也觉得我不是个东西,我应该转身过来扒光你全身的衣服,在你挑逗的笑容下蹂躏你。可能‘蹂躏’有些过了,可是我一看你脸上的笑我就觉得烦,胸口有火想上去扇你一耳光,真他妈的不爽。”
说罢,我从房间了走了出去。说实话,如果李瑗馨不说那句话我可能会在宾馆的台阶上坐一晚上,等第二天她起来后能被我的举动而感动,最好能掉几滴眼泪,这样我能顺势把她揽入怀中,多么美妙的情节啊;其实也不用她哭,只要能看到她委屈的表情我就很心满意足了。可现在想想自个可真是个傻缺,本以为是偶像剧,却成了恐怖片,那个女人早就成了狐狸,我还不知好歹的给她全身刷白漆,指望成为一直只吃胡萝卜的乖兔子。
越想越气,我给宿舍的哥几个打电话问他们在哪个摊吃夜宵。去了之后,有人开玩笑说鹏哥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是不是身体不行啊!
我没搭话,一瓶酒的功夫后我实在忍不住就问室友什么是爱情。
他们笑我傻缺,嚷嚷着跟我碰杯。
那天晚上夜过的漫长,室友们变得特别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