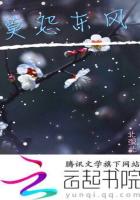郡仙王咽了下口水,刚才抡斧的壮汉腿肚子也在微微颤抖。
“凌将军,忘了平日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间大将军月峰从后面走出,来到郡仙王面前,躬身行礼,说道:“卑职拜见郡仙王!”
“哼,月将军,这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将士?违抗大王上谕,抗喻不尊,好大的胆子!莫非那胡人封官许愿,许了你月将军多少好处?”
“仙王,这话可不能乱说,卑职从未与那胡人有何勾结,一腔热血只为大王效忠!”月峰没有抬头。
江边渐渐起了大雾,雾气从远处江边袭来。
郡仙王说:“月将军,你我同为武官,也算同僚一场,还请月将军不要为难本王,跟我们回亲天府走一趟吧?”
“月将军,不要啊,这一去可就凶多吉少了!”
“是啊大将军,这是他们下得套,将军千万不要上当。”
“对,大不了,咱跟他们拼了,鱼死网破!”
郡仙王一听,见月家军群情激奋,军中哗变一触即发,连忙斥责道:“月峰你自己听听,看看你部下这态度!还要我多言语什么?你们这…这不是造反,是在干什么?”
“凌将军,带士兵们回营。”月峰转头望向马上的郡仙王,说:“仙王,我跟你们走!”
“呵,算你识相!”
周围又是一阵哗变,月峰大吼一声:“这是军令!”
凌花飞两眼噙泪:“诺!”
月峰扭头跟着郡仙王踏上了回凤洲城的路,大雾飘散过来,淹没了凌花飞和部下的身影,郡仙王带着月峰越走越远,消失在重峦叠嶂的山屏中,只留下马蹄声。
远处的江边上随风而来一声又一声的渔号子声,悠扬高坑。
月峰不在的日子里,凌花飞白日练兵,夜晚则一人走到江边,席地盘腿而坐,背对军营,面朝滚滚长江,左手一壶酒,右手抚琴,彻夜长弹,弹不尽对大将军的思念。
殊不知,军营周围的密林里有好几双眼睛正监视着凌花飞的一举一动,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八百里加急传讯回亲天府。
凤洲城内,茶坊内、酒楼间、说书房、大街小巷串门的阿嫂、卖糖葫芦的货郎、贩夫走卒都在传论着一个话题:月将军被亲天府的人绑回来了。
“哎哎哎,你们都听说了没?月将军通敌!竟和胡人有一腿!”
“现在凤洲城谁不知道这件事?不过,你们相信月将军是那样的人吗?”
“我不相信,月将军可是条好汉,从没依仗自己势力欺负咱们这些平头小百姓!”
“话不能这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们没听说过?月家军有个吃人的将军,叫叫叫啥来着!”
“小阎罗!对,就是他,哎,攻城之后屠城殆尽,还吃生人肉,简直是人间炼狱那,啧啧。”
议论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凤洲城一小茶馆内,角落里,一头戴斗笠黑纱蒙面的人独自品着一杯香茗,仔细听着周围人的一言一语。
店小二见他一人坐着,想过去招呼招呼,问道:“客官,可还需点些糕点?本店新出了自家酿的桂花糕,酥软可口,入口即化,与客官您面前这壶顶好的龙井,那是绝配那!”
“滚。”
声音虽轻,却透露出不可抗拒的威严。
店小二自讨没趣,整理了一下戴歪的帽子,弯着腰,夹着托板灰溜溜了离开了,走到楼梯间,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刚才喝茶的那个客人。
“咦?人呢?”
原先坐着斗笠蒙面人的地方空无一人,只有一盏杯子放在桌上,旁边排着几丁碎银。
“好奇怪的人。”店小二自言自语说到。
亲天府正堂,监正司长国二公主坐在太师椅上,问前面跪着的人:“山魁,审得怎么样了?人,招了吗?”
山魁猥琐又邪魅的一笑,脸上肥肉将眼珠子全包了进去,回话道:“禀正司大人,那老骨头可真他娘的够硬的了,打折了我十数根杀威棍就是不招。”
“用刑了没?”
“嗐,别提了正司大人,能用的全用了,那老头身上现在是找不到一寸好皮肤,可…可就是硬的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宁死不招。”
监正司眉头皱了皱,说道:“再审,半个时辰后再来找我。”
山魁领命而去,监正司寻思着等的时间总归要找点事情做做,心里也有些莫名的烦躁,便命人取来文房四宝,自己一边磨着墨,一边若有所思,接着摊开宣纸,挥毫落笔有云烟,徐徐而书,字体苍劲有神韵、力透纸背,笔缝处龙蛇腾跃、雄健又不失洒脱。
正司大人的书法江湖早有说法,宁得秋蝉一字,不要黄金万两。秋蝉是正司大人的名字,单姓黄。
一炷香的时间过了,山魁气喘吁吁的走了进来,见正司大人挥毫泼墨,不好打扰,便站在一旁,候着。
直到山魁身子前后微微摇晃,头开始上下点动,嘴角边的哈喇子也渗了出来,监正司才放下笔,问道:“招了?”
山魁摇摇头,道:“招,招个屁。”说完才发现正司有些愠怒,杏眼瞪着他,山魁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声音小了些:“那老王八,我敲光了他所有的牙齿,打得他全身上下没一根骨头连着,可…可就是不招,自认对大王忠贞不二!”
正司黄秋蝉听了山魁的话,没着急回答,而是拿起了刚刚写的字,问山魁:“烦请山大人掌掌眼,我这字写的如何?”
山魁眯着眼左看右看,眼泪都快下来了,哭着求饶道:“正司大人你就别取笑山魁了,在下就一粗人,打小就没念过几个字,你让我杀人还行,这识字…就。”
“罢了,带我去地牢,我倒想看看,这月将军的骨头能有多难啃?”
监正司黄秋蝉与山魁一道离开了亲天府,风起时,掀开了她的披风,也吹开了她刚刚泼墨完成的字,杀人诛心。
阴暗潮湿的地牢里,斑驳老旧的四壁爬满了青苔,空气里都充斥着发霉的酸臭味。
监正司跟随山魁走到地牢最深处,这里重兵把守,别说一个大活人,就是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月峰两只手被铁链悬空锁住,一只大铁钩从背后勾住他的肉,脚脖子上则束缚着俩千斤大铁球,月峰脑袋歪垂,好似睡过去一般。
正司黄秋蝉想靠近些,山魁好心提醒道:“大人小心,小心…有诈。”
黄秋蝉鄙夷地看了山魁一眼,没有理睬他,径直走到月峰面前:“月将军,好久不见。”
月峰微微睁眼,见是亲天府监正司,笑了笑,不说话又闭上眼睛。
黄秋蝉踮起脚尖,附在月峰耳畔,轻声细语说了些话,月峰眼睛再次睁开,只不过这次眼神没了之前的锐利,盯着黄秋蝉看了好久,嘴微微张开,叹了口气又闭上眼睛。
黄秋蝉走了出来,到了山魁旁边时候停住脚步,说:“把认罪书再给月将军送去。”
山魁摸了摸后脑勺,有些不明所以。
黄秋蝉皱了皱眉:“要本司重复第二遍?”山魁连忙扯过桌前的认罪书奔向月峰。
地牢里因为正司黄秋蝉的光临而多了一丝花香味,精雕细琢的美人脸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黄秋蝉走出地牢,深深吸了一口空气,慢慢吐出来,如此往复循环吐纳了好几次。
“神了!神了!大人您真厉害!神了!神了!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山魁跟着从地牢里跑出,手上挥舞着月峰的认罪书。
山魁身形壮硕,跑起来地动山摇,冲到监正司黄秋蝉面前,立马刹住狂奔的脚步,却刹不住四下扬起的灰尘,引得周围守卒一阵咳嗽。
正司大人,他…他认了!”山魁恭恭敬敬将月峰的认罪书双手奉上。
皱巴巴的宣纸上,详细记录着亲天府审问月峰的口供,如何通敌胡人等细节应有尽有,详细描述记录在纸,落款处,两个血红的大字:月峰,刺眼夺目,是月峰用自己身上的血水签字画押,血水未干,沿着字迹向四处散开。
黄秋蝉没有接过这张认罪书,说:“行了,既然月将军认罪了,将他擦洗干净换个囚室好生招待,怎么说也为我大长国立过战功,走之前也让他走得体面些。”
山魁又是一脸惊讶:“这…这…正司大人,一个叛党,干嘛要对他这么好?”
“你也想违抗我的命令?”
“奴才不敢,只是…”山魁叹了口气,说道:“诺!”
山魁接着问道:“正司大人,在下实在是有个问题憋在心里,不吐不快!”
“说。”
“大人您是使得啥神仙法子,跟他都说了些啥?这不打不骂就让那老头给签了认罪书?真是神了哎?”
黄秋蝉
……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夜凉如水,北疆月家军军营内,凌花飞和军中几个伍长、什长围坐一起,蚕豆大小的烛火微弱,随着众人的呼吸摇曳不稳。
“钱伍长,消息打探到了?”凌花飞小声问到。
“千真万确,大将军,他…他认罪了,午月问斩!”
“怎么办?凌将军?大将军素来带我们不薄,我们…我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凌花飞冷眼看了几个人一眼,说道:“救是肯定要救,这个法场,凌某劫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