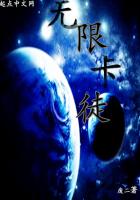宋未名。
我躺在床上,回想几个月前,删掉他的电话号码、微信和QQ时,态度坚决,情绪激动。即使他留给我的是屈辱,我仍然承认,他是我的初恋,始终无法轻易放下。
翻过身,再次取来手机。这条短信透着诡异,真不像是人写的。即使是人写的,他的神经也应该是出了问题。
如果不想让我轻易读懂,短信应该写的难一点,比如用法语或者莫尔斯密码来写。现在这样算什么呢?我一眼就能读懂,除了诡异,没有其他感受了。
哦,对了。几个月不来往,我竟然忘了,在宋未名的心里我根本微不足道,怎么会值得他花功夫来取悦我?还法语,莫尔斯密码?一不小心,我又高看自己了。
既然这样,为何不直接用汉字,难道是手机输入法坏了?我摇了摇头,觉得这个借口很可笑。看看他写的内容,“好想你”、“有很多话想对你说”,除了想再玩一次暧昧,我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
在他看来,我就这么好糊弄?一次不够,以为我还会蠢上第二次?呵呵,怎么可能呢!
放下手机,重新躺平,合上眼。我不会让自己再当备胎,也不会为了这件事再撕心裂肺,甚至不会再浪费时间去想。一切到此为止。
---------
两天后,我和老妈买了姥姥爱吃的蝉蛹、姥爷爱吃的牛肉,去看他们。
姥姥家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楼房建于七八十年代。走上第五层楼梯,一条穿堂的走廊,住着十几户人家。每家门前都堆满了杂物,有自家不用的破烂,也有从外边捡回来的破烂。一大堆破烂,遮住走廊的小窗,黑压压地分不出每件到底是什么,只是都蒙上了厚厚的灰。
走廊的宽度仅容得下一人,闷热无风。快走到尽头,便到了姥姥家。一扇生了锈的铁门,上面贴了一张大大的福字,福字下还印着“百姓超市恭贺新禧”。
来开门的是姥爷,比上次见他时黑瘦了一些。
“怎么瘦了,还晒黑了?”我跟姥爷打招呼。
“嘿,天天出去溜达,一天能走上三圈,就沿着河畔公园。”姥爷说话是山东口音,在东北生活了几十年,都没变过。
我边说边走进里屋,一股“老人味”迎面而来。中午的阳光还没完全射进来,屋子不够亮堂。姥姥背对着窗户坐在里屋的床边,她的脸在阴影里,看不清楚。
“姥,我来看你了!”我笑着向她走过去。
姥姥抬头看我,说:“谁啊?”
我侧着身,坐在她边上,攥着她的手,说:“我,乐乐!咋的,不认识啦?”
她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笑着说:“哦,乐乐,你放学了?”
“放学了,也放假了?”
“放假好,放假好。考试考得好吧?考不好,你爸可要揍你的。”
“考得好着呢!”
她嗯嗯地点头,转过头去看我妈。看了一会儿,也不说话。
她看起来和年初时没什么差别,反而白了许多。她始终没有一丝白发,满头黝黑黝黑的,像是不曾老。但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一条连着一条。身上瘦瘦的,穿着长衣长裤。我摸着她的手和手腕,肉很少,一层薄皮下是清晰的筋骨和青色的血管。
隔了好半天,姥姥扭过头,看着我说:“珍珍快读初三了吧?”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满是期待。或许是想了很久,她才想出一句觉得是正确的话吧。可是,她把我叫成了我的表妹,她的孙女。
“姥,我是乐乐,不是珍珍。我都读大学了,开学就大三了!”
“哦哦,对,是乐乐。你看我,哈哈哈!”她不好意思地大笑,露出满嘴的牙,“你看我,脑子不好使了。哎呀!”
姥爷坐在八仙椅上,冲着姥姥说:“你说这人,怎么说傻就傻了呢?”
老妈一边收拾屋子,一边说:“爸,我妈她这是病,不是傻,是病!”
姥爷叹着气,不再言语。
---------
一会儿工夫,大舅二舅和小姨,几家人都来了。屋子显得更加狭小,憋闷。
两个舅妈和小姨在厨房做饭,两个舅舅和姨夫喝茶闲聊,我们几个小孩就在床上玩扑克。姥爷始终坐在八仙椅上,抽着旱烟,看着一大家子人。
老妈一直在收拾屋子,最后要整理衣柜。姥姥看她把自己的衣服从归里搬出来,就没头没脑地喊了一句:“你别动!”老妈说:“我不拿你衣服,就给你洗洗!”姥姥显然不高兴了,走过去,扯着她的手臂,说:“别动,别动!”老妈被拽了一趔趄,我赶紧去扶她和姥姥,却意外闻到那叠衣服带着一股味,说骚不骚,说馊不馊的。老妈只得把衣服放回衣柜,说:“你害臊啥,又没外人!”姥姥看她不再搬衣服了,才不好意思地笑着坐回床上。老妈还要说姥姥,我赶紧阻止:“别说了,妈!”
姥姥,一生好面儿。如今看来,就算记不清人了,糊涂了,也还明白什么事是丢人的,不能让孩子们知道。
菜做好上桌了,一大家子人围着拼起来的两张桌子坐下,倒酒的倒酒,倒饮料的倒饮料。
小姨说:“我姐夫啥时候下班?等他一会儿吧。”我妈说:“他说在路上了。咱们边吃边等!”于是,她俩张罗着大家动筷吃菜。我舀了勺西芹虾仁,递给姥姥和姥爷,姥姥不抬头地只管吃,姥爷说好好,你自己吃吧。
席间,不知道是谁,说起姨夫的饭量大。姨夫人好,跟谁也不生气,还逗姥姥,说:“妈,他们说我吃的多,你说我吃的多吗?”姥姥起先没听清,说,你说啥?姨夫又问,我吃的多吗?姥姥先是呵呵呵地乐,嘴里的菜还没咽下去,等咽下去了,她还在乐,边乐边说:“可不多嘛,当初要知道你这么能吃,二姑娘都不敢嫁给你!”她这语气特别神,逗乐中带着吐槽,吐槽中又带着一家人独有的亲密,真是一句话就透着几十年的智慧。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姥姥看看大家,好像明白了,孩子们喜欢听自己说话,所以她的神色终于有了一些清明,那像是几分得意。姥爷也嘿嘿地笑,边笑边给姥姥擦了下嘴。很快,大家聊起了别的话题,姥姥神色中的清明也渐渐没了。
---------
饭快吃完时,老爸终于到了,还拎着几盒补品。大家一一招呼过,然后吃完了饭,大人们留在客厅喝茶,我们小孩在里屋,陪着姥姥和姥爷。
两个表弟捧着手机玩游戏,我和表妹珍珍聊着明星们的八卦。只听客厅那边传来了小舅妈尖尖的声音:“我家可不行!孩子正好小升初,我们可分不出身管爸妈!”我一听,气氛不太对,就走过去,扒着门缝瞧。
客厅里,大人们围着饭桌坐了一圈。老妈和小姨明显生了气,歪着身子,不看小舅妈。男人们默默地喝着茶,都不知声。不一会儿,大舅妈也开了口:“我家倒是可以,珍珍住校了,我又没上班。不过呢,我自己爸妈那边,得隔一天一过去。真要把这老两口自己放家,我也不放心。你们说是不是?”说完,她看向四周,见没人搭她的茬,她就碰了碰自己老公,我大舅。
大舅一看躲不过去了,就放下茶杯,跟我妈说:“姐、姐夫,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三家每月给你们钱,你们来照顾爸妈。毕竟呢,现在乐乐上大学了,你们照顾最方便。”老妈一听,一拍桌子就要开骂,老爸赶紧拽住老妈,让她小声点,别让里屋听见。老爸想了想,说:“我们照顾没问题,钱就不用你们给了。”老妈气得说不出话来,平时怼我的能耐一点发挥不出来。
两个舅妈见我爸同意了,还不要钱,就开始夸我爸,又说自己家的确有难处,不是不愿意照顾。
小姨实在看不下去,指着我那两个舅舅说:“你俩真行,有钱是吧?要媳妇不要娘了,是吧?”两个舅舅低着头,喝着茶,也不知声。两个舅妈臭着脸,挨在自己老公身边,气哼哼地听着。
姨夫扯了一把小姨,让她别说了,然后对我妈说:“姐,咱俩家轮流吧,爸妈在哪家呆腻了,就换一家。你看行不?”我妈压着胸口,点了点头。
小舅妈一看事情解决了,立马笑着说:“辛苦两位姐夫了!我们也不会不管的,你们要是有啥事照看不过来,说一声,我们立刻到位!”小舅跟着点头,老妈和小姨一眼都没瞧他。
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我正回头去看姥爷和姥姥,怕他们听见了,跟着上火。谁知道,大舅妈这时候又说话了:“姐夫和妹夫好样的,是没错。不过有句话,咱们还是说在头里的好。你们照顾爸妈,如果让我们拿钱,我们二话不说。但是,爸妈每个月开到手的那六千多,可是爸妈的钱。”我一听,真想冲到客厅,拿起个茶杯,摔她面前,让她闭嘴。
只见老妈抬起手指着大舅妈,冲着大舅说:“这话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图爸妈的钱?”大舅妈见大舅没反应,接着说:“图不图的,谁也不知道。所以,丑话咱还是说在前头,要是真孝顺啊,就别用爸妈的钱。”老妈气得浑身发抖,小姨气得叉着腰站了起来,嘴里只说着“你你你”,说不出别的。
我正扒着门缝看,谁知身后的姥爷一下子拽开了我,打开门,喝道:“我们的钱我们说了算,谁也管不着,谁也都别惦记!”
我看着姥爷的背影,他垂着的一支手拿着旱烟,另一支手攥成了拳头,两条宽松的裤腿儿耷拉在脚后跟,后背挺得比平时直,但还是佝偻着。
大舅妈显然被吓到了,声调软了许多,说:“爸,我不是……”这时,大舅终于说了句人话:“行了,别说了!”大舅妈这才闭了嘴。
姥爷一把关上门,走回了里屋。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老妈推门进来,催我说,赶紧收拾东西咱回家。然后她又跟姥爷和姥姥说:“今天先回去了,过几天来接你俩。”
------
我家和小姨家,六口人往外走,姥姥也跟着出来送,她拽着我们,问:“要走了?”我们说:“走了,过几天来接你。”她就嗯嗯的点头,一直送我们到楼梯口,才被姥爷拽住。
我走下楼梯,看姥姥伸着脖子还在看我们,我就说,姥回去吧,别送了。她也不走,冲我摆摆手。我又说,回去吧,姥。她抬起手,擦了擦眼睛。
走到街上,小姨一家开车先走了,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老妈靠着老爸,呜呜地哭起来,我拽着她的胳膊,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也被气得只想骂人。
老爸搂着老妈,往家的方向走。我跟在后面,有好多话想说,却不知道该说给谁。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直接翻到赵九正,写了一句:人生这么短,分别这么长,欠下的情这么多,能还上的却又太少。
写完,就直接删了。矫情得可怕。
正要收起手机,我想起了那条用汉语拼音写的短信。我突然看清了它,那么荒谬又没有诚意。我把它找了出来,拉黑了电话号码,然后删除。
这世界上,有很多无情无义的人,一不小心,遇上了,并不是我们的错。但是,要记得,那些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在意,更不值得我们流一滴眼泪。
我快跑了两步,赶上了老爸老妈。老妈已经不哭了,我和老爸逗着她,一家人往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