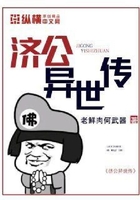钟棠哭了一夜,第二天到学校时几乎是通红了一双眼,惹得整个班级的人都纷纷侧目。傍晚放了学,她却仍旧不愿回到那座半山上的别墅,索性让司机载着她环城绕了好几圈,一直绕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才不情不愿地绕回了家。
别墅之中灯火通明,沈歌前已经先她一步回了家,他仍旧坐在沙发上,和平日里略有不同的是,此刻那张硕大的白色沙发之上,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池微漪。
“你回来了。”他看都不看她一眼,淡淡道,“正好,我也想告诉你,我和微漪已经准备挑选新婚场地了。”
钟棠明白他是有心气她,干脆不作声,转身就要上楼,却被沈歌前一个闪身站起,再度拦住去路。
“我已经打过电话给你母亲,告知她顾弦如今的状态,并说明了你对我的心意,我相信很快,她就会要求你回美国。”
钟棠一双哭得血红的眼睛蓦然睁大,难以置信般地用力瞪住他,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一丝一毫的不忍或无奈,可是,都没有。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比以前更冷淡。
而他刚刚的话……
他分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心意了!
钟棠闭上眼,许久之后,终于生生扯出一个冷笑来。
“沈歌前,你够狠。”
那天夜里的钟棠,仿若周身都坠在冰渊之中,她躺在床上,却分明感受不到一点温度,四肢乃至全身都是彻骨的寒冷。
如果说先前没有父母陪伴的她只是一头乖张的小狮子,那如今的她,就是一条锋芒毕露的毒蛇。
这些日子里,她几乎都要忘怀自己先前究竟为何执意要跟随沈歌前,为何执意要住到他家来……
她原本以为,她可以为他放弃那些计划的……
如果说先前她还有一丝一毫的不忍心,那么今天的沈歌前,就彻彻底底地催化了她的恨意,那恨意被放大、发酵,最终逐渐滚成了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要将她这个人都吞噬下去。
她终于还是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电话。
“让你之前找到的那个人,去吧。”
她平静地说完这句话后,就让目光放肆去追寻屋顶闪烁的点点蓝色灯光。暗夜之中,她只觉得那灯光好似是泪滴——一滴,一滴,又一滴,无穷无尽,生生不息。
第二天,钟棠从学校出来后,一如既往地上了自家司机的车,可司机叔叔却不似以往那般立即发动引擎,只是略带探寻地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了句:“小姐,沈先生说,要您立即去医院。”
钟棠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整理背包的手没有一丝停顿,只是平静地问道:“出什么事了吗?”
司机欲言又止道:“是顾弦小姐,她出事了……”
顾弦出事了。
钟棠忽然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因为这件事,原本就是她干的。
——她从很久以前,久到她第一次见到顾弦,就在酝酿着这样一个局。
彼时顾弦以那样决绝的姿态回绝她,以她的个性,必然不会那样轻易就善罢甘休。可之后看到沈歌前的眼神,她却忽然确信,沈歌前对顾弦,是有情的。因此她十分好脾气地退出了顾弦的住地,还死缠烂打地转学来了中国,住到了沈歌前的房子里。
这些日子里,她已经旁敲侧击地从沈歌前口中打听到了顾弦那个故去爱人的大致信息,她专门派人前去调查搜寻,就在前不久,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同那故去之人有着十分酷似面庞的男人。
她原本是想要让那个男人前去偶遇顾弦,顾弦有着那样深的执念,倘若看到一个同她心心念念的故去爱人有着酷似长相的男人,难保不会重新爱上他,并且振作起来。假使计划顺利,那她便能顺势让顾弦收自己为徒,教习自己大提琴。
钟棠以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天衣无缝。
如果真要说其中出了什么差错,那就是她没能想到,有朝一日,她竟然会赔上自己。
她爱上了沈歌前。
她甚至想要为了沈歌前,放弃这个计划,可他偏偏要刺激她。
她终于还是让那个男人去找了顾弦,可顾弦的自持力显然同他们预想当中的不一样,她明确地同那人说,你不是他。那男人收了钟棠的一大笔钱,倘若空手而归,必然没法向钟棠交代,走投无路之下,竟然企图强暴顾弦,顾弦大喊大叫,最终被同幢楼的邻居救下,那男人也被警察抓走。
可顾弦却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整个人竟然都变得疯疯癫癫起来。
司机平静地望着后视镜,向她讲述完这件事,钟棠缓缓闭了眼——说起来,这件事的始作俑者,终究是她。
她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道:“去医院吧。”
钟棠赶到的时候,沈歌前已经在病房里陪着顾弦。
顾弦,那个她只见过一面的顾弦,此刻正站在加护病房里,病房的窗户大开,淡色的窗帘被风吹得鼓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说也奇怪,别人神经失常,都是上蹿下跳地闹个不停,她却只是站在那里,站在大开的窗户面前,揪着窗帘,把自己掩在其后,无声地流泪。
沈歌前站在她身后,看起来悲伤得无以复加,他凝视她半晌,终于抑制不住,忽地伸手将她抱进怀中,搂着她的那双手不敢用力,但钟棠却分明看到,那过分好看的一双手上青筋暴起,应当是心疼得紧了,可他只是轻声道:“没事的,没事的。”
钟棠站在窗外,加护病房外那扇硕大的窗户是面单面镜,她站在那里,屋里的两人完全不知她的存在,她几乎是颤抖地伸出手,隔着一扇窗,细细描摹他的轮廓。
他看顾弦的眼神,分明是从来没有放下过。
初识时她同他说,希望他放下顾弦,他微笑着应下,可事到如今,她才知道,他从来,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
她原本已经想通,她甚至可以接受他被迫结婚,可以接受他放弃作曲,却唯独无法接受,他从头至尾,心里都只有另一个人。
那样的眼神,是他对她从来没有显露过的。
可她却分明已经见过两次。
一次是她初识他,他凝望窗边转过身的顾弦,一次就是今天——事到如今,他依然是用那样的眼神看着顾弦。
两次都是顾弦,她就像是他心底的白月光,年年岁岁,永永远远,都是他最不可触碰的那根软肋。
而她不是顾弦。
她终于明白,无论她多努力,陪在他身边多久,他的心之所向,都不会是她。
有个护士兴许是听了沈歌前的吩咐,看见她站在外面,就进了病房,同他耳语了一句什么,沈歌前这才松开顾弦,哄着骗着将她拉到病床上,又安抚了许久,顾弦才勉强睡着。
他小心翼翼地退出病房,而后走到钟棠面前,二话不说就扯着钟棠的衣袖,直直地将她往病房走廊的尽头拖。这个过程之中他始终沉默着,双目血红,眼神凶狠得仿佛他拖着的是个什么十恶不赦的人。
钟棠心中有愧,加之他力气极大,她根本挣脱不开,只能任由他拖着。
可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她的印象之中,他对她似是永远温和,永远宠溺,即便对别人生气,也能在再度面对她的时候堪堪地笑出来,从来没有像这样一般……
——仿佛一个陌生人。
及至走到尽头的窗前,他才终于站定下来。
钟棠站在他身后,眼睁睁望着他瞪着一双好看的狐狸眼,可那双眼中如今已再无柔情缱绻,取而代之的全是危险仇恨。他转过身子,那样好看的一张脸上如今堆积了满溢的愤怒,几乎是没有一丝犹豫,就高高扬起了一只手臂,直直地冲钟棠挥过来。
钟棠愣了愣,终于闭上眼,准备好承受这样一次痛击……
可是没有,整整半分钟,钟棠都没有等到预想中的疼痛,她睁开眼,就看到他的手悬在半空之中,终于还是颓然地放下。
沈歌前望着她,自嘲地笑起来:“是我错了,我太过宠着你,惯着你,才让你有恃无恐,让你连这种事都敢做……钟棠,我忽然发现,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地了解过你。”
“你明明知道,她都已经隐居在那里,连最爱的大提琴都已经放弃了,你还要这么伤害她吗?你到底是一个小姑娘,还是魔鬼?”
钟棠心中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却还是不敢相信,她着急地同那人辩解道:“你究竟是听说了什么?”
沈歌前却已经不再看她,将身子半倚在医院那冰冷的墙壁上,看起来已经十分困倦。
“我听说了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之前说,你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我错了。你不像任何年纪的人,你心里只有自己,我从来,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么狠毒的人。”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像是有谁在暗无光日的天际划了一道口子,漫天的瓢泼大雨一下子全部倾泻出来。
沈歌前从她面前迈着大步离开,钟棠却再也没有办法同往常一般伸出手去扯他的衣角,她像是忽然被谁抽空了浑身的力气,只能徒劳地沿着走廊墙壁上那冰冷的瓷砖,缓缓瘫软了下去。
他说不想再看到她了。
她无端笑起来,像是绚烂的夏花,美丽而又凄绝,笑着笑着,那原本以为的整个世界便全部坍塌,她上扬的嘴角忍不住耷拉下来,落成一个不大好看的弧度。
明天太阳依旧会升起,潮汐依然会涨落,可是宇宙洪荒,她心头的那个人,却再也不会毫无顾忌地让她陪在身侧了。
她闭了眼,终于旁若无人地抱头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