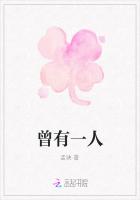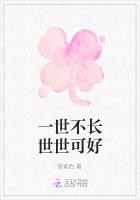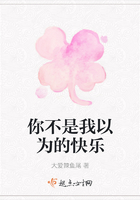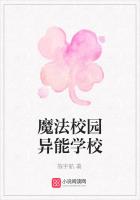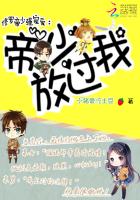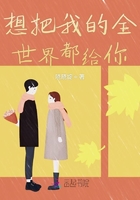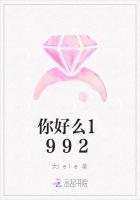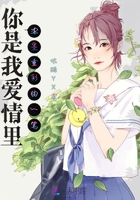从五岁多开始读学前班,到考上大学,陈楼楼一共读了十三年的书,陈楼楼觉得年份挺多的,但是一回首,却是感觉一眨眼就到了现在。
有些事情还能记得很清楚,比如两岁左右的时候去外婆家,那儿是山地,盛产红薯。陈楼楼记得晚上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把她抱在腿上,面前是一个大火炉,烧煤的那种。
火上正在烤红薯,陈楼楼记得外婆家的红薯是放在她们坐的大板凳下面的煤灰里,是挖了坑,用燃尽的冷煤灰埋在里面的,红薯不能受冻,受冻后会烂,会变苦,所以要用干的煤灰盖住。
火上的红薯没有了,就叫陈楼楼的表哥蹲在大板凳下面去刨出来,继续放在火上烤。农村人吃东西就是要吃饱的,随你吃个够。
再比如小时候,陈楼楼的母亲要给陈楼楼做炒鸡蛋饭,陈楼楼拿着鸡蛋在自家的帐架床上一敲,壳儿破了以后,鸡蛋就全部流到了地上。
当然,关于鸡蛋流到地上以后的事,陈楼楼就不记得了。
但是有些事情,陈楼楼就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比如,她不到两岁的时候父母就一起出去外省打工了,一大早上就起床走了,那时候睡得模模糊糊的,陈楼楼只记得他们一人吐了一口口水在陈楼楼手心里,大人说是怕陈楼楼挂牵父母。但是至于醒来以后有没有哭闹,陈楼楼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的。
现在陈楼楼终于考上了大学,是一个二本学校,省外的。陈楼楼填志愿的时候就填了一个外省的学校,但没想到就被录取了。陈楼楼有时候就在想,自己五百八十多的高考分数,虽然是一个读文科的,但是比一本线还长了好多分,自己怎么就去了这么远的地方,最合算的就是坐火车。若是快车,得坐三十来个小时;直达的话,就是二十五个小时左右;但是买到慢车的话,就要在火车上坐三十多个小时。不仅路途遥远,车费还要得多,何苦来哉!
若说是警校,但是自己的省会也有警校啊,虽然名头和教学质量不怎么样,但好歹离家近些,不至于只有放寒暑假才能回去。
而且这个学校也不是很好,是一个八人间寝室的大学,每天早上起来整理内务的时候都要你让着我,我让着你。阳台小的可怕,放了几个箱子就没有落脚之处了。晾晒衣服的杆子就在阳台上,三米左右长,八个人的衣服一挂上去就挤得密不透风,看着就膈应人。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准时集合跑早操,解散后去吃早餐,整理内务。七点十分左右会有学生会的来检查个人内务和寝室卫生,七点三十五又准时集合,八点开始上课。
陈楼楼来学校一个学期,也就是四个多月,一共写了三份检讨,共计四千五百字,实在是让人躁得慌。
对于写检讨这事儿,校内有同学还写了不少打油诗进行调侃,比如:“日间体劳夜神伤,操书罪己又几章。圣府本事育才地,何故遣使省诏扬?”
对此,陈楼楼觉得其实也还好,既然是警校,那就得有个警校的样子,那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只有将小事做好,才能迈上更高的舞台,自己的才能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施展。
话是这样说没错,但是因为毛毯虚了一点点,就被罚写检讨,陈楼楼还是有些无奈。
想她没上大学前,那可是妥妥的乖学生,成绩中上等,总之是校排名前十五乃至前十的人物,没想到越活越回去了,居然被写了检讨,还是三份,简直是丢人,陈楼楼想死。说给高中同学听,都让他们纷纷称奇,直说这是一个有特色的学校。
陈楼楼的高中同学们,不管考的好不好,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人家都过得有滋有味的,不像陈楼楼的这种制式管理学校,连头发都是有规定的,女生前不过眉,后不搭领,男生就更短了。人家都是要么女生迷人大波浪,男生撩人离子烫。
寝室更是装扮得随心所欲,甚至那些设计的好的,还有奖金。而陈楼楼看着自己寝室里白白的墙,蓝色的被子沉默了。但仔细一想,这样其实也挺好的,没有贫富差距的出现,最起码在这些方面是没有的。
至于其他的,陈楼楼也不在乎。
室友今儿个入手一只两百多一只的口红,明天请人代购一套三千多的护肤品;中午吃这家特色店的寿司,晚上订那家专营店的鸡公煲……这些,陈楼楼觉得内心深处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更谈不上什么落差。
最起码,她每天都可以吃饱饭的,穿的也是警服,照样滋润潇洒。
作为一个农村人,陈楼楼有自己的自觉。那些莫须有的攀比和虚荣心,陈楼楼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她不在意这些的。就算她在意,她也没有那个能力。
父母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赚钱,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白班上到夜班转,磨的就是那几根骨头。作为子女,她很感激她的父母,她感恩他们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去努力。
每个月工资三千多块钱,四千不到,但是自从陈楼楼上大学以后,考虑到她一个女生独自在外省,没个亲人照顾,就每个月给她一千二百块钱的生活费。这对她们家来说绝对是一笔重大的开销。
父母每个月不到四千块钱的工资,要交租房子的费用,还有水费,电费,自己的生活费……除了这些,两个人也就剩下四千左右块钱了。每个月给她一千二,给她上高中的弟弟八百,就只剩两千左右了。
还有欠家里亲朋好友的债务,也是要还的。
陈楼楼的父亲前几年患股骨头坏死,因为不懂这些,加上一些顾虑,就没有直接去大医院换股骨头,做换置手术。而是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吃中药,去打针,还有钻孔减压,理疗……去了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等地,花掉十几万块钱,有些地方花的钱是能用农村医疗保险报销的,而有些则不能,所以算下来也差不多用掉了近九万块钱。
但是却毫无作用,最后花了三万多块钱在市里面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换了一只腿的,另一只没换,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没有钱。
家里所有的钱都用光了,亲朋好友那儿能借的都借了,到最后还是只能筹到换一只股骨头的钱。
而这些钱,大多都是借的。
因为手术后需要恢复与保养,所以父亲就在家里待了半年多。在那半年里,家里所有的开销都是来源于母亲:陈楼楼上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陈金龙上初中的学费和生活费,陈德奇在家里的生活费和买药的钱,还有去医院检查的,都是来自徐德可在外面打工挣的,还有一些就是向别人家借的。
每当有亲朋家办喜事或者丧事,陈德奇就要自己去借钱。
三分钱难倒英雄汉,此话不假。
陈德奇做手术的两天前,陈楼楼是陪着他的。他们去市里面的医院以前就打听好了,定下了其中的两个医院,决定到了以后再具体看看选择哪一家。
最先去的是第一中心医院,问好了价格,讲好了价钱,两人就去了之前决定的另一家医院,也就是第三医院。到那儿以后,发现那儿的条件要差很多,医院的走廊里随处可见的都是地铺,那是病人家属晚上睡觉的地方。每间病房都挤满了人,床单上都是斑驳的、洗不掉的血迹,里面的病人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睡觉,还有的在呆呆的坐着……
陈楼楼感到一阵阵的恐慌,心里尽是说不出的害怕。
问了价格,比市第一中心医院贵了差不多两千,两人那就决定还是去市第一中心医院。
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钱。
他们从家里一共带来两万三千多块钱,但是总共要三万四左右,也就是说还差一万多。
陈楼楼打电话给她母亲,她就只有一千多一点,其他的都已经寄回来了。
徐德可最后寄了一千块回来。
陈德奇打电话给陈楼楼的幺叔,也就是陈德智。
当然,他们也知道他没钱。幺叔家有两个孩子在上学,一个初中和陈金龙同级,一个小学。幺叔并没有出去打工,因为孩子还小,他也还要照顾爷爷。这两年陈道盛都是在陈德智家生活,并没有要求陈德奇一家赡养。因为陈德奇生病已经两年多了,行动尚且不能自如,连自己都没有做饭吃,是在陈德智家里吃饭,自然是没有办法再去照顾一个八十五六的老人的。
所以陈德智就在家里种一些庄稼,每年喂一只猪等腊月二十几的时候就杀来过年。喂猪的粮食是自己土里种的苞谷,自己家吃的大米也是自己家田里种的稻谷。
至于平时的花费,就是来源于外出打工的徐双琴。
因为徐双琴和徐德可都是姓徐,所以大人就教陈楼楼和陈金龙喊她舅舅,而不是幺娘。
正是因为这样,陈德奇知道,陈德智也是没有钱的。
但是,陈德智打电话给徐双琴,她就寄了四千块钱回来,是她一个多月的工资。
陈楼楼是读高中的,因为有精准扶贫,所以国家每年都有一些钱打进她的卡里面。因为她是第二批交申请材料的,所以这个学期就只有一千块钱,也给了陈德奇。
但是,手术费还是差了差不多五千块钱,现如今,这五千块钱又该向谁借呢?
陈德奇打电话给何志平,是他的表哥,也就是陈德奇母亲何氏的娘家侄子。
何志平是一个教师,是名师转正的,教小学语文。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这何志平能够教书还是因为陈道盛。
以前陈道盛还在大队里面的时候,就将何志平叫去教书。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少,有文化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村里要办学校,但是却没有老师,陈道盛就把何志平叫去帮忙,从那以后,何志平就走上了教书的道路。
至于陈道盛为什么不叫自己的儿子呢?
那时候陈德元生病,脑膜炎烧坏了脑子。其他的儿子年纪还小,毕竟第二个儿子是老六,中间的那些都是夭折了的。因此,其他的儿子年龄自然是够不上的。
现在,何志平每个月都有五六千块钱的工资。但是,再过一年就该是要退休了。
陈德奇打电话过去后,是何志平的妻子接的。把这件事说了以后,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说是明天在陈德智送钱来的时候给他一起送过来。
现在手术费是够了,但是陈楼楼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生活费没有了。他们在医院总是要吃喝的,把钱交了手术费,就没有生活费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陈德奇又给何志平的妻子靳氏:“老表嫂,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开口,但是现在我手术费是凑齐了,可是没有生活费,你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再借一千块钱给我?”
靳氏说没有问题,明天会让陈德智一起带过来。
陈楼楼发誓,那是她唯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这个以前脾气暴躁且暴力的男人,第一次在陈楼楼面前露出了怯弱。
有些心酸,但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
陈楼楼突然想起几天前去寨子里面向人家借钱的光景。父亲请了伯娘史氏和陈楼楼一起去的。
在人家坐了许久,却还是难能开口,真的,那种感觉实在是令陈楼楼难以忘怀,只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了。
现在钱也借到了,父女两人又在第三医院的凳子上坐了许久。
两个人都没有再开口,就这样沉默着。陈德奇把头低下,陈楼楼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想看清。
这个男人从小没少打她,无论是巴掌还是火钳,不管是竹条子还是扁担,陈楼楼都感受过它们落在自己身上的重量与痛感,这些都是难以忘记的。
但这一刻,陈楼楼仿佛又不想忘记了,不是那种记恨一辈子的决心,而是希望眼前这个被她称之为“父亲”的男人不要老得那么快,最起码希望时间能够对他温柔以待,希望病痛不要折磨他。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头上的银丝刺痛了陈楼楼的双眼,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喷薄而出,直到越来越朦胧……
举袖一抹,不敢再想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