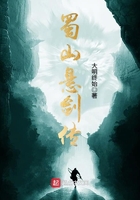分离从来就是为了下一次的久别重逢。他游荡在街上,从没感觉到三年的时间那么快,他初中毕业了,可他连高中都没考上,也真是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这个年纪习学不好,没有追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还没成为最想成为的那个人,仔细一想也真是一事无成。
他回到家里他父母倒是毫不避讳,劈头盖脸便是反正你高中也考不上,随便找个学校混几年就去当兵好了,他到不想去军队,军人们确实英姿飒爽,但对他吸引力真的是不大呢,他反驳:“我不去。”
他父母加大声音:“那你想干嘛?”他不语。
“考不上高中,也不去当兵,你告诉我你想去哪?”
“我说了你们能同意吗?”
“你倒是说啊,真不知道你整天在想什么。”
“去学设计。”
“你学设计有什么出路?要是不想去军队,就去学电梯,实在不行学个汽修也行。”
“不去。”
“你为什么不去!”
“我不想学。”
他父母有些气急败坏:“你学设计能赚到钱吗?电梯现在行情那么好,你看外面那么多楼,以后肯定会建起来更高的,肯定少不了电梯,你为什么不学,就因为你不想?你从小到大都这样,什么事就一句不想,然后就可以不用干了?”
“我又不是没想过……”
他说了一半的话被他父母打断:“你能想到什么?你就是个十五小屁孩你能知道什么。你不去当兵就去给我学电梯。”
“我说了我不去!”
“你能不能听话,我们还是不是你父母?”
“谁说不是。”
他父母再一次打断他的话语:“是,我也没见你听过我们的话。”
“我怎么不听的。”
“听就去当兵。”
“我说过了,我不去。”
是啊,从小到大,他就没有个好孩子样子,他父母从没有一刻以他为荣过,也从来没在任何人面前说过他们儿子的好,其实不也就是因为他学习不好吗?就此来否认他的所有,他从来没忘他们在他小时候吵的每一次架,也忘不了他妈把爸关在门外,忘不了那天晚上他们有多么的震天动地,还有他第一次见到的那个鲜红色的可怕的液体,他藏在房间里不敢说话他甚至连爸爸妈妈都喊不出来,那是一个幼儿园孩子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的恐惧,就像这个世界就剩一个人了周围寒风刺骨,冰天雪地。他没忘他妈妈的多少次离家出走,忘不了他父母半夜里把他关在大门外的一次又一次,他一次次喊着妈妈妈妈我不敢了,以后不敢了,把我放进去好不好他忘不了,她妈妈因为他犯得一丢丢的错说的每一句不要他,把他往门外丢,把他往马路旁丢,那时候他从没感觉自己温暖,只有如入骨髓的孤独。摧毁一个人,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在他用尽全力做一件事找你讨嘉奖的时候,说他一事无成,在他照镜子时,说他简直不能看,没事送他块糖,随后给他一巴掌,且一定要重复,让他感受到你爱他时,用你的实际行动告诉他,那可不一定,什么是实际行动,冷落,自顾自的占有,打骂,否认,从内心深处表现出的厌恶。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秉持着父母之名,连整个世界都会说他们是对的,如果反抗,就会背上不孝的骂名,他们可以在饭局餐桌上对你讥讽,说你一事无成,而你不能反驳,你只能受着,可有时他们只是想证明,他们是你的父母,你不论如何都要听他们的,可怜可厌的听话便为孝禁锢了多少思想,禁锢了多少十七八岁孩子的思想,让他们这一辈子都只活在对父母的言听计从中。
他与父母吵了一架,摔门而出,他又重新回到大街上,他喜欢去湖边转转,那湖边总是没什么人的,他没事就去湖边唱唱歌,他以前也在家里唱,迎来的只是父母的厌恶,用那种及其轻蔑,极其厌恶的白眼,所以他便不怎么唱了。他唱着唱着抽泣起来,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哭,也许是因为那个叫葛方茗的人从此开始不知何时才会与他相见,今天可真是让人难受啊,他抽泣着,抽泣着,声音越来越大,他的心越来越痛,那是种万千根针直插心脏之痛,那种痛疼得他说不出话,他用双手压住胸腔,可他竟压不住那痛,那股痛还是直击大脑,仿佛在告诉他,你所清楚地都是真的,她真的离开你了。自此再也不相见,再也不相念,他越想越痛,剥皮抽筋之痛恐怕也不能与他比,他想起她的一颦一笑,想起他每次抬头看见她,看到她的马尾,看到她满是数学题的练习本,看到她的每一次笑颜,也看到她就这么离自己而去,他一刻一刻的像是凌迟一样,到最后他也没力气了,干脆躺在地上任由泪水绕过耳朵,流过头发,滴到地上,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他也曾梦到她离自己而去,只是没想到来的那么快。她来时他忘了相迎,她走时他竟依依不舍。
他也不记得自己躺了多长时间,也终究是感觉不到那痛了,他尝试站起来,他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摇摇晃晃的,竟没站起来,他笑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无用了,他尝试了几次,终究是站起来了,他慢慢的走摇摇晃晃的,仿佛周星驰电影里,城墙下的孙悟空,背影像条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