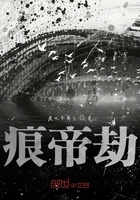我重生了,回到了我及笄的那一年。
相府荣宠,世人称我有倾城之姿,我及笄的那一日,整个朝京盛况空前,相府门庭若市,进进出出的掎裳连襼。
母亲去世的早,是舅母将我一手带大,家庙上,我身着曲裾深衣,她作为笈者给我挽髻插笄,缠缚五彩缨线。
冠笄盛于盘中,上面蒙以帕,是由有司执之,父亲将钗冠、罗帕依次给我佩授毕,我着其出房,众宾客惊叹,在赞者赞唱礼之下,我跪拜了父亲,聆听祖训。
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接亲吹吹打打的庙乐声,姜彦领着一众人抬着聘礼走了进来,他说他要迎娶我做正室夫人,众宾客惊奇,父亲大怒,姜彦是毒医谷的人,乃江湖草莽之寇,父亲向来不喜,却碍于面子,只说赶紧将人打发了走。
“怎么,岳丈这是不喜我这个新女婿?”
他调侃中带着痞气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赞礼停了,我被阿凉扶了起来,高站于庙台之上,看着石阶下他的模样,他着一袭淡紫色长袍,光亮华丽的贡品柔缎,不仅仅是在阳光下折射出淡淡光辉那样好看,穿在身上亦是舒适飘逸,高高绾着冠发,长若流水的发丝服帖顺在背后,微仰着头,幽暗深邃的冰眸子,显得狂野不拘,邪魅性感。
我压下心底陡然传来的阵痛努力回想,前世的我是怎样鄙夷他的这一番愚蠢的行为来着----
“姜彦,凭你也配?”少女正值芳龄,世人追捧,又心底怀着小女儿的梦,自是狠狠的将那人的骄傲给粉碎了个挫骨扬灰。
他走了,决绝的背影竟让那时的我愣了许久,热闹的笄礼,宫妃的赏赐,赞唱高贺,采亲纳礼,不过一转眼便又忘了个干净。
阿凉推我,回过来了神,只见院内出现了一群府兵,父亲高喊,“宵小在我儿笄礼上胡闹,拉去大理寺,交给梁大人审判。”
“等等。”情急之下,我站了出来,“父亲,这是女儿的笄礼,将人打发走便是,不要涂惹怒气了。”
父亲还未说话,他便上前了一步,深邃的眸子凝在我的眼里,他说,“臻儿,天山雪狐当做聘礼,我来娶你了。痛,蜿蜒的痛在作祟---
此言一出,大惊四座,天山雪狐?!生长在天山之巅的千年雪狐,朝京最勇猛的武士都未能靠近其一丝一毫,哪里来的儿郎,竟这么威猛。
众人纷纷看,那么大的一个聘礼箱内,打开,竟然装有铁笼,里面赫然放着一头血淋淋的狐狸,看样子,已经没了生气。
众人骇,父亲大怒,“放肆。”好好的及笄礼,来了这么一出,带着血色,父亲气急了,有礼节说,女儿家在及笄礼上带了血色,一辈子都安稳不得,前世,也还真真是应了此言。
“臻儿,你可愿意嫁给我?”江湖上,不在乎礼节,可我身在相府,长在朝京,今日当众求亲,言辞放浪一事,父亲的面子全然丢了。
“不愿。”
他不甘,“那为何救我说那一言?”
轻飘飘的话似乎只在我耳边回荡,我苦笑着沉下了心中所有的痛、悔、怒、面色故作平淡,敛目开口,“顺手罢了。”
记忆实在太过久远了,依稀记得,应该是半年前了,冬日里,我最是喜爱去护城河上游湖,泛舟江上,看山景,赏清湖,听一首小曲儿,弄一曲清箫,快活哉矣,那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声响,我震惊,想要探头去看的时候,一个血淋淋的人“砰”的一声掉在了我的船上,他全身都被血浸湿了,看着极为可怕,可那一双黝黑的眼睛里,却藏着冰冷的嗜血,阿凉惊讶想要大呼救命的时候,被他一招给打晕了。
“阿凉--”我忙跑过去,摸了摸阿凉的脉搏,还好,无碍。
“你敢喊人,小爷我毙了你。”
他恶狠狠的样子自是吓了我一跳,任是谁,在那种境地下,只会赶紧远离开这人吧,可我偏偏着了魔,管了这档子闲事,抿了抿唇,“公子若信我,我便帮你。”自是要与他说好,万一他以为我图谋不轨,一刀弄死我丫的,可太冤枉了。
他似有惊疑,抬眸间,点了点头。
我费力将他拖回了画舫的内阁小床上,在红木抽屉里找到了止血的药,给他撒了上去,包扎好,身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伤口,大小不一,我看着触目惊心,他很是友善的说了句,“姑娘若害怕,我自己来吧。”
“没。”一个重伤之人,我实在于心不忍,笨手笨脚的给他上了药,每一处都包扎好了,这才作罢。
“可真笨,谁娶你当媳妇倒霉喽。”他在打趣儿,可我听了还是生气,挑眉回了一句,“不牢公子来娶。”
他笑了,说实话,我没有见过比容云更好看的男子了,他一笑,却是让我想起来了传说天山上的千年雪狐,邪恶却魅惑人心,当真比得上倾城,气氛怪异,我拾了拾额间的碎发,想要出去。
“姑娘莫气,你家住哪里?改日我上门提亲?”
我愕然回眸,“公子休要胡说。”
“家父教导,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姑娘救了我,我自要报答。”末了还加了句,“何况,是你这么美的姑娘。”
他这般无厘头的不着调,我自然不信,哪一家的长辈会教孩儿这么没有礼数的报恩方式,收了收心神,当下想要戏弄于他,“你若想娶我,杀了天山上的千年雪狐,当作聘礼。”
岂知,他道,“好,你及笄之日,我迎亲之时,姑娘等我。”
后来的事情实在想不起来了,死的时候,只记得,公子卧榻美人靠,三分邪面半目媚,许我一生承诺,“你及笄之日,我迎亲之时。”前世,我负了你,今生,等我。
“你是真心而言?”院子里,热闹非凡,他站在人群中央,直勾勾的望着我。
跟前世一模一样,我的心无比荒凉沉痛,转过了身,不再言语。
“人家不愿嫁于你,回去吧。”
“真倒是落花无意堪薄凉。”
“哪里,分明是这小子仰慕秦姑娘大名,死皮白赖的上门娶亲被拒了而已。”
人群中的叽叽喳喳的热闹声让我心一痛,腥甜涌了上来,我努力忽视掉背上凝过来的眸子,将鲜血兀自吞了去。
他自是走了,与之当年一比,好似恍然一梦,我转过身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沉沉的古老红木门被小厮关了上,徒留眼前一声叹息。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众宾客也看了够热闹,舅母与父亲对视了一眼,笄礼继续,赞唱起,有司撤去笄礼的一些陈设,在西阶位置摆好醴酒席,家族里的嫡系一脉揖礼,舅母等人入席。
我象征性的吃了一点醮子,答谢了众宾,老者取字后,我便退了席,父亲怜我,也没加阻拦。
真是世事无常,看着满园子的花草,我感慨,死的时候是冬日,今却身在夏日,回来有一阵子了,如今是圣武十四年,没有战乱,没有夺嫡,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父亲是文官之首,位高权重,与苏府并列二臣,相府处在盛宠不衰的地位,一切,好玩多了。
我想要出门,却被阿凉提醒,父亲的禁足时期还未过,是了,当时,我刚刚醒过来,太过惊讶与喜泣了,拖着残败的身子骑了一头马往郊外的深谷里去了,父亲被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在谷底找到了我,病恹恹的躺在草堆里,回来后,我便被禁了足。
“还有几日?”
阿凉回我“三日,小姐便可出去走走了。”
我平静了一会儿,往闺阁走去,心底暗暗提醒自己,仅那一次,在不可意气用事。
“小姐,你变了好多。”
身边陡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停下了脚步,阿凉是个极其沉默的人,平日里,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前世,是在相府要被满门抄斩的时候死了的,我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大病一场,脱胎换骨。”我看她一眼,“阿凉,你多笑笑,很好看。”记忆中,我没有见过阿凉的笑容。
我及笄了,有奔着相府嫡女的名头来求亲的,也有人是奔着所谓的倾城之姿来一睹芳容的,都被父亲挡了去,禁足已过,我从后门溜了出去,前世,便是父亲不让我理会政事,导致相府走在深渊的时候,我没能拉上一把,如今,逆天改命又何妨,还有三年的时光,足够了。
我先去拜访的苏府,去了,悄悄的打听了一下,奴仆说,苏家大小姐苏锦四年前便死在了禹城的庄子上,我慌着神走了出来,茫然无际的街肆上,“四年前便死了,四年前便死了,阿锦死了?”
我不敢相信,前世,阿锦是在两年后也就是圣武十六年被接回的朝京,赐婚给了容云,如今死在了禹城,我不由怀疑,难道是因为我重生的缘故,都变了,一切都变了。
阿凉推我,“小姐,你看。”
长街上,古巷里,淡紫儿郎,携一壶桃花酿,醉醺醺的朝我走来。
“姜彦---”
他一身酒气,一把便将我掳上了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