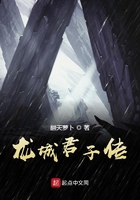云惜是在下山的路途中想明白这一切的。
信真破坏壁画的真正手法她早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但整起事件中仍然有两个地方令人万分不解:一个是报案人李保泰的身份;另一个则是拙一亲眼目睹第三次壁画自毁的场面。
而下山途中与信觉小和尚的那番对话,帮她彻底解开了所有的谜底。
信觉就是李保泰。
她喊出这个俗家姓名的时候,信觉就仿佛中了什么符咒,身体僵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缓缓回首来看云惜,目光中带着惊异甚至惶恐。
这不难猜。
因为信觉说出了“韩记纸铺”,说出了江南来的皮纸。
那皮纸是平日里云惜给人订制画作用的,比她父亲爱用的纯青檀皮纸要略差一些,但也是上品。
那家“韩记纸铺”,与云惜的画店只隔了那么一条街。
面对云惜的指认,李保泰——信觉没有否认,他只是讶异:“云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你信真师兄,”灯笼晦暗的灯光下,云惜解释起来:“我来这里的第二天,信真师傅看见我在泥地上画画,上来便是一句‘听闻女施主也是位丹青妙笔,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当时我便十分疑惑,我来山寺之时明明没有自我介绍职业,信真师傅如何知道我擅长丹青?后来在帮你师兄弟们给壁画上色的时候,听说了你经常随信真去京城采买的事情,而且你为了划价,往往会在采买的时候支开信真师傅。我就猜你有没有可能是报案的那个李保泰。直到刚才你说出了韩记纸铺的事情——这韩记纸铺不但离我的小店很近,离晏怀安的衙门也近。可见你在先前应该是路过过我的小店,见过我画画,所以知道我擅长丹青。另外,这件案子则是你在晏怀安那里报的,报案的时间跟你上次去京城买纸完全吻合。综合以上两点,我猜测报案的‘李保泰’可能是你出家前的姓名,当然我也不能完全确定,所以刚才在你身后突然喊出‘李保泰’这三个字,其实也是在诈你。”
“原来如此……”信觉眼神黯然,“云姐姐你不但擅长丹青,连破案也很擅长。我……我也太不小心了。”
“那么,你就是李保泰?”旁边晏怀安开口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信觉一遍,没想到他们寻找了好久的报案人其实一直就在身边。
“嗯,这是我从前的俗名。我还有张旧的贱籍,出家后也一直藏着。报案的时候我问街头乞丐借了件破衣服,然后把贱籍身契给书记官看了一眼,就这么掩盖了自己和尚的身份,蒙骗了过去。”
“那你为什么要报案?还不让你的好师兄知道?”晏怀安又生硬地问。
信觉垂下头去,有点儿脸红:“我、我……”
他“我”了半天没有结果,云惜替他回答:“因为你敬爱师兄,不希望他一错再错。”
信觉震惊地看着云惜。
“云姐姐……你……”
云惜说中了他真正的心事。信觉作为云摩寺的和尚,关心云摩寺的清名以及那三面壁画是自然。不过,他更担心的是一直善待他的师兄。
“云姐姐你早就知道了……”信觉欲言又止。对于壁画“自毁”之事,他作为信真最信任的师弟之一,自然也是知根知底的。
正是因为知道信真在此事中的牵扯,所以希望自己的好师兄能悬崖勒马,以免堕入魔道。
“是,我已经猜知一切应是信真师傅所为。”云惜淡淡回答,“我还猜,你出家前家里从事的就是纸张买卖?”
“云姐姐你真是神了。对,我家主要从事纸张买卖,也兼顾墨锭之类的文房买卖。所以我对京城文安坊特别熟悉。我见云姐姐也并非是出家之后的事情了,好多年前我还小的时候,就见过姐姐一面,当时姐姐的小店里还有一位,想必是姐姐的父亲?大概姐姐画画没画好,令尊正在打你手板。”
“还有这样的渊源?”云惜心念一动,微笑了起来:“那咱俩也算有缘。”
听到“有缘”二字,晏怀安差点气得七窍冒烟。
“那你后来是怎么被贬为贱籍的呢?商人也有民籍才是。”云惜问。
“我父亲做买卖路上遇到匪盗被抢掠一空,因此欠下不少债务还不上。商人在本朝本来地位就地,这下被人告了上去,自然就被贬了。几年前我父亲还带着我四处给人做缝补浆洗过活,后来父亲得病去世,我就省了自己,便来投了云摩寺。”
云惜听了心里感伤。除了信觉身世可怜外,她还未他父亲亡故而难过。
云惜进而想到自己的父亲,以及那个飘渺可怖的梦,心里的怅惘更浓重了几分。
信觉见她出神,不知道她在思索什么,便问:“云姐姐你知道了我的身份,是不是还知道了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壁画的事情?”
这便立即将云惜从怅惘中惊醒过来。她惊呼:“对了!壁画!”
***
信觉就这样带着云惜和晏怀安重新回到了云摩寺。
信觉先到的,当晚在山门入口原本由另一位师兄当值,这天所有人都为壁画忙碌了一整天,唯有信觉相对闲些,信觉便提出替师兄当值。这位师兄也未多说,谢过后便自己回了僧寮。
云惜和晏怀安如入无人之境。墨一样漆黑的夜色里,云摩寺平添几分阴森诡异。
云惜进了寺门,便急匆匆往参堂那边赶。
还好还好,凑在参堂的门口侧耳倾听,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云惜暗自舒了一口气,然后转向信觉:“信觉,我现在要画画。你去给我弄些颜料,打一碗水,再准备几只毛笔来。”
“画画?”信觉不明所以,一听这话有些着急了。压低了声音:“云姐姐,现在可不是画画的时候啊!而且这黑灯瞎火的,你想画什么呢?”
“猫。”
一直到这次日的早晨,信觉才明白云惜绘那只猫儿的用意。
如果不是那只猫儿,这群田鼠便不会盘桓在参堂之外,很大可能已经进了参堂里面。
参堂里面,是壁画……
信觉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壁画“自毁”的原因,但是仔细想想:田鼠莫非成精了不成?要不然怎么会去破坏壁画?
不管怎么说,他可得谢谢这只猫儿,否则的话,他冒着风险以“李保泰”之名去报案,将会是空忙一场。
再看看这只功臣一般的猫儿,画得的确出彩。
十分逼肖不说,还虎虎生威,仿佛伏在石阶之上,随时准备扑下来冲向群鼠。这便让群鼠胆战心惊,乱窜不已。
只是信觉仍然不明白:如果田鼠们害怕,为什么还围着参堂不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