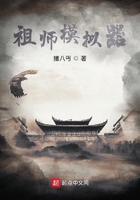“怎么突然打雷了?”夜色中,几户熄灯较晚的人家突然听到这雷声,吓了一跳,以为又有妖怪来袭。不过再听,宁静中再无异动,这才放心,念叨了几句“河神爷保佑”,这才沉沉睡去。
“刀成之时,春潮涌动!如此,你便唤作‘潮音’吧!”陈庭安见一刀挥出,巨浪击空,惊涛拍岸,心中欢喜,轻抚长刀道。
“喵!”一旁守在他脚下的球球,似是对这个名字也极其满意,喵了一声,用头蹭了蹭主人的青缎鞋袜,一脸惬意地眯缝着眼睛。
陈庭安收刀入鞘,抱起球球回道房中,儿臂粗的鹅油白蜡燃得正旺,淌落蜡油满地。他轻轻吹熄蜡烛,也不脱衣,便这样抱刀和衣而卧,不觉间已经陷入深度睡眠。
这一夜,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手握潮音刀,带着已经长大的球球,血染青袍,刀光如电,一路诛杀妖孽,竟然不知不觉便杀上了南天门。
而那南天门上,妖气森森,邪祟滚滚,却又哪里能见到半个天兵天将,分明尽是妖魔,唇齿掀露之间,个个说着“吃人”二字,让人不仅遍体生寒,汗毛倒竖。
在噩梦中厮杀了一夜,陈庭安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窗外暖阳高照,驱散了陈庭安心底寒意。
他翻身起床,提着陶罐来到河边,淘洗干净,先煮了半罐香喷喷的新米粥,热气腾腾吃饱,接着便带着球球到村里四处走走,不时与人拉拉家常,说上几句闲话。即便已入神道,但这浸润着人间温情的浓浓烟火气,仍让他感觉十足珍惜。
托了河神庙的福,近几个月,梅村往来人流也比以往更多了许多,其中不乏从极远乡镇赶来,专程为拜谒河神,讨一杯灵酒而来的。
陈庭安也不吝惜,对于他而言,哪怕只是几个浅信徒的些微信仰,积少成多,也有喷薄而出的一天。
而狡黠的商贩们,也不吝脚程,紧跟着纷至沓来的人流,久而久之,竟在入村口的青石板路两旁,形成了一处小小的集市,卖些吃食、杂货、香火等,倒是给大家伙提供了许多方便。原本偏僻的小山村,竟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繁华起来。
这一日,陈庭安清晨起床,照着往日般吃完半罐热粥,提着潮音,带着球球,正要去附近山上练刀,孰料一出门,便遇见四五个人用门板抬着一名老汉,匆匆向河神庙走来,神色焦急,显是出了什么事。
“松伯?”陈庭安一眼望去,便看清躺在那门板上的,正是村中最嗜酒的松伯。
松伯爱酒,陈庭安心中是清楚地。仅是自己来后的这几个月,他已因贪杯不知醉过几回,更与婆娘吵过多少回架,但始终恶习难改。如今这大清早的便被家人匆匆抬来,莫非是饮酒过量,酒精中毒?
“庙祝公,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家当家的!”松伯婆娘远远看见陈庭安似要出门,急忙匆匆一路小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哭嚎。
“发生什么事了?”陈庭安急忙扶起她,温和问道。
“都怪我,昨天上山采了几个蘑菇,晚上炒着吃了,结果他说有好菜,非要喝上几杯,没想到过了一个晚上,就成这样了!”松伯婆娘又悔又怕,急忙说明缘由。
“只怕是蘑菇中毒了。”陈庭安心中猜测。在大山之中,各种蕈类千般万样,有的是救人的仙草,有的是致命的毒药,哪怕是最有经验的山民也不能完全分辨,因此蘑菇中毒之事时有发生。只是这松伯婆娘向来精明,对于分辨不清的蘑菇,怎么会冒然采吃呢?
陈庭安心中暗想,感觉有些奇怪,快步走到躺在门板上的松伯身旁,仔细检查,心中又是一跳,“松伯症状,只怕不是普通的蘑菇中毒啊?”
“但昨晚我家当家的,的确只吃了半碗蘑菇,喝了两杯酒,然后就睡了啊?”松伯婆娘听陈庭安疑惑开口,心中更急。
“那剩余的蘑菇和酒带来了吗?”陈庭安回头问道,神情十分严肃。
“带来了带来了!”松伯婆娘忙不迭从门板被褥里摸出半碗蘑菇一壶酒,递给陈庭安。
“都是很普通的松蕈啊,酒也是新酿的五谷酒。”陈庭安心中疑惑,放下蘑菇和酒,眼神凝重,看向躺在门板上的松伯,只见他胸口没有半分起伏,浑身发黑僵硬,指甲变尖变长,这哪里是蘑菇中毒之像,分明是一只即将成型的僵尸啊!
“这其中,只怕是另有关节啊!”陈庭安低声一叹,袖中只手探出,轻轻搭在松伯腕上,神念探出。
果然,陈庭安神念方一探出,便感觉松伯体内隐隐传来一缕十分微弱的迟滞之力,若非自己神识入微,只怕一时之间亦难察觉。
“除了昨晚吃了些蘑菇和酒,松伯近日可有外出?有没有提及一些奇怪的事情?”陈庭安一脸严肃,沉声发问。在他想来,这等奇异脉象,仿佛附骨之蛆,只怕是邪祟居多啊!
“没有啊?每日都是和大家伙一块上地下河,也没听说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啊?”松伯婆娘一听,心中更慌,茫然答道。
“当真怪哉!”陈庭安一时难以理清头绪,也无法将那异毒从松伯经脉驱离,只好收回手,转头看向松伯婆娘:“不知阿嫫您可否将手伸出,让我一探!”
说罢,又转头看向抬着门板送阿伯来得众人:“你等也是!”
“当然!当然!”松伯婆娘急忙伸手。
“好!”陈庭安手指一搭,神念探出,便如缕缕游丝,沿着松伯婆娘经脉细细探出,一时间但也还算正常,并未发现什么异像。
“莫非是我多疑?”陈庭安心中疑惑,但总觉不安,双目微闭,神念一分三,三分九,变得更加微细,丝丝缕缕深入骨髓。之中。
“轰!”神念刚刚探入骨髓,陈庭安脑海之中便如响了一个霹雳:“果然,阿嫫也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