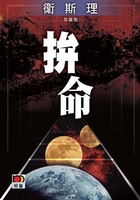阿丽与胜男离开夜总会的时候,一再鼓动我与她们一起离开,我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因为我不知道那两人醒来会不会上来找人,如果我走了,会惊动整个夜总会,全世界都知道我骗了人家800元。这个行业就这么大,我可不想搞坏自己的名声。
阿丽以为我还想继续挣钱,说:“你今晚轻轻松松地就挣了800元,不如提早下班,吊颈都要松口气啦。”
我朝她们笑笑,继续到各房间看场子。此后风平浪静,直到三点多我离开的时候,都没有见到那俩男人的身影。
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想起那晚的事,感觉真不可思议,随随便便就挣了人家800元。有的人辛辛苦苦地工作一个月,拿到的也不过是这个数。
从那以后,我与阿丽和胜男成为朋友,经常相约着一起逛街看衣服。相处久了,我才发现,原来“卖艺不卖身”是她们的口头禅。有时候我与她们开玩笑:“你们经常陪客人出去,看在钱的分上一定做过不少坏事。”
阿丽说:“你晚晚在夜总会上班,是不是经常与客人……”
我说:“我只是卖啤酒。”
阿丽说:“我是卖艺的。”其坚决的口气,令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三流武侠片,侠女在耍了一通拳脚后,双手抱拳道:“小女子初到贵地,卖艺不卖身……”
我们上的班,都是白天闲晚上忙,这给了我们不少相互走动的机会。当我们打扮一新地走在街头的时候,总能引来不少热辣的目光。
正是青春年华,十八廿二无丑女,再加上刻意打扮,自然是赏心悦目。
相处久了,我觉得她们都是本性善良的人,而且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良爱好,慢慢就把她们当成好朋友。
过了一段时间,遇上旧城区拆迁,业主让我另找地方。她们俩人极力邀我与她们住在一起,说房租三个人分摊,又可以省下一笔钱。
她们住的地方我去过,虽然很旧,但比较宽敞,还剩下一个空房间,于是我答应了。
找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她们帮我把家搬了。说是搬家,其实除了衣服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我一直想着存钱开酒庄,平时除了买点衣服外,什么东西也不舍得添置。
这一天又是周末,夜总会20多个房间都满了。我气喘吁吁地提着啤酒送往各个房间,脚被高跟鞋磨得生疼。挣这点小钱真不容易,如果能自己开个酒庄,又何至于如此奔波?
我暗暗鼓励自己,现时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待我储够钱,便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酒庄里当老板了,因此即使脚被磨破,我依然健步如飞,神采飞扬。
人最怕就是没理想,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在奔往理想路上的所有苦和累,都会减半甚至可以被忽略。
还是“贵宾一”,我见到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正在心里暗想是不是熟客时,有人叫我:“喂,阿冰,还记得我吗?”我抬头一看,一双明亮的眼睛,那满脸的笑意,令我一下子就记得刘小姐生日的那天晚上,那个临时拉我做女朋友的男孩子。
我笑了,向他伸出手:“彪哥!怎么来了都不给我打个电话?”纯属场面上的套话,其实我们根本没互留电话。他伸手拿过我挂在胸前的电话,按下了一串数字,然后再掏出自己的电话按了几下:“好了,我记下你的号码了,以后有事可以找你了。”
我笑着说:“好呀,有好事别忘记我。对了,今晚是什么活动?好像人比上次还要多。”
他朝我笑笑:“大哥宴请兄弟们,当然是庆功宴了。”
我说:“你们大哥的生意做得好大。”
虽然感觉那晚的小混混挺多,但想起波哥那晚表现得儒雅有礼,对刘小姐的深情款款,料想他也是正当商人吧。
彪哥低声说:“总之是食大茶饭的啦,说了你也不懂。”大茶,是一种剧毒中草药,据说大补,如果吃得合适,对身体非常有益;如果吃得不当,毒发身亡。每年秋冬时节,便有广东人冒死吃大茶汤,与冒死吃河豚,应该是同样道理。
前者,人们贪其大补;后者,人们贪其美味:归根到底都是为口腹之欲。
人这一生,总免不了时时为自己的欲望埋单,只是有的价廉些,有的昂贵些,有的仅只需几张纸币,有的却需要付出性命。
由于当晚的客人比较多,我把10打啤酒送到“贵宾一”后,便到其他的房间走动去了,待过了一个多小时后再到“贵宾一”,发现基本上没有人唱歌了,房间所有的茶几都被拼合在一起,所有的人团团围住茶几。
他们在赌“三公”,每个人桌前都堆着一堆钱,波哥坐庄。看样子波哥的心情不错,不管输赢,他始终都笑口吟吟。
在娱乐场所赌博,本来是大忌,但在这间夜总会,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据说老板在市里有熟人,每次不管公安消防还是卫生检查,都提前有人打电话过来打招呼,尤其是周末,派出所根本不会来人。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又为“贵宾一”补充了10打啤酒,便到别的房间走动。为几个房间的客人送了一些啤酒后,因为数量不够,我便到夜总会的仓库拿酒。
说是仓库,其实是杂物房,是夜总会临时为啤酒公司提供的存货点,里面还有一些备用的桌布和一次性用品,甚至碗碗碟碟等。
当我听到楼下传来的警笛声时,也没有想到这与夜总会有什么联系,更没有想过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会改变我的一生。
我提着啤酒走到外面时,听到到处是混乱的脚步声,还有大声喝骂,客人们歌也顾不上唱了,纷纷从房间里钻出头来,惊疑不定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火警?”
“差佬封局!”不知道是谁在叫嚷。
差佬是公安,封局就是抓赌。“贵宾一”!我立即想起彪哥那帮人,还有桌上堆着的一堆堆的钱!
到处一片混乱。我也顾不上送啤酒了,连忙跑到总台去,看看什么情况。老板已经在气急败坏地打电话了,他平时极少过来,只是遇上周末才过来照看一下,想不到竟然遇上这种事。
“什么?不是你们?是刑警队的人下来?那你叫我怎么做生意?
30多个房间,全乱套了,差佬来搞档,以后谁还敢到我的场子来玩?”他在电话中质问对方。
估计是对方在电话中解释了几句,他脸色才好些:“好吧,如果只是想查‘贵宾一’的人,就叫你的兄弟快快把‘贵宾一’的人带走,不要惊动其他的客人。”
放下电话,老板对站在一边战战兢兢的众人说:“都去安抚客人,告诉他们,没事,没事。歌照唱,舞照跳,酒照喝!”
不等他说完,突然听到从“贵宾一”那边传来惊天动地的呼叫,然后从房间里冲出许多穿制服的警察,往门外奔。
不知谁嚷道:“有人跳楼了!”
天啊,夜总会是八楼!我忙跑到收银台旁边的窗口,打开窗户往下看,隐约看见一个人砸在一辆小车顶上,一动也不动。
老板站在我身边,脸色惨白:“这下生大事了。”
对于出来寻欢作乐的人来说,但凡娱乐场所死过人,便视为不祥之地,自此会无人问津。
“贵宾一”的人一个个地被押了出来,走出门口时,都路过收银台。我默默地看,没有发现波哥和彪哥的身影。
摔到楼下去的,到底是波哥还是彪哥?我同情地想,如果是波哥,刘小姐该多么难过啊——她的愿望,是一辈子与波哥在一起。
因为死了人,小事也变大事了,只一会儿,远处便传来救护车和警车的呼嘯声。从窗台往下看,到外都是闪烁的灯光,还有穿着制服的警察。
救护车上下来的医生看了一眼摔在小车顶上的人,再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的眼睛,挥挥手,看样子是表示不行了,与身边的警察说了一会话,估计是让他们通知殡仪馆,然后上车走人。
更多的警察不断地涌进夜总会,所有的灯全部打开了,到处明晃晃的,真实得不像我熟悉的夜总会。所有的客人被通知待在房间里接受问话,待证实无事后方可离去。
老板双脚发软,站都站不稳了,歪歪地靠在沙发上,双脚直打战。想想看,一帮赌徒在他的地盘聚众赌博,然后其中一个跳楼死了,不但夜总会得关门,巨额罚款更在所难免。一句话,他要破产了。
被盘查后证实无事的客人陆续走出房间,离开夜总会。今晚的一夜白忙活了,我心里想着,暗暗庆幸后来给客人点的十几打啤酒没有送出去,这才突然想起放啤酒的杂物房的门还没有关,便走过去打算关好它。
奇怪,门竟然推不开。难道我已经关了?我掏出锁匙打开门,在我打开门的一瞬间,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估计对方也在想趁我打开门的时候冲出去,所以我们生生地撞在一起。他看清楚了我,我也看清楚了他,是彪哥!
那么,刚才跳下去死在车顶上的是波哥了!我心里叹息一声,竟然没有害怕,只是呆呆地看着彪哥,心里,在为刘小姐叹息。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像刘小姐那样,要承受生离死别的痛苦。
因为,我们都选择了同一类男人。选择了什么样的男人,便意味着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怨不得别人。
他把一个黑色的大皮包塞到我手上,不容置疑地说:“这个包你先拿回去,我迟些时候再找你。”不容我拒绝,他便冲出门外,大声叫,
“波哥!波哥!”
很快,我听到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冲过去盘问他,把他带下楼了。
我把门反锁上,放下手中的大皮包,很重,估计有30斤。我拉开皮包的拉链一看,是一叠叠的百元大钞!一卷卷地用橡皮筋扎着,不知道有多少卷。
我心跳加速,几乎是立即下意识地拉上拉链。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我摇摇头,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可是此刻,这个黑色的皮包就真实地握在我手上,如果我就此离开,这些钱就属于我,谁也找不到我。
后来我无数次地想,如果在把这些钱塞给我之前,彪哥征求我的意见,我会答应帮他保管这些钱吗?不知道,如果再来一次,我依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因为这并非我的选择,而是他的选择。
可是,有时候,别人的选择,却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生。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蛮不讲理。
事后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警察在封了“贵宾一”后,以为桌子上的赌资就是全部的钱了,根本不知道波哥还有另外一个装满巨款的黑皮包。
当天晚上,在听到楼下骚动的时候,波哥与彪哥带着那袋钱趁混乱钻进了空无一人的杂物房。把钱藏在杂物房后,波哥便爬窗躲到了墙体外面的空调机外,想不到楼下的警察用手电筒一照,心慌意乱的波哥便掉了下去。
当我在外面推门的时候,彪哥正拿着钱左右为难,当他看到是我时,干脆就把一大皮包钱交到我手中,他自己却走了出去。后来他告诉我,他觉得夜总会是我的地盘,料想我把黑皮包带出去不是难事。
其实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
来不及思考,我机械地用黑色的塑料袋装好黑色皮包,再用角落的桌布盖好,然后走出房间。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几个服务员一脸惊疑地面面相觑。从窗户往下看,楼下也零零星星仅剩几个警察。
反正留下来也没事,我跑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把裙子的后摆全部冲湿了,然后慌慌张张地走出去问服务员:“你们谁有干净的衣服在这里?我大姨妈来了,借我穿一下。”
年轻的女孩子喜欢扮靓,上班穿的服务员制服她们认为不好看,因此上班前和下班后都是穿自己的衣服。亏得我平时人缘好,马上有个女服务员与我说:“我自己的衣服在这里,你应该合身,借给你穿吧。”
当天深夜,我换上了另外一套衣服,把弄湿的衣服放在黑色的塑料袋里,压着里面黑色的皮包,与一群女服务员下班了。路过楼下的时候,留守的警察看也没有看我一眼一一在他们眼中,我不过是一个下夜班的平凡女孩。
他们不知道,我袋中的东西,比他们一个晚上的“战果”还要丰富。
在路边等出租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黑皮包里到底有多少钱?
8万?10万?应该差不多了吧?我虽然在夜总会里卖啤酒,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可是卖啤酒的提成,我最多的一次也不过拿了几千元一一那不算厚的一叠,在我看来已属巨款。
如今,我竟然有一大皮包的钱,我惴惴不安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每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人,都形迹可疑得像打劫犯。这个我曾经无数次地在此等车的路口,变得陌生而阴森。
直到一辆出租车来到,我在上车前还特意看了一眼车牌,上车后对司机说了目的地,就开始装模作样地打电话:“喂,我上出租车了,车牌号是粤……对,如果半小时后我没到家,你就帮我报警。”
然后东扯西扯,好像与自己通话的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大人物。其实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等我。正是午夜时分,阿丽一定还在发廊守株待兔,胜男应该还在用双手为老中青各式男人的身体送上温柔的抚摩。
实质上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我没有任何依靠,就算是父母,在我无法衣锦还乡的时候,我决不会找他们,免得他们又在我耳边念经,企图超度我。
他们不知道,有的人注定成不了佛,为其念经纯属浪费口水。
待我以通完电话的姿势把手机收好的时候,司机慢悠悠地在旁边说话了:“靓女,你不知道有假车牌这回事吗?如果我这个时候拉着你往乡下的黑道跑,你朋友来得及救你吗?”
我心里一紧,真遇上坏人了?司机却又道,“半夜还要出来找食的,都是挣辛苦钱的穷人,真正的坏人都改成白天明抢了。”
我心里一松,连忙附和:“是的。咳,不好意思,师傅,我没见过世面乱说话,请不要见怪。”心里暗想,他妈的都是让钱闹的,人一旦有了钱,就会疑心生暗鬼,以为周围人都居心不良。
终于回到出租屋。我松了一口气,开门,进屋,锁门,冲进自己房间,打开黑皮包,数钱!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其间心跳加速数百下,双手发抖。
虽然钱不是我的,但现在在我手上,而且,其中有部分可能会成为我的,我有理由为它而激动,甚至精神失常。
终于点算完毕,一卷是5万元,一共20卷,我算来算去,一下以为是50万,一下又觉得可能是100万。
想让一个女人智力变低脑电波短路吗?那就给她一堆数量大得让她心惊肉跳的钱吧,保证她神经错乱。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100万元。在2004年,如果拿这笔钱在这座城市买楼,可以买下8套面积为10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想想,如果有人突然把8套新房子送到你名下,你会不会发疯?
反正我已濒临疯狂的状态。先是把数好的钱放进皮包里,想想不妥,拿出来;又想想没有更好的地方放,再全部放进去。我就这样拿着装满钱的皮包在小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甚至连洗澡间都不敢去,唯恐一走开便有人破门而入拿走了它。
澡也没洗,我抱着黑皮包睡觉了。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听到阿丽与胜男陆续回来了。
我的心终于安定了一下,可是马上新的担心又来了:如果她们进我的房间看到皮包,再打开皮包发现这些钱怎么办?
我连忙从床上跳起来,冲过去查看房间门上的插锁插上没有……
发现确实稳稳地插上了一一如果她们不用斧头劈开锁,绝对不可能进我的房间——我才安心地重新回到床上躺下。
一夜失眠。
弄了两块饼干就着自来水吃了,我打电话给夜总会的经理:“强哥,今晚上班吗?”其实我上不上班完全不用请示夜总会,与我在那里做同一品牌啤酒的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如果我不上班,与对方说一声即可。
强哥沮丧地说:“阿冰,夜总会放长假了,不用上班了。你与你们老板说声,转到其他的场子去吧。”
虽是意料之中,我仍然忍不住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