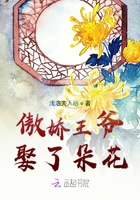海鲜市场建成后,彪哥的生活更忙碌了,他经常答应了儿子回家吃饭,可是吃了一半,往往接到一个电话便走出去,弄得儿子很失望。当他深夜回来的时候,儿子往往都已熟睡了。
一天深夜,他从外面回来,正有一句没一句地与我闲聊,说着儿子的趣事,突然外面有人叫门,是阿榜与乐哥来了。
“彪哥,刚收到风,渔民和鱼贩打算明天到市政府静坐,向市政府施加压力。”阿榜说。
彪哥说:“弄清楚是哪些人带头搞事的没有?”
阿榜说:“搞清楚了,渔民这边是捉鱼安组织的,鱼贩那边是卖鱼荣牵头。”
彪哥的脸色很难看:“妈的,老子不发威,当我是病猫!”
乐哥说:“如果公安佬压不住,我们就上了,不打死一两个没人会害怕。”
彪哥拨通陈就伟的电话:“陈老板,听说明天上午九点钟,有渔民和鱼贩到市政府静坐抗议海鲜批发市场的统一管理,你们不做点事?”
电话中传来陈就伟没好气的声音:“喂,大佬,给个场子你们挣大钱,拜托你做得不要那么露骨好不好?搞到现在渔民到处上访告状,我在常委会议上都不好交代。”
彪哥火了:“陈老板!你叫我做什么事,我何曾说过多余话?当初是你鼓动我建这个海鲜批发市场的,现在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才洗湿了个头,你反倒怪我了?你搞不定这班渔民,就让我来搞好了,出了事你别怪兄弟我没向你通气!”
陈就伟忙说:“你们别乱动,我叫人把带头搞事的人控制起来。”彪哥脸上露出笑容:“你早这样说嘛,不然明天出了什么乱子,你脸上也不会好看。”
打完电话,彪哥说:“陈就伟虽然答应摆平此事,但明天兄弟们还得做点事。”阿榜与乐哥点头称是,告辞离去。
第二天早上,彪哥竟然很难得地在家里吃早餐。仔仔一觉醒来发现爸爸在家,兴奋地冲过去爬上他的膝盖,说:“爸爸带仔仔到公园玩。”因为平日彪哥早出晚归,难得的几次在家,都是因为特别的节日,比如六一儿童节、春节之类的,因此仔仔以为爸爸早上在家,定是要带他到外面玩。
彪哥逗他说:“为什么要到公园玩?”
仔仔说:“公园人多啊,仔仔喜欢。”
彪哥笑了:“那现在爸爸带仔仔到人多的地方玩?”
仔仔欢呼:“好呀!”说罢去拿我的手袋,交到彪哥手中,“你帮妈咪拿袋,妈咪抱仔仔。”
彪哥哭笑不得:“仔仔还是喜欢妈咪多些啊。”
我宽慰他说:“你以后多花些时间在他身上,他自然会亲近你多些了。”
原来彪哥带我们到市政府的门口看热闹。我们到达的时候,到处都是人,有的人还拉着横额,上面写着:低价进,高价出,海鲜市场挣黑钱!放渔民一条生路!鱼贩无路可走!还有的拿着大卷的报纸,席地而坐。
市府大院里面,保安把铁闸紧锁,如临大敌地对着外面黑压压的人群,此时正是9点钟,要上班的人被堵在门口不得其门而进,人人都在议论市府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了一眼彪哥,他抱着仔仔,若无其事地笑,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
突然,人群里骚动起来,有人在大嚷:捉鱼安昨晚向差佬告密了!差佬把卖鱼荣捉起来了!”
又有人拿着麦克风大嚷:“是卖鱼荣出卖了捉鱼安,捉鱼安刚才打电话给他老婆,说卖鱼荣出卖了他!”
顿时,整个场子都乱了,市政府门口的人们,迅速分成两派:一派渔民,一派鱼贩。此前他们分别以捉鱼安与卖鱼荣为召集人,可是现在他们人影不见,大家的心里便不安起来。
“其实捉鱼安与卖鱼荣都没事,他们现在在家里好好地待着呢,他们鼓动大家来为他们卖命,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去捉鱼卖鱼呢!”又有人在人群中高声说。
“他妈的!骗老子来这里闹事,自己却跑去悄悄做生意,老子也不闹了!”人们纷纷把手中的横额和报纸扔在地上,瞬间走掉了一大半。
余下的人虽然坚持坐在市政府门口,但气势已减弱。突然有人走近场子里叫:“真是一班傻瓜,你们都不去卖鱼,现在市场上的鱼价比昨天升了一倍多!”
还在静坐的人也坐不住了:升了这么多?那我还是回去先卖鱼好了……”
不到10点钟,整个市府大院门口人都走光了,只留下满地残败的旧报纸。从市府里面走出几个搞清洁的大婶,迅速把地上的报纸清扫完毕。市政府门口又变得干干净净。
彪哥笑着说:“没热闹看了,咱们回家吧。”
我说:“卖鱼荣真的在卖鱼?”
彪哥说:“不知道。我先送你们回去,我得到市场看看。”
晚上吃饭时,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消息:“因为鱼贩与渔民发生矛盾冲突,一名外号叫卖鱼荣的鱼贩被几名疑似渔民的男子持刀追打,双脚被砍了十多刀,左腿腕被当场砍断,现场无人敢伸手相助,直到有市民报警后才有医生赶往现场……鱼贩与渔民之间的争斗由来而久,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仍须加强……”
我默默地放下饭碗,进房间打电话给彪哥:“卖鱼荣的脚是你让人砍断的?”
彪哥说:“你问这些做什么?仔仔乖不乖,吃饭快不快?”
我含泪说:“彪哥,请你告诉我,卖鱼荣的脚是不是你叫人砍断的?难道仔仔吃饭快不快,比不上人家一条腿重要?”
彪哥说:“断人衣食,犹如杀人父母,不杀一儆百,以后还会有人再犯。”
我说:“低价进货,高价卖出,你这样做,只会逼到鱼贩到邻市进货,到时偌大的批发市场无人进去交易,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彪哥不以为然地说:“谁敢到邻市进货,我叫他倾家荡产!”我长叹一声,再也说不出话。从什么时候起,他变得如此决绝而冷血?好像是突然之间,又好像是在慢慢地变化。我的话,对他来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分量,既影响了不了他的想法,更影响不了他的做法。
两行冰冷的泪水缓缓地从我的脸上流下来。
仔仔端着碗跑进房间叫我:“妈咪,你为什么进房间?你不是说要吃完饭才可以做其他的事吗?”
我哽着声音说:“没事,妈妈让一根鱼刺哽在嗓子上了,进来弄一下。仔仔说:“噢,妈咪让鱼刺弄得流泪了,以后吃鱼要小心呀。”我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把脸伏在他的背上,喃喃地说:“是的,妈妈让鱼刺弄痛了。”
第二天,彩婶从菜市场买菜回来,告诉我:“今天的剥皮羊卖到20元一斤。”剥皮羊是一种海鱼的名字,因为外皮比较厚硬,人们用这种鱼做菜的时候,必先把鱼皮剥除,然后再煮食。这种鱼肉质细嫩而味道鲜美,配以胡椒做汤最是好吃不过,故而彩婶常常买来做。我说:“这种鱼平日不是10元一斤么?怎么突然升到这么贵?”彩婶说:卖鱼的人说,现在这种鱼在批发市场都要18元一斤呢。”我说:“为什么突然升得这么厉害?”
彩婶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市场上的人都在说,此事与李先生有关。”
我说:“说来听听。”
彩婶说:“他们说,恶人……彪动一下,全城的人没鱼吃。”
我明白了,淡淡地说:“去做饭吧。”
“哦。”彩婶默默地走开。仔仔却欢声道:“噢,恶人彪好厉害,我也要学恶人彪,动一下让全城的人没鱼吃,只给我妈妈鱼吃。”
我的心头五味杂陈,只好引开话题:“仔仔,你九月份就要上幼儿园了,妈妈教过你的儿歌,你会唱没有?唱得不好,幼儿园是不会收你的。”
仔仔说:“谁说我不会唱?我唱得好听又大声,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这一年的秋天,仔仔进幼儿园了,我与彪哥商量:我想开间酒庄。”彪哥说:“我每月给你的钱不够用么?”
我说:“不是,你每个月给我的钱,都剩下大半,这几年我手中剩下的钱,都可以打本开酒庄了。”
彪哥说:“既然钱够用,为什么还要开酒庄?开酒庄能挣多少钱?一个月赚的钱,恐怕不够大富豪饮食城的一顿饭。”
他已完全忘记了这是我当初的理想,我说:“我想开酒庄,不是为钱。”
彪哥笑了:“傻妹,是因为无聊?无聊就参团外出旅游,哪个国家你随便挑,反正咱们不缺钱。”
我说不出话来。他搂着我,说:“不让你开酒庄,我有私心一一我怕有人知道酒庄是我阿彪老婆开的,会去捣乱。我不怕别人找我的麻烦,但我怕别人找你的晦气。”
我涩声说:“这两年,你得罪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