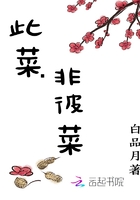“蓬”
地狂使劲浑身解数、将全身功力提至极限、才勉强阻挡了雪球暗器的必杀一击,但他的人至少被雪球激带的强猛劲气撞得向后倒退半丈有余。
雪球遭地狂劲道十足的护体真元正面对心碰撞,突然生出“啪”地一声爆鸣,炸成无数碎片。每一片碎雪块都裹含着陆琴风劲道十足的螺旋和直进的真元气流,化成万千让人无法捉摸方向和准绳的“箭矢武器”,沿地狂没法掌握的万千道攻击路线,无情地朝他全身上下如雪网般罩了下去。
地狂骇的肝胆欲裂,并不是因为无法躲过这些劲道十足的雪片,而是发出这颗雪球的神秘人。一个人若要将真元注入到冰雪山石等凡物之中并非难事,但要把气劲等分成无数份均匀地分配到这些凡物中便就困难非常了,更何况还要保证这些被灌注了气劲的凡物在爆碎后还能保持原有的那一份劲气,那已不是常人能够从容做到的。最可怕地是,这颗雪球暗器竟似乎是来自上空数十丈高处的崖顶,其中需要施放者的眼力、对自身真元收放的控制力、以及暗器在空中轨迹的位置计算都应精准而不偏差分毫。
能够做到以上几点,此人若非是修行足有半个世纪的大宗师,也必然是步入半仙级的仙门老前辈。
地狂于刹那光景,将全身数十年的修行灌注到两条腿肚的腓肠肌内,脚踏奇步,带动身子不拘陈法地向后疾退。无数被灌注了陆琴风两股真元的“雪网”就像是嗅到蜜糖的彩蜂,如蚁附膻地贴上地狂被风掀起的衣角而来。
雪块碎片体积虽小,携带的气劲也不多,击中人体后本不会生出多大痛楚,然而毕竟呈现在地狂眼前的是无数道型呈网织的万千片残雪碎屑,若被刺中,到时全身上下都好似被毒蚁蛰咬般痛痒参半,那种噬心的折磨恐怕比剖腹自尽还要惨烈难耐。
地狂不敢大意,百忙中自袖内探出自己的压箱绝技——银龙宝枪。双足不改先前的退势,另手却一把扯下裹体的黑衣,然后枪尖疾探,挑住黑衣的背心,劲气到处,尖头和黑衣紧密联结一体。握枪的臂腕“唰”地逆转半圈,银枪顿如活了过来一般,哧溜”旋动着伸长数尺,旋合的枪头同时反向急转,带动枪尖挑起的黑衣如一块乌黑的伞布似地旋转起来。
眼见黑衣幻成的伞布愈旋愈快,渐渐已分不清袖头领襟,地狂突然顿足,持枪的手臂倏忽间沿虚空划开一道径长尺余的圆弧。
黑衣旋伞在枪尖的带动下急旋着破开苍穹,留下的黑影眨眼间铺满了地狂的眼前半米外的虚空。只是黑衣闪动委实太过旋急,留在虚空的黑影久久不能散去,乍看之下,便似一片有形而无质的纯黑步幔如陡岩峭壁般纵向插在地狂的身前,正好拦住了那雪网的所有进路。
“雪网”终于撞上了“纯黑布幔”。只听无数声细微却刺耳的“嗤嗤……”异响,好像有万万千千的小股真劲相互碰撞,并互相溃散。足足有眨眼间的数息光阴,“纯黑布幔”与“雪网”才完成对撞,并终于都沉寂消匿了下去。
“噗”,地狂虽侥幸躲开了被无数含劲雪片刺肤的危险,但终因舞动银龙宝枪时体内真元消耗甚巨,又被“雪网”和“纯黑布幔”交击时迸发的残劲所伤,这时气力不济下却无法抑制胸口的烦恶,忍不住张口喷出一股鲜血。
“好功夫,”地狂抹了一把嘴上残留的血渍,两眼牢牢地盯着数十丈高的崖顶,虽然入眼的只是烟雾缭绕,但他心中坚信那迷茫的烟雾下定然隐匿着一个不世出的绝顶高手,口中忍不住钦叹道:“前辈这身功夫便是放眼整个五届,只怕也难寻出十余人来。但叫晚辈不解地是,以前辈的修为,为何不去中土开宗立派,反而留在我们冻古蛮荒忍饥耐寒?”
崖顶的陆琴风只差点儿没有笑破了肚子,暗忖“老子若去开宗立派,首先便要创立一个污月派,专门将月染得脏乱污秽,留给你们净月派去清洗整理。况且老子早想离开这个兔不拉屎的鬼地方,只是苦于背后不能生出翅膀,没法飞跃那座云峰。”干咳一声,清了清嗓子,他忽然探出左手食中二指捏住自己的嗓门,将声调变得苍老且沙哑地道:“老夫朽木一堆,徒有一身劈天裂石的修为,却无法留住逝去的韶华。只是小娃儿年纪轻轻,功夫也蛮不错的,为何不去中土闯荡闯荡呢?”
既被地狂尊称作前辈,他当然不可错过这个提高身价的机会,“倚老卖老”一番。当然他也猜出地狂不是不想去中土闯荡,而是没法克服那座百丈冰山,这般说话只是故意让地狂久积的压抑情绪加重,从而没法听出自己这个“冒牌”前辈的声调。
果然,崖底的地狂沉默了好一阵子,似乎费了好大劲才压住沉闷的心事,然后才充满自怨自艾的苦笑韵味地道:“前辈真会说笑,晚辈自从五岁开始潜心静修,迄今算来已有七十六余载,如今已是风烛残年,又哪里还有残余精力去闯荡磨砺。况且七十多年的苦修却不及前辈一层之功。唉,晚辈自知资禀愚钝,再不敢有何进级成仙的非分之想。”
陆琴风一愣,显然没料到自己的一句谑言竟让地狂产生了如此大的意冷心灰的心境,心中暗叹一声,正要不忍地坦言相告,突听崖下的天狐仙道清一声清喝道:“听阁下一副看破尘世的清高风度,却不知在这殒命崖顶隐居了多少年月?”
陆琴风耳听天狐仙道这声含喝的询问有些威逼胁迫的味道,心中老大不欢喜,暗忖“你我见面时,你硬是处处出言顶撞老子,现在趁着老子身份被无形中提高的机会,且看老子如何讨占你嘴舌上的便宜。”于是打消了立即公开身份之念,又捏嗓装成沙哑地道:“老夫百年前已在这座崖顶独居,准确算来,应该是一百又三年。”心忖老子装的年龄愈老便愈能压服你这个桀骜不驯地天狐。
“哦,”崖底的天狐仙道声音突然变得喜怒难测地道:“一百又三年,那么阁下肯定不知中土这百年来的大小异事,也肯定不认识在下了。”
“你老头儿简直是废话连篇!”陆琴风心底气道,“既然老子一百多年前就留在了这里,又从何得知这一百年内中土的事情?”但嘴里当然不能这么说,只装作一副老气横秋口吻道:“如果凭借天星移位、日月穿行来猜渡世间之事也算知晓的话,那么老夫或者可以猜出小娃儿你的身份。”
“哈哈……”崖底的天狐仙道突然大笑起来。
陆琴风却觉不出自己这种足可称得上是“世间一绝”的回答究竟有何可笑之处,忍不住问道:“小娃儿,你笑什么?”
崖底的天狐仙道似乎很在意陆琴风对他“小娃儿”的称呼,闻言突然止住笑声,冷哼两声道:“小娃儿真是井底之蛙,却偏偏还要充作无事不通的假道人,哼哼,五十年前老夫就与地狂上过此崖,并在崖顶大战了一天一夜,如果你果真在崖上呆了一百多年,却为何会认不得老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