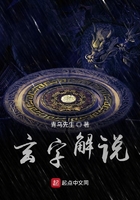须臾,皇上抿嘴一笑起身,摇晃着身子,提着镶嵌翡翠玛瑙的金壶踉跄向我而来。
我左边位置虚空,听说是留给皇后娘娘,却偏逢娘娘身体不适,不能前来。右边,便是三公主,皇上此行过来,莫不是来寻我?我心下一紧,他已来到我面前,手中壶置于案上,“嘭”的一响,我不由一惊。
他含醉的眸光颇是迷人,斜睨着眼,兀自的打量我笑着,口中含糊不清道:“想不到,想不到,深宫中,还能遇到懂得丹青的知己。”
我倏然一惊,皇上这是如何了,竟然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说出这等言语。我慌忙起身俯首,他低了头,挑眼从下面打量我的面颊,一脸醉意地笑说:“朕,朕就喜欢西洋画,很好!”他摇摆着手,脚下摇摆不定。一旁的太监慌忙来扶,却被他一把推开。他舌头发僵说,“朕不怕有伤风化,八夫人喜欢画,朕便与你做画偶可好?”趁了几分醉意,笑了打量我的眼神都含了几分色迷迷般悠悠道:“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说罢,伸手一把擒住我皓腕,那手却是冰凉如玄铁。我的心惊得霎时狂跳,急得抽手不得,却无处能逃。他却低头打量我的葇夷,强拉起凑去鼻边轻嗅,啧啧叹息:“纤纤玉指,果然是作丹青之妙手。”
我又惊又羞,谁能想到眼前登徒浪子,竟然是一国帝君。是生xing放浪还是酒后无德?若是旁人,我便挥手一掌抽他面颊,只是他是皇上!
众人无不愕然,贞妃更是愕然。致深倏然起身,眉头一拧,大声道:“皇上,这是醉了。”声音冷冷的,大步就要过来。
妻子当面被戏,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是眼前人是皇上,可致深看似毫不忌惮,就要冲来为我解围。
太后面色一沉,呵斥道:“你们这群奴才,皇上醉了,还不快快扶他下去安歇?”
但眼前的尴尬,皇上的酒后孟浪,我忽然见他眸光中的隐隐愤恨和快意,如积蓄压抑了许久的岩浆,蓄势待发一般。只不过须臾间,我忽然觉得此事蹊跷,他的眸中分明是报复般的快意,他有恨。
事关大体,若是此刻稍有意气用事,只怕致深和皇上的嫌隙更深了。不能!
皇上的手一空,身子一晃便要倒下,急得我忙去搀扶,他却坐在了我身边的椅子上,拉住我的手哈哈大笑。
若是致深此刻扑来,怕就是中了计。我急中生智,起身一笑对了一旁愕然无措的贞妃道:“贞主子,怕是皇上醉酒了,错拿臣妾当做主子你了,贞主子快来这里伺候皇上吧。”说罢我向后撤身,手向外扯。他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不甘心。既然醉了,我就对付醉鬼罢了。我面颊含笑,吩咐内侍们说:“怎么愣着?没见皇上醉了,要起身待人搀扶呢。”说罢一手按住他的腕子,含着笑,只用尽全力在他腕间穴位上一掐,趁他手一抖,我奋力一撤手,抽出了手。心里暗自庆幸,便是那手腕上令人手臂酥酥麻麻的穴位,还是致深同我嬉戏时教给我的。
皇上恼羞成怒,挑眼冷冷地望着我,趁了些许酒意喝一句:“大,大胆!”
贞妃已过来伺候,我将她索性推去皇上怀里,趁机吩咐身后的宫女:“还不去给皇上备一碗醒酒汤来?”
庆幸自己金蝉脱壳,我心下暗想好险。致深徐徐撩了衣襟坐下,慧巧对我悠悠一笑,似有令我侥幸逃脱的隐隐怅憾。我心里便多了几分对她的提防。
难道因宫中是她的老家,她便如此肆无忌惮地卸下面纱了吗?这口气,我不能这样忍下去。
我敛衣坐定,淡笑了对她盈盈说:“多谢姐姐在圣驾前替妹妹美言了,只是漪澜那点子雕虫小技的丹青,实在不足挂齿,岂敢在君王御驾前自作聪明班门弄斧?”
太后看看我,又看一眼五姨太慧巧,似明白几分,不觉得淡然一笑。
佳丽却不明就里,起身为太后添酒,娇滴滴笑盈盈地说:“若说我小嫂嫂的画技,果然传神呢。那么多人为我大哥哥画像,都没有小嫂嫂画得眉眼神态逼真呢。”
太后长长地“嗯”了一声,打量我笑笑,忽然转向致深拉长声音问:“铭哥儿,你那个幼弟人在何处呢?”面容便渐渐阴沉下来。
在一旁吃醒酒汤的皇上也放下汤碗,向致深望来。
致深却含笑云淡风轻般地答:“臣弟福薄命浅,平日里娇贵,一路上染了海风,害了肠痧,险些个丢了小命,臣便打发他回兴州了,改日再来给老佛爷请安。”
太后老佛爷把玩着自己长长的镶嵌珠玉的尖尖指甲套说问:“你就不怕,这一路上又遇到兴州那伙子革命党乱匪……让他枉送了性命?”话音一落,凌厉地目光如剑一般刺向致深。
我一惊,这话音幽幽的,难不成老佛爷另有所指。
一句话风云骤变,正这时,太后忽然调转话锋,冷冷地问:“有人告发,说是此番兴州大乱,就是你那个谋逆的兄弟勾结革命乱党,助纣为虐,居心叵测。这场暴动,就同他休戚相关!”她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bi问,“周大人如今胆子大了,心也大了,胆敢抗本宫懿旨,在本宫眼皮儿下私放人犯了。”
我一惊,仿佛惊涛骇浪一波高似一波汹涌拍岸而来,仿佛前一刻是风平浪静,瞬息间便是雷霆风暴直直砸来。
致深却是安然不动,轻轻一笑,无奈摇头道:“太后这可是冤枉微臣了,九弟他身子弱,天生不足,福薄命浅,大病卧倒途中……”
佳丽也慌得随声附和着:“老佛爷,哥哥所说句句属实,九哥的肠风犯了,疼得打滚口吐白沫,不信,澜姐姐和慧巧都可以作证呀。”
太后将信将疑地打量我们,唇角一撇勾出意味深长的笑。
致深躬身拱手启奏:“老佛爷,微臣斗胆,也不敢抗旨妄为。只是,兴州乱党围城一事,另有隐情。所谓的兴州的革命党乱党,纯属的子虚乌有。怀铭抓了几名乱党,审问之下,才知道他们不过是山匪,黄毛匪贼,打家劫舍的草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