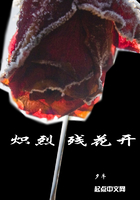周日上午,简在家里睡觉休息,等她醒来时,闹钟显示时间已经是12点了,她躺在床上没有动,直直的瞪着天花板,看着上面的纹路,试着做一些自由联想。
每次她做完,或者准备做一些事情时,就会问自己为什么会想这些?其实,自从半年前发现危险的征兆后,她早就可以自由的选择离开,而完全不必一直等到现在,才去玩什么惊险逃脱。
她也有点搞不懂为什么,是因为侥幸心理,肯定不是;是因为舍不得离开,那些熟悉的生活和朋友,也许吧。
她只知道,自己正在体会很惊人的经验,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了,所以,她不想浪费这个机会,她要是能够解除所有的管制就好了,这样也许,她就会在醒着时做梦。
下午13点半左右,简·雷诺兹走进了皮尔咖啡厅,就在月亮街的街角,这是一家很温馨的咖啡厅,有小小的圆桌和黑色的椅子,橱柜里放着各种糕点,屋里弥漫着咖啡和牛奶的香气。
咖啡厅并不大,有许多人围着几张餐桌坐,她走到大理石吧台那儿,要了一杯柠檬茶,又要了一份三明治,她端着茶杯走到一张空桌子坐下来,并注视着门口,这里不断有人来来去去,其中的很多人,都是她熟悉的邻居。
细嚼慢咽的吃完东西后,她走过去与店主告别,然后到咖啡店外坐上了出租车,出租车也刚刚到门口,是在她点餐的时候,就请咖啡店的店主帮着打电话预约的。
简到了牛津街附近才下车,人们正像蚂蚁窝里精力充沛的蚂蚁一样熙来攘往,这条街道形成于12世纪,被判死刑的人经过这里,中途喝最后一杯酒,到了19世纪,才和附近的摄政街等一起,组成了伦敦最著名的商业区。
到了这里之后,才会发现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么巨大!光是玛莎百货的周围就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高楼;林立的店铺都布置得很豪华,热闹不已,好像在举办什么特别的活动,街上的行人每个人都很有气质,看起来都很富有,外国人尤其多,反而是真正的伦敦人要逛街购物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去附近的摄政街。
顺着密集的人流,简沿着牛津街走了一阵子,路上她进了一家商店买了一件衣服和帽子,感觉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她进入了塞尔弗里奇百货,在一楼的店铺里逛了很长时间之后,简进了2楼一家专卖女性衣服和鞋子的商店,向店员点了几双看中的鞋子。
为她服务的店员,记清楚她要的款式后,转身去库房给她拿符合她号码的鞋子试穿,简起身和另外一个店员,咨询和交代了一下,拒绝了她的陪同,她拿着手中的购物袋,向后侧的更衣间走去。
仅仅一分钟不到,她就从更衣室出来,已经完全变了一幅模样,换上了新买的蓝色大衣和黑色帽子,戴上了金丝眼镜,原来的白色大衣、红帽子和购物袋,都被她留在了更衣室。
截然不同的装扮,再配合上她与原来完全不同的行为举止,露西那样的熟人都不可能认出她来,她现在即使走在监视的人面前,他们都会对她视而不见,因为他们眼里还残留着简原来的影像,大脑和注意力也高度集中于简本身,会自动的将认为无关的事物过滤掉。
很多行人都在那儿,但这些行人对他们却是不重要的,甚至可能觉得这些行人很讨厌,因为他们占去太多空间了。
在哲学和心理学上,都有对这种状况的类似描述,人们会自行“虚无化”与我们无关的事物。
哲学家萨特曾举例说:当你和女朋友约好在咖啡店里见面,你进去时唯一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她不在那儿,你看到的第一件事物,却是一件不在这里的事物,这不是很奇怪吗?至于店里当时还有什么人在喝咖啡,就是被你虚无化的。
不过,简没有直接从正门出店,这里是她早就考察过的地方,是特意选好的几个脱身之处之一。
出了更衣室向左手走几步到尽头,她停下了脚步,因为以前来过几次,她知道打开眼前的这道门,外面就是塞尔弗里奇百货的另一条廊道。
如果不从店铺里直接穿过,而是走百货商场的正常行人通道的话,得绕过大半个2楼才能到达那里,通往走廊的门是锁上的,但只是对外的,在内侧随手就可以打开,她扭开把手走出去。
关上门出去后,沿着走廊向右侧继续走几十米,打开右侧的门进入消防通道,下到一楼推门出去,在一楼跟着购物的人流,向右侧前方走不远,就是通往地铁的地下通道,到了这里以后,进进出出的人就更多了。
简已经像一条鱼儿一样,游到了入海口,外面就是更广阔的世界,她即将开始新的人生。
直到这时,在店铺里换鞋的座椅旁,商店里的店员还捧着5、6个鞋盒子,等着简从更衣室出来。此时,在店铺外面跟踪监视她的警察们,也根本就想不到,简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们的视线。
通过地下人行道,简进入地铁车站,坐着地铁一直到了国王十字地铁站,这个地铁站是伦敦地铁最大最繁忙的车站,又是通往英国东北部、苏格兰和约克郡的,5 条主要地铁干线的交通枢纽。
简随着人流向站内北部线——维多利亚线和比加地利线的共用进出口处走去,当她踏上金斯克鲁斯中央大厅的木制自动扶手电梯时,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时针正指向17点30 分。
这些木制扶手电梯,加工制作的极为讲究,摸起来就感觉很舒服,电梯载着她朝售票厅方向升去,在那里她出了地铁口,在附近找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报童,让他将一封信送往——爱德华道,绿色之春大厦3楼,乔治·亨特侦探社。
报童向他要送信的报酬,她笑着对他讲:“你到大厅的时候,见到管理人员就说,要送给侦探社的乔治先生,是一封今天必须送到的急件,然后向收信的人要5英镑,否则就不给他们信件,相信我,他们会给你的。”
然后,她转身又进入了地铁站,消失在了来去匆匆的人潮人海中,如果是上下班的高峰期,这里会有多达几万的乘客,他们四面八方的蜂集于此,又分乘不同方向的5 条地铁线路而去。
3个小时之后,从火车站出来,她对照着记忆中的景象缓缓走在街上,她对这个城镇的记忆很模糊,实际上她只来过一次,但走在街上的时候勾起了很多回忆,连她自己也不禁感到惊讶。
这个城镇当然也不是完全没变,商店街上,已经看不到以前去过的那家香肠店,记得那家店名好像叫海星,黝黑的老板很有精神地,对着商店街的路人大声吆喝:夫人,今天的香肠很棒,不买就亏大了。
简沿着昏暗的街道往前走,虽然有路灯,但并不是每一盏路灯都亮着,路灯也只维持着能够看到脚下路面的亮度。
这里是多佛尔,距离伦敦100多公里,她坐了2个小时火车才到,海峡的对面就是法国的加来,两地最近处仅相距34公里,多佛尔的本地人口只有几万人,但却是英法之间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也是英国最繁忙的一个海港,每年旅客多达几百万人次,英法间的海峡也因此得名多佛尔海峡。
多佛尔的城市特征让她选择了这里,因为外来人口众多,本地人早就习以为常,而不像英国南方的一些农业小镇,虽然看上去非常僻静,但是来个陌生人,全镇的人都会议论纷纷。
半年前发现危险后她就来过一次,用假身份租了一栋靠海的房子,她只来过一次这个城镇,现在却不断唤醒往日的记忆,她没有选择留在伦敦,虽然她不认为,有人看到现在的她就会真正认出她,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离开伦敦,更不会靠近以前住的地方。
出过一次无法预测的意外,只会让她更加谨慎小心,伦敦毕竟有很多曾经的熟人,谁知道哪个人有什么特殊能力,突然就会发现她的伪装呢,必须靠自己保护自己,之前一直都是这样过的,和别人有过多的牵扯都不会有什么好事,对目前的自己毫无帮助。
前方是一个T字路口,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眼前的路况完全符合她的记忆,她在T字路口左转,走了一会儿来到缓和的下坡道,这段路也符合记忆。
看了下手表,已经是21点了,沿着石板路又拐了一个弯,路的尽头,一栋独立的别墅跃然眼中。
她缓缓走了过去,抬起头,随即用力深呼吸,又吐了一口气,再度打量着那栋房子,房屋处于一片漆黑中,看着紧闭的大门,她心想,这就是她未来的家了。
仔细观察房子没发现异常,环顾四周,也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她停下脚步转身走向商业街,夜晚的空气很冷,但她的脸颊很烫,所以并不在意,她需要吃一些食物,终于看到一家亮着灯的小餐馆。
推开深色的店门向店内张望,前方是柜台,后方有6张桌子,一个穿着白色厨师服装的男人正坐在柜台内椅子上,店里没有其他人,就走了进去,生意好像很冷清,也许时间太晚了吧。
厨师有点惊讶地转过头:“你是客人吗?”他年约四十多岁,在柜台内侧站起来,有些迟疑的向简问道。
她向厨师温和的笑了笑,说是写东西的时候肚子饿了,也忘记给冰箱补充食物了,好在您还开门,否则这个晚上就难受了,她点了啤酒和多佛尔的特产多佛尔鲽鱼,又要了一份白面包。
餐厅内就有冰箱,她自己走过去拿了一瓶德国黑啤酒,打开瓶盖把黑啤酒倒进杯子;她很会倒酒,啤酒表面浮起两公分、像是奶泡般的泡沫,咕噜喝了一口,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独特的苦味在嘴里扩散。
清晨,她被海鸥尖锐的叫声吵醒,她起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站在窗前拉开窗帘,俯瞰着窗外的海湾;
温柔的海浪,一波波的拍打在远处的礁岩上,成群的海鸟在天空飞舞,红红的太阳,在海平面上刚刚探出半个身子,她满足的笑了。
她转身回到书桌前,在摊开的笔记里写上这样一段话:
在他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个既定的大目标或者梦想,然后他们就为了实现它们而努力。
他们都曾遭遇当头一击,一度被彻底打倒,然后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们走投无路,但是每次被击倒后,他们总会站起来,你不能摧毁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