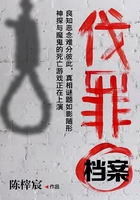刘静一路笑着,心里似有些快意,总是想乐,又不好和竹溪说,面上有些忍不住的笑,又止不住的拘束。
竹溪偷偷瞄着他,只见他又蓄了胡须,亮亮地捋顺了,活像个老山羊,心里也乐起来,也不好笑出声,憋在面上,却越憋越忍不住,刘静头摇一下,他就非得把头撇向后头张开大嘴不出声地笑,这下完了,好像被刘静打通了笑穴,无论刘静说什么,做什么,他都觉得好笑,而且难以抑制,又停不下来。
刘静也略微觉察到了竹溪的反常,心里只是高兴地没地发泄,也不讨厌,自己也止不住地想笑。
两个人就那样尴尴尬尬地想笑又不敢笑,一路往后头书房走去。
迎面只见谷坡起了个大早,穿着大蓝军棉袄,踩着黑跟硬靴出来了,刘静上前笑道:“好久不见啊,坡子哥,怎么今儿打扮地跟唱戏似的出来了?这天儿还没到时候,到了正午又该热起来了,你就穿这样出去?”
谷坡低头看了眼服饰,笑道:“这几天在家忙事儿,不出门,忘了气候了。”
说着回头就要去换,顶头霄玉一手正上着紫木耳坠,嘴上涂着淡血薄红的唇膏,满面微笑地走来,不等众人说话忙就笑道:“你这几天也留起了胡子了?一眼过去我差点以为是头老羊,唬了我一跳,原来是你!”
竹溪一听瞬间破功,仰天哈哈大笑了两声,吓得几个大人呆了半会儿,回头愣瞧他,霄玉走到跟前又笑道:“今儿去街头去见几个熟人,非得早早去了才好,趁着人家漱牙洗脸的工夫和人商议,人或一急一乐,就应下来了,我们也不陪你吃早饭了,昂!”
刘静笑道:“你们有事就先忙,我吃过了来的,今儿天不错,有些风,但是不冷,我一路骑车过来,倒觉得比前几天还热了,我就说哥这穿着太唬人了,惹不好出去人还一笑。”
谷坡说道:“我也说这袄子太早了,你嫂子非要我穿上。”
霄玉给了他一下,又帮他理了理领子,说道:“你不知道他的,外头强里头弱,成天躲屋里不见阳光的,都虚在里面,这又赶着换季的关头,我可再伺候不起一个病人了,随你怎么说,这个早晨非得依我,不然还是我自己去张罗,你就别出这个门。”
谷坡一脸无奈看向了刘静,刘静抚了抚胡须,又笑道:“那就是甄姐说的有理了,也是这样才好。”
霄玉忍不住要去掰刘静的手,笑道:“你这动作倒让我想起来像谁,可不就是上半个月那个老先生?你俩可真是师傅徒弟,越发一个模子去了!”
刘静哈哈大笑,不则一言。
霄玉携着谷坡走去,又冲着竹溪笑了一记,竹溪起身要打招呼,霄玉忙摆手要他坐下了,接着一径去了前面,哐唧唧几声,大门开了又关,他俩已面着初阳去了。
竹溪有点疑惑在心里,又不知道怎么说,忽想想倒是好久没见谷坡了,自个儿爸受伤那会儿也不见他,还以为他去了外地,怎么今天听她说这阵子都躲在家里?可真是个一影子秘密的大人。
正想着,刘静已经去了后面和老奶奶说话去了,两人不知道又就着什么话芬,聊个旁若无人。
竹溪有些百无聊赖,胡乱翻起书来,看到了诸葛亮的那篇《出师表》,他一时读了起来,初读一遍虽不大解其意,但是总觉得哪里窜来一股汹涌澎湃、慷慨激昂的风来,吹得他满心热血,不知自己想要干嘛,忍不住又一字一句地细品起来。
正这时,又有一人掀帘出来,抬头就和竹溪搭话,说道:“你霄玉大姨和你坡叔出去了?”
竹溪抬头去看是谁,原来是彩云,只见她也披着个青草绿军大袄,鬓发略散,只有一根木耳皮筋在后面扎着,他就说道:“才刚走了没一会儿,阿姨还有事问他们?告诉我,我骑车也快,去找他们。”
彩云忙摆手不止,脸上表情皱到了一块,说着‘不用不用’。
竹溪点了点头,看她又掀帘回去了。
果然她不太对劲,筱烟妹妹的猜测原来还挺靠谱。只是不知道她为什么梳理了那么久还没回来。
竹溪发现自己犯了相思病,一会不见筱烟心里直痒痒地无可释处,忽又想起那个暖炉,起身去前面去拿了,一上手,只觉温度掉了些,香味倒更浓了,他就着孔眼往里狠瞅,只见里面黑黑的有些红星儿,也管不了那么多,左右还有些热,捧着又往书房走去。
走在半道儿,看见书房窗口里有一人,歪着头看着自己刚看的那本书,他忙上前笑道:“你怎么也起来了?天冷不多焐会儿被窝?”
原来是筱云,她缓了缓头过来,笑道:“谁都像你似的?没有我们家的铺盖就睡不着觉,好好的,叫人听见才骂你呢!”
竹溪笑道:“你个机灵鬼,回回都叫你听了去了,你们家又没有不透风的墙,叫我怎么说话才好?”
筱云翻了翻书,说道:“你不用学,你就跟着我姐姐,她什么都教给你了,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你侬我侬,爱恨情仇,她都把你教得五体投地,长长久久地要在一块呢!啊~这句可太肉麻了,以后啊,还是少听你们这些鬼话才好!”
竹溪心里痒将起来,笑道:“今天这几句也被你听了去?”
筱云笑道:“你们那些事,原来也有趣,现在啊,都弄到我头上了,我也不爱听了!”
竹溪笑道:“你不爱听可就救了人了,不然以后还怎么说话?”
筱云忽坐下看着他说道:“你们那些话,可是真的?我怎么不知道妈妈晚上出去过了?”
竹溪松了松笑脸,不知道怎么措辞,半天才挤出一张脸来,说道:“你倒来问我,正经你姐姐才是最聪明的那个,你不问她。”
筱云皱了皱眉毛,急着说道:“你快告诉我呀!你还不知道姐姐?她才不告诉我这些事呢!反而你成了唯一能和我说这些的,你要是告诉我,我以后天天在她耳边吹你的好风,要知道,枕边风吹多了,她也就更向着你了,不过,你也要对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行。”
竹溪愣住了神,张嘴看着她。
筱云又摇了摇他,要他快些答复,不然姐姐就快过来了。
竹溪也急着说道:“要我想想。”
筱云等不及,摇着他似在摇一个秋千。
就在这当儿,后面已听见了脚步声,那人掀帘一现,果然是筱烟。
只见她今天梳了个齐的,后面静静坠着一片黑发,就着阳光,活脱脱像个遥远国度里一位安静的公主,筱云由不住哧地笑了出来,说道:“姐姐,你也学起了人家,好像一个安静的淑女!再给你换套戏服,你可真就能唱出来了似的!”
筱烟抬手去捏她的脸,说道:“皮相!怎么?我还不能换换发型了?以后都要留这个呢!天冷了,不留神睡着了也不会冻着。”
筱云笑道:“那我也要留!”
筱烟笑道:“去吧!我们一会上课,不能给你梳了,自己梳不好可不许闹!”
筱云笑着跑了过去,笑呵呵地也没回复。
竹溪巴着窗沿看呆了神,眼里心里都离不开她。
筱烟看了他一眼,走过去又翻了翻书,说道:“你俩刚才聊什么呢?”
竹溪还傻傻地看着,筱烟又说道:“问你话呢!傻人!”
竹溪还是没点反应,筱烟急了,拿起边上的戒尺给了他一下,这才把他拉回人间来,只见他忙忙地拐弯抹角跑进屋里来,坐到旁边,像条哈巴狗似的看着她等她吩咐。
筱烟又问了他一句:“你们俩说啥呢?怎么老不说话?”
竹溪笑道:“哦!你问这个啊!你妹妹可真是机灵鬼,咱们说的话,回回都叫她听了去了,你说她是天性爱玩,还是突然变得敏锐起来了?”
筱烟不禁皱起了眉毛,说道:“你这么一说,以前她可心大着呢!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这下看来,她还是被家里影响了,已经开始察言观色了,我说,我们还是别瞒她,省得她以后心事更沉,变了个人就不好了。”
竹溪听得这一句‘我们’,心里漫山遍野地开花,笑道:“听你这么说我就开心了,刚才她还和我做生意似的跟我交换条件,弄得我实在不好回答,这下我可以什么都告诉她了。”
筱烟问道:“还有这事?她倒真的爱这么说话,说了什么?你快说说我听听!”
竹溪笑道:“她说如果我以后把我们聊的都告诉她,她就天天在你耳边说我的好处,要不是她是你妹妹,我还真就一口答应了!”
筱烟说道:“死相!你有什么好处?凭她怎么说,你还不就是个烂了头皮的?”
竹溪低头笑了两记,又说道:“可她真的听见了我们刚在那屋说的话,追着我问呢!你说这可怎么办?”
筱烟想了想,说道:“就告诉她吧,反正我们做事小心点,别伤着婶子的脸面就是了,有她在,我们去逛的时候还有个幌子。”
竹溪点了点头,筱烟又问他道:“你今儿见没见婶子?”
竹溪说道:“见了,好奇怪的做派,问了我句阿姨叔叔走了没有,想是她又谋划了什么。”
筱烟点了点头,说道:“看来她今天要行动了,不知道要去哪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可怎么办?”
竹溪想了想,说道:“有一个好法子,你就正经围着她转,她烦了,或许就要推你走,自己立马就去行动了,你也有头绪好找,或许她又哄你去午睡,你可正好装睡,起来跟在她后头,除非这样,不然只能看运气,满院子找了。”
筱烟笑道:“说你笨,这点子不是挺好?只是,你中午不是说要出去?难不成都交给我?”
竹溪想了想,这下倒没好辙了,又习惯地狂挠头皮,筱烟一把拽过他的手来,说道:“不许挠,你看,都快不长了。”
竹溪感觉到她的手有些冰凉,忙就抓过她的手,放到暖炉上焐,自己趁机也把手捂在她手背上。
筱烟说道:“把你手拿开,我自己焐。”
竹溪笑道:“这炉子冷了,还是一起焐才暖和。”
筱烟略笑了笑,好不甜美,竹溪看着舍不得放开眼睛。
正这时,忽听帘子后头一声故作的咳嗽声,他俩忙松开了手,还吓得热出了些汗。
原来是刘静过来了,他或许在后面听了一会儿,又或许没有,只见他微眯着眼,若有所思,一手背在后头,一手又捻着胡须,轻步轻声地走过来,说道:“你们俩有福,我这几天费心力给你们出了套练习的卷子,足够你们写一天的,今天哪儿也别去了,就留在这好好做,晚上我要检查!”
两人瞬间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张着嘴巴互相望着,刘静站着又翻了翻书,背着手又到别处逛去了。
竹溪翻了翻练习,只见白纸黑字厚厚好一沓呢!立时灰了心,不知道怎么办。
筱烟埋头一道一道地作着,一句话也没说。
竹溪看了看她,执起笔,也奋力写了起来。
外面只听几处欢莺雀舞,窗户台上有些粟米,不时引得几只各色花样的鸟儿扑腾腾飞过来,这时,又有一只黑喙绿身的雀儿飞了过来,仰头不停叫唤,竹溪写不进去,脑子里都思索着这些事,真是恨得他想学会分身术,把这些事一件件都办了。
最后只能舍却次要的,选择最要紧的,那要把绿玉斗换给小宝的事还是先搁着,保不准彩云就拣着大家吃饭的当儿行动。
接着就是这堆要命的卷子,刘静一定是听见了我们的谈话,故意下绊子不让我们舒服,真是不讨人喜欢的人,平白地叫人气你,何苦呢?说回来,大约见过的老师都有这些个通病,自以为管束了学习就管住了全部,以致于自己也不知道收敛,什么都插一竿子,最后还是惹了一屁股屎,擦也擦不干净。
想到这儿心里就毛躁个没完,翻了翻卷子,语文写完还有数学,数学写完还有一张外语,写作还是俄语,神天老爷啊!我们是中国人,学那么多洋文有什么用?这镇上的人哪个能听懂?再说了,那语言那么别扭,到底有什么意思?
他想不明白,狠命挠起了脑袋,筱烟这才抬起头来,忙用笔敲他,说道:“怎么了你?写不下去?”
竹溪笑了笑,说道:“有点儿。”
筱烟笑了笑,说道:“没事儿,今儿不行,明天去,明天不行,后天,只要你在这儿,我在这儿,还怕什么呢?”
竹溪被她暖哭,真想一把抱住她,说一声‘爱’或是‘喜欢’,可是,他没勇气,他只有任由表情似哭略笑地扭动着他的脸。
筱烟笑了笑,说道:“呆子,快写吧,写完咱们再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