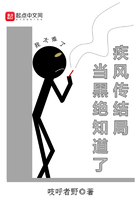时已黄昏,万籁无声,一扇已经腐朽斑驳的大铁门悄然地隔开了人世和地狱,看守铁门的狱卒看到她来,殷勤地为她打开了门。随着大铁门沉重的嘶鸣,一个昏暗而潮湿的世界正式为她打开。这里很空,空得还在门口她便能听见里面隐隐的喊冤声,哀嚎声,和钝物击打在肉体上发出的沉闷声响。扑面而来的,是汗水、鲜血和腐物混杂在一起的奇异而难闻的味道。
这一切,和她在电视里看到的差不多,但是又不太一样。
如果非要深究的话,可能是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她竭力地按捺下去内心涌上来的不安,步伐不紧不慢地跟着狱卒进了监狱。
大约是为了方便提审,张逸被关在挺靠外边的地方,她跟着狱卒拐了两个弯,便找到了她想要找的人。四周的牢狱倒是都空着,也不会有人打扰或者偷听他们谈话,这让她很满意。
“多谢。”宋远知有礼地朝着狱卒点了点头,那狱卒便识趣地离开了。
骤然出现的声音惊醒了靠在墙角打盹的张逸,隔着精铁打造的牢门,宋远知负手而立,静静地打量了他一番,道:“看来张大人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张逸眯着眼仔细地看了看,才认出眼前的白衣人是谁,顿时扑了上来,狠狠地撞在了牢门上,他毫无所觉,只是疯狂地嘶吼着:“是你,宋远知!你来干什么,看我的笑话吗?”
“不错。”宋远知理所当然地应道,一见到他,她心里的不安便皆数飞到了爪洼国。
张逸愣了一瞬,顷刻间反应过来,又吼道:“那你看啊,看够了吗?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倒是很好奇会不会有这么一天,不过,你应该是看不到了。”宋远知回以一个阴冷的笑,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瓷瓶,红布封口,看不透里面装着什么,她把它弯腰放在他能够得着的地方,等着他的反应。
张逸一见到那个瓶子,就猜到了那里面是什么,他瞳孔骤缩,青筋暴突:“你想我死,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我不会死的,孙大人会来救我的,我手里抓着这么多他的把柄,他不会放任我不管的!”
“哦——可是,一个死人对于他来说,不是更安全吗?他为什么要冒着被你牵累的危险,拼死把你救出来,然后让你继续威胁他?”宋远知一脸嘲讽,“一个罪臣,一个死人,纵使你铁证如山,又如何教人去信服?你以为,就凭你,撼动得了孙氏百年根基,惩治得了你的孙大人吗?倒不如——你把罪证交给我,我可以保你不死,如何?”
“你以为我会信你,那你送这个过来干嘛?难道这里面装的不是鹤顶红,还是糖丸不成?”他又咆哮着扑上来,终于把狱卒重新引了过来。
狱卒一脸谄媚地搬了把椅子过来,请宋远知坐下,又用手中刀柄敲了敲牢门,呵斥道:“老实点,听到没有!”
宋远知作势揉了揉太阳穴,叹道:“唔……吵的我头疼,对了,张大人,你的头还疼不疼?”
她的毒舌和冷血竟出人意料地让张逸冷静了下来,他退后两步,双掌一摊,露出腕间数尺长的镣铐,哗哗作响。他恨恨地问:“我一直想问你,我们统共也没见过几次面,我送过的礼你也退了回来,我所求之事你也从未搭手,我们可以说是毫无交集,无冤无仇,你究竟……为什么这么恨我?”
宋远知的目光慢慢地转向狱卒,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那狱卒仍不放心,犹豫道:“先生,这家伙凶得很,前两天还咬伤了我们一个兄弟,我得帮您看着。”
“你看,他不是已经冷静下来了?”宋远知笑道,“你放心,他伤不到我的,如有需要,我会再来找你,麻烦了。”
狱卒无奈,终究不敢违逆她的意思,只能又用眼神警告了张逸一番,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宋远知慢吞吞地在椅子上坐下,道:“你错了,我并不恨你,只是我要拿别人开刀,少不得拿你试试刃,委屈你黄泉路上先走一步,我马上送他们下来陪你,你只安心等着便是。”
张逸脸色骤变。
“但我又何曾冤枉了你,这一桩桩一件件,哪样不是你所为?吴敏敏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子,你竟要将她挫骨扬灰,死无全尸?你一个小小的通判,为官不过十载,索贿送贿金额竟达数千万两之巨?”
“还有……你听见外面的动静了吗?他为了你,不惜火烧大理寺,销毁罪证,刺杀朝廷命官,就差劫狱了。如此目无纲纪,胆大妄为!”她目光如炬,语调冷如寒冰,像是要把张逸剥皮拆骨,生吞入腹,“这些,都要算到你的头上!回头到了阎王殿,你大可以报我的名字,可别说是我冤枉了你!”
“他?谁?”张逸敏锐地抓到了她字里行间最关键的信息,而这正是她想要听到的结果。
“你想知道?反正我们时间很多,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她望向张逸,“我这里有酒,我们可以慢慢喝,慢慢讲。”于是她转身又去找了狱卒,要来了两个酒杯,还附送一碟花生米,大有要在牢里说书的架势。
她自己慢慢地啜了一口,见张逸不动,她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讲了起来:“三十年前,长陵安阳坊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这个家族有很多男丁,但尤以长房嫡子最为出众,风头无两。他有一个自幼定下的娃娃亲,女方是他的邻居,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们会水到渠成,结为夫妇的时候,男方家里发生了惨烈的家族斗争,他的父亲死了,而女方以自己家族已经没落,无法为男方增添助益为由,在这个时候离开了他,迅速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她讲得平淡,连语调都没有起伏,可是透过她清冷如水的嗓音,人们已经看到了故事背后的荒芜结局。
“男子骤然失去父亲和爱人,已经丧失了理智,一日酒醉,闯入女方夫家,打伤了她的夫君,强暴了她……男子母亲是宗室公主,事关皇家颜面,先皇出面压下了这件事。但是女子怀孕了,十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谁也无法确定,那个男孩到底是谁的孩子,他名义上的父亲将他弃如敝履,动辄打骂,而另一个施暴者,却将他视如己出,悉心教养,甚至带在身边时时提携。”
花生米尚未见底,故事却已经讲完了,宋远知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意犹未尽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也没想到,这个故事原来讲出来竟然这么简短,果真是旁观者清啊。可惜那个男孩不争气……”
“别说了!”张逸突然又怒吼一声,双手掩面哭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