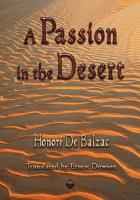“过来,”奥列弗夫人说,“坐下。你怎么了?好像很难受。”“我的双脚痛死啦。”赫尔克里·波洛说。
“就怪你那双该死的漆皮鞋,”奥列弗夫人回答说,“坐下。跟我说说有什么要告诉我的,然后我要告诉你点事情,你听了没准大吃一惊!”
波洛坐下来,舒展了一下腿说:“啊!好多啦!”“把鞋脱了吧。”奥列弗夫人说,“把你的脚解放出来。”“不,不,那怎么行呢。”波洛显然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哎呀。都是老朋友啦,”奥列弗夫人说,“要是朱迪思从屋里出来也不会介意的。不是我说你,在乡下穿什么漆皮鞋呀。干吗不买双好皮鞋呢?那些看上去像嬉皮士的男孩子穿的那种鞋也成啊。你知道吗,那种鞋一蹬就穿上了,又从不需要擦——看样子有一种特别的自净过程。多省事。”
“我根本不会喜欢那种东西的。”波洛-本正经地说,“真的不会!”
“你的毛病在于,”奥列弗夫人一边说一边拆桌上的一小袋东西,一看就知道才买了不久,“你的毛病在于你一味地追求风度。心思全放在衣服呀、胡子呀、姿势呀什么的,完全不顾舒服不舒服。如今舒适可是一个大问题。人一过了五十,舒服不舒服就是第一位的啦。”
“夫人,亲爱的夫人,我不敢苟同。”
“是吗。你最好听我的,”奥列弗夫人说,“不然,就是自找苦吃。一岁年纪一岁人,不服老不行。”
奥列弗夫人从纸袋中掏出一个漂亮的盒子,揭开盖,她用两个手指夹了一点里面装的东西送入口中,然后舔舔手指,又拿手帕擦了擦,顺口小声嘟囔了一句。
“太粘了。”
“你不再吃苹果啦?从前老看见你手上拎着一袋苹果。要不就是正在吃。
有时候袋子破了,苹果滚得满地都是。”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奥列弗夫人说,“我跟你说过我连看也不愿意再看一眼苹果了。不看。我讨厌苹果。兴许有一天我会克服这种心理又吃起苹果来——可是苹果给我的联想太糟糕了。”
“你吃的是什么?”波洛拿起颜色鲜艳的盒盖,上面画着一棵椰枣树。
“啊,改吃枣啦。”
“没错,”奥列弗夫人答道,“是枣。”
她又拿起一枚枣放入口中,去了核,扔到树丛中滚了好几下。
“枣(早),”波洛说,“很不寻常。”“吃枣有什么不寻常的?吃的人多着呢。”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吃枣。是你说‘早’字让我听着觉得不寻常。”
“为什么?”奥列弗夫人追问道。
“因为。”波洛说,“你一再给我指路,告诉该怎么办。你指明了方向。
我愿意听你的。早晚。时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事情发生的日期多么重要。”
“我不明白早晚跟这里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没牵涉到什么具体的时间。
整个事情也不过发生在——仅仅五天之前。”
“那件事发生在四天前。对,没错。但是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来说都有一个过去。过去与现在并非没有任何关系。过去可以是昨天,也可以是上个月、去年。今天总是植根于昨天。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前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个孩子目睹了这次谋杀。正因为那个孩子在过去的某一天目睹了这起谋杀案,她才会在四天前丧命。对吧?”
“嘿,是的。至少我觉得没错。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兴许就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干的,他以杀人为乐。一玩水就想把某人的脑袋摁在那儿不动。可以说成是一个心理变态者在晚会上尽情娱乐了一番。”
“你当初请我来这儿不是出于这种想法吧,夫人。”
“不是。”奥列弗夫人说,“当然不是。当时我不愿意凭感觉办事。现在我还是不愿意跟着感觉走。”
“我赞成。你说得对。要是不喜欢跟着感觉走,就得把事实弄个水落石出。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想弄个明白,不过你也许不这么认为。”
“就凭这里走走那里走走,跟人们聊几句天,看他们是不是好人,然后问几个问题?”
“完全正确。”
“那弄出什么结果了吗?”
“弄清了一些事实,”波洛说,“这些事实到一定的时候按时间先后顺序一排列就能说明问题。”“就这些吗?别的还弄清什么了吗?”“没有人相信乔伊斯·雷诺兹会说实话。”
“是指她说目睹过一桩谋杀案?可我亲耳听见她说了。”“对,她是说了,但没有人相信是真的。因此,有可能不是实话。”
“我怎么觉得,”奥列弗夫人说,“你那些事实像是引你倒退了,没有坚持你的立场,更谈不上有什么进展啦。”“事情要前后一致才行。比方说伪造遗嘱的事,大家都说那个外国女孩博得了上了年纪的富孀的欢心,老太太留下一份遗嘱(或者说遗嘱的一个附加条款),把全部财产留给了这个女孩。这遗嘱是女孩子本人还是别人伪造的呢?”
“还会有谁伪造遗嘱?”
“村子里还有一个伪造文件的人,他曾经被指控过。但是因为是初犯,并且情有可原。就被放过了。”“是一个新角色吗?还是我早已知道的?”“你不知道他。他死了。”
“哦?什么时候死的?”
“大约两年前,具体日期我不得而知,但我会查清的。他伪造过证件,而且住在本地。仅仅因为交女朋友招来嫉妒,在一天深夜被人用刀杀死。我有一个想法,这些事故似乎比我们想像的联系更紧密。有一些我们想像不出来,兴许不是全都有联系,而是有两三桩。”
“听起来倒挺有意思,”奥列弗夫人说,“不过我不明白。”“目前我也是,”波洛回答说,“不过我认为日期可以对我们有帮助。具体事件发生的日期,发生的地点,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他们都在干什么。每个人都认为那个外国女孩伪造遗嘱,也许,”波洛说,“也许大家都是对的。
她不是直接受益人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什么?”奥列弗夫人问。
“我突然有个主意。”波洛说。
奥列弗夫人叹了口气,又拿起了一枚枣。
“夫人,你回伦敦吗?你还要在这里呆好长时间吗?”
“后天走,”奥列弗夫人回答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
“那——你家里,你搬了那么多次,我都记不住是在哪儿啦——你家里有客房吗?”
“我从来不肯说有。”奥列弗夫人说,“要是你一说在伦敦有一间空的客房。马上就有人想租用。所有的朋友,还不仅仅朋友,有的只是熟人,或者熟人的远房亲戚都会写信问,让他们暂住一晚上我是否介意。我真的介意。他们一来,又是换床单啊、枕头啊、洗衣呀,还要送早茶,还得供饭。所以我不告诉别人我有一间空房。我的朋友们来了才可以住在那儿。是我真正想见的,而不是别人——不行,我帮不了你的忙,我不喜欢受人利用。”
“谁会喜欢呢?”赫尔克里·波洛说,“你可真精明。”“不过,究竟是什么事?”
“如果有必要,你能留一两位客人住下吗?”
“也许可以吧,”奥列弗夫人回答说,“你想让谁住在我那里?不是你自己吧。你自己的房子那么漂亮,超现代派的。那么抽象,全是什么正方形、菱形之类的东西。”
“只不过是也许有必要采取明智的保护措施。”“保护谁?又有人会被杀害吗?”
“但愿不会,可是这种可能性尚存在。”“谁呀?是谁呢?我不懂。”
“你对你的朋友了解多少?”
“对她?不十分了解。我只是在旅途中与她相识的,后来我们总是一块出去。她挺叫人——怎么说呢?——挺有意思的。跟别人不一样。”
“你觉得会把她写进你的书中吗?”
“我实在讨厌别人这么说。人们总这么说,可这怎么会呢。
我并不把我认识的人写入书中。”
“夫人,可不可以说你有时真的把某些人写入书中?我是说你碰见过的人,而不是你认识的人。我同意写认识的人没有意思。”
“你算说对了,”奥列弗夫人说,“有时候你还真善解人意呢。就是那么回事。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你看见一个胖胖的女人吃葡萄干面包。她一边吃嘴唇一边不停地动着,你会觉得她要么在跟谁讲话。要么在想该打某个电话。
也许是想起了该写封信。你看着她,打量着她的鞋子、她穿的裙子,猜测着她的年龄,还看她是否戴着结婚戒指。然后你下车了。你不想再见到她。但你的脑海中编出了一个故事,一位卡纳比太太坐在公共汽车上回家去,她刚刚在某处赴了一个奇怪的约会,在那里一家点心店里她看见了一个人。她以为那人早死了,可是显然他还活着。天啊,”奥列弗夫人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就是这样的。我离开伦敦之前在公共汽车上是见过一个人,现在我脑海中就编成了这样一个故事,马上完整的故事就出来啦。像她将会说什么,她是否会陷入危险,或者别人会陷入危险什么的。我甚至还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名宇是康斯坦斯·卡纳比。只有一件事能毁了这一切。”“什么事?”
“要是我在另一辆公共汽车上又遇见她,和她搭话,对她有所了解的话,一切都毁了,毫无疑问。”
“对,对。故事必须属于你自己,角色也是你自己的,她就像是你的孩子。你创造了她,开始懂得她,知道她的感觉,知道她住在何处,在干什么。
可是若是换成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话,要是你知道了这个人的本来面目——那么,故事就不存在了。对吗?”
“你又说对了。”奥列弗夫人回答说,“我觉得你刚刚问起朱迪思也有道理。我是说在旅途中我们常在一块儿,但事实上我并不太了解她。她丈夫死了,留下个孩子。可没给她留什么钱。米兰达你见过。我还真的对她们有一种很有趣的感觉。觉得她们挺重要,就像是与一场很有意思的戏剧有什么关联似的。我不想知道那是一场什么戏,不希望她们告诉我。我倒愿意把那场戏想像成适合她们演的。”
“对,对。看得出来——嘿,她们会成为阿里阿德理·奥列弗的另一部畅销书中的角色。”
“你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奥列弗夫人嗔怪道。
她停下来静静地思索了一阵说:“不过也说不准。”
“这哪是什么俗不可耐的话呢。是人的天性。”
“你想让我邀请朱迪思和米兰达到我伦敦的寓所里作客?”
“还不忙,”波洛回答说,“等我能够肯定我的想法是对的时候再说。”
“又是什么想法?我刚得来了条消息要告诉你。”“夫人,我真高兴。”
“别高兴得太早啦,恐怕要把你那些想法全部推翻了。设想一下吧,要是我告诉你,你谈了半天的伪造证件根本不是伪造的,你怎么办?”
“你说什么?”“那位叫阿,琼斯,斯迈思还是什么的太太的的确确给她的遗嘱写了个附加条款,把所有的钱都留给那个侍奉她的女孩。有两个见证人亲眼看见她签字,这两个见证人也当场并签了字。好好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