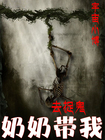只要不是公文,她就会说:‘你代替我写吧,模仿得越像越好,弄完了代我签名。’清洁工明登夫人有一天就听她这么说。因而我觉得女孩子习惯了替她写信、模仿她的笔迹。后来她突然想到可以这么做而不被发现,于是她就这么干啦。不过我说过,律师们眼睛太尖了,一眼就看出来啦。”
“是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的私人律师?”
“是的。富勒顿、哈里森和利德贝特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在曼彻斯特享有盛誉。他们一向为她处理各种法律事务。反正他们是内行。提出不少质疑,女孩子不得不回答许多问题。弄得提心吊胆的,有一天就出去了,一半的东西都没有带走。他们本来准备进一步询问她的,她可不想坐以待毙,于是溜之大吉。事实上要想出境并不难,只要选准了时间。怎么说呢,你不需要护照就能坐绕大洲一日游的客车,只要在那边和某人稍作安排就能办妥,不会惹来多大麻烦。很可能她是回国或者隐姓埋名了,藏在哪个朋友那里了也说不准。”
“而每个人都认为卢埃林·斯迈思夫人属于正常死亡吗?”
波洛问。
“对,好像从来没有询问过这件事。我只是说有某种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因为曾经发生过这类事而医生一点也没有产生怀疑。会不会乔伊斯听见过什么话,听见那个外国女孩端药给卢埃林·斯迈思夫人,而老太太说‘今天的药味道跟平常不同’或者‘这药苦多啦’或者‘味道怪怪的’。”
“这么说你当时在场,埃尔斯佩思。”警监斯彭斯说,“都只不过是你的想像而已。”
“她是什么时间死的?”波洛问,“上午还是晚上?是在屋里、屋外或者离家很远的地方?”
“哦。是在屋里。有一天她在花园干活回来时,呼吸十分急促。她说太累啦,想上床躺着。长话短说吧,她再也没有醒过来啦。从医学角度上来讲。似乎相当正常。”
波洛取出一个小笔记本。本上早已写着“受害人”几个字。他接着写道“第一可能性,卢埃林·斯迈思夫人。”下面的几页纸上他分别写上斯彭斯告诉他的其他几个的名字。
他问道∶“夏洛特·本菲尔德是什么人?”
斯彭斯马上答道:“是个十六岁的商店售货员。头部多处受伤,在采石矿树林附近的一条小路上发现的尸体。有两个年轻人成为怀疑的对象。他俩都偶尔陪她出去散步。没有证据。”
“在调查中他们配合警方吗?”波洛问。
“他们不太配合,简直吓坏了,编了一些谎言,不能自圆其说。没有判定他们是凶手。但也说不定二者之一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
“彼得·戈登,二十一岁。失业。有过一两份工作但都没干多久就被辞退了。懒惰。长得十分英俊。有一两次因为小偷小摸被处缓刑。没有施暴的记录。大法不犯,小错不断。”
“另外一个呢?”
“是托马斯·赫德。二十岁。说话结巴。害羞,有点神经质。
想当一名教师,成绩却不合格。母亲是个寡妇,宠孩子宠得有点过分。不喜欢让他交女朋友,千方百计把他拴在身边。他在一家文具店工作。没有前科。但似乎心理上有作案的可能性。那姑娘弄得他十分痛苦。嫉妒很可能是作案的动机,但是没有证据。两个人都有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赫德在母亲那里。她对天发誓说那一整晚他都没有离开家,而且没有人能证明他不在,也没人在别处见过他。年轻的戈登有些狐朋狗友替他作证说不在现场。他们的话谁知道是真是假。可谁能反驳呢。”
“发生在什么时候?”“十八个月以前。”“在哪儿?”
“离伍德利新村不远的一处田间小道上。”“四分之三英里开外。”埃尔斯佩思说。“离乔伊斯家——雷诺兹家的房子很近吗?”“不,是在村庄的另一边。”
“好像不太可能是乔伊斯所说的谋杀。”波洛若有所思地说,“要是你看见一个年轻人猛击一个姑娘的头部,你马上就会想到这是谋杀,不会过上一年半载才明白过来。”
波洛又念了一个名字:“莱斯利·费里尔。”
斯彭斯说:“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员,二十八岁,受聘于曼彻斯特的富勒顿、哈里森和利德贝特律师事务所。”
“那几个人是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的私人律师吧,我记得你说过。”
“正是。就是他们。”
“莱斯利·费里尔出什么事啦?”
“他背上被捅了几刀。在离绿天鹅酒店不远的地方。据说与房东的妻子哈里·格里芬有私情。她可真是个尤物,至今还风韵犹存。可能牙有点变长啦。
比他年纪大五六岁,但是她就爱招惹年轻的。”“那凶器呢?”
“匕首没有找到。莱斯利据说是跟她分手又找了个姑娘。
但究竟是谁一直没太弄清楚。”
“哦,此案中谁是嫌疑人呢?是房东还是他的妻子?”“你说得对,”斯彭斯说,“说不定就是他俩中的一个。妻子似乎可能性更大。她有一半吉普赛血统,脾气不小。但也许是别人干的。我们的莱斯利算不上品行端正,二十刚出头时就闯祸了,在某个地方工作时做假账,被查出伪造行为。据说他生长在一个破裂的家庭中,如此等等。雇主们替他求情。他没有判多久,出狱后就被富勒顿、哈里森和利德贝特事务所录用啦。”
“后来他就走正道了吗?”
“啊,那谁知道。他看上去挺老实,对上司们言听计从,但他的确跟朋友们一起染指过几笔不清不楚的交易。他是问题青年,还比较小心。”
“那么还有哪种可能呢?”
“也许是某个狐朋狗友干的。一旦你加入了一个流氓团伙,你若让他们失望了,保不准就有人拿着刀子向你逼来。”“别的呢?”
“嗯,他在银行的账户有许多钱。人家付的是现钞,没有丝毫线索表明是谁给他的。这本身就值得怀疑。”
“也许是从富勒顿、哈里森和利德贝特律师事务所偷的?”
波洛提示道。
“他们说没有。他们有一位特许会计师负责账目并进行监督。”
“而警方也不清楚还有可能是从哪里弄来的吗?”“对。”
“这个,”波洛说,“也不像乔伊斯目睹的谋杀。”
他念了最后一个名字:“珍妮特·怀特。”
“发现被扼死在从校舍到她的宿舍的一条捷径上。她和另一位教师诺拉·安布罗斯合住一套房子。据诺拉·安布罗斯说,珍妮特·怀特常常感到十分紧张,不时告诉她一年前被她甩掉的某个男人总给她寄恐吓信。关于那个人什么也没查出来。诺拉·安布罗斯不知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具体住在什么地方。”
“啊,”波洛说,“这倒有点像。”
他在珍妮特·怀特的名字旁重重地打了个勾。
“为什么?”斯彭斯问。
“这更像是一个乔伊斯那么大的女孩子可能目睹的谋杀案。她可能认出了受害者是自己学校的老师,兴许还教过她。可能她不认识凶手。兴许她看见两人在搏斗,听到了一个她熟悉的女人同一个陌生的男人之间的争吵。但当时她没有多想。珍妮特·怀特是什么时候被害的?”
“两年半以前。”
“对啦,”波洛说,“时间也符合。主要是没有意识到把两只手放在珍妮特·怀特的脖子上除了爱抚她之外还有可能是要掐死她。但当她慢慢长大时,就渐渐找到了正确答案。”
他看了一眼埃尔斯佩思。“你同意我的推理吗?”“我明白你的意思。”埃尔斯佩思回答说,“但你这不是绕冤枉路吗?不找三天前在伍德利新村杀害孩子的凶手而找什么几年前的凶手?”
“我们从过去一直追查至未来,”波洛回答说,“也就是说,从两年半以前查到三天前。因此,我们得考虑——毫无疑问,你们已经反复考虑过——在本村参加晚会的人中究竟是谁与一桩旧案有牵连?”
“那么现在我们的目标范围可以缩小一些啦,”斯彭斯说,“要是我们没有弄错,乔伊斯之死的确与那天早些时候她声称目睹过一场谋杀案有关的话。
她是在准备晚会的过程中说那番话的。注意,我们把这当做作案动机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不认为我们弄错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她当时声称亲眼目睹过一桩谋杀案,而那天下午帮忙准备晚会的人当中某个人听见啦,并且一有机会就下了毒手。”
“在场的都有谁呢?”波洛问。“喏,我给你列了个名单。”“你已经反复核查过了?”
“对,我检查过好几遍,但是挺难的。列了十八个人。”万圣节前夜晚会准备期间在场人员名单:德雷克夫人(主人)。巴特勒夫人。奥列弗夫人。惠特克小姐(小学教师)。查尔斯·科特雷尔牧师(教区牧师)。西蒙·兰普顷(副牧师)。李小姐(弗格森大夫的药剂师)。安·雷诺兹。乔伊斯·雷诺兹。利奥波德·雷诺兹。尼克拉斯·兰森。德斯蒙德·霍兰。比阿特丽斯·阿德利。卡西·格兰特。戴安娜·布伦特。加尔顿夫人(帮厨)。明登夫人(清洁工)。古德博夫人(帮工)。
“你确信就这些吗?”
“不,”斯彭斯说,“不敢打包票,没法真正弄清楚。谁能弄明白呢。要知道,不时有人送东西来。有人送了些彩灯,又有人送来一些镜子。还有端着盘子来的。有个人借给他们一只塑料桶。这些人把东西送过来,寒暄几句就走啦,没有留下来帮忙。因而可能会忽视掉其中的某个人,忘了他也在场。而那个人,即使只把桶搁在大厅里的那一会儿功夫,也有可能听见乔伊斯在起居室里说话。你知道吗,她是在大叫着。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名单,但我们也只能如此啦。给你。看看吧,名字旁边我都作了简要说明。”
“非常感谢。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肯定询问过名单上的某些人,他们也许也出席了晚会。有没有谁提起过乔伊斯说起目击谋杀案的事?”
“我觉得没有。没有正式记录。你告诉我时我才第一次听说。”
“有意思,”波洛说,“也可以说真是妙绝。”“显然没有人当真。”斯彭斯说。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得去和弗格森大夫会面啦。他想必手术已做完了。”他说。
他折好斯彭斯列给他的名单装进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