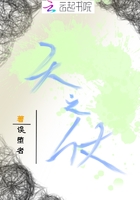她捧着剧本,下马时脚步似有些不稳,解珩匆匆迎上去扶她,却一下子愣住了。
阿邯注意到两人的异常,也匆匆赶过去,“怎么了?”
走近一看,她也愣住了,白豆儿竟浑身都是伤。
解珩皱眉,“豆儿,你……”
“父亲知道你今日要出征,不许我前来送你,就派人将我锁在房间里面,于是我……”白豆儿怯怯地望着解珩,声音越来越小,“于是我翻了窗户。”
“傻瓜,”解珩没有说剧本的台词,上前一把搂住她便吻了下去。
阿邯自知站在这里有些不妥,趁两人吻得专注,默默退回到结界内。
奈何站在那里,也无法忽略到扎眼的二人,她和太子爷只能尴尬的大眼对小眼。
“哎哎哎?不对啊,他不说台词,那珠子为何不电他?”太子爷在阿邯耳边问道。
“或许有些时候,台词就是多余的,多么精巧的语言也言不出内心苦衷,也言不尽心中真意。”
“……”太子爷扁了扁嘴,对她说的表示不认同。
皎月照耀之下,大地仿佛落上了一层雪霰,透亮透亮的,有种别样的梦幻。
亲了好一会儿,两人才分开。
解珩板起脸来,“豆儿,以后不许再这样将自己的性命当作儿戏,你若摔傻了,我怎么办?”
“其实,窗下有棵很繁茂的歪脖树来的,只不过,我没抓紧。”
他轻轻拥住她,“疼不疼?傻瓜。”
“疼,”白豆儿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小声对解珩道,“我摔下去疼得我脑子发昏,我忽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太真实了,疼也是真疼,一点也不掺假,一点也不像是演戏……你说,这里会不会就是真实的世界?那个姑娘会不会是脑子有毛病呀?”
解珩轻笑,捏着她的小脸蛋儿,“你竟然说人家脑子有毛病……”
白豆儿嘻嘻一笑,又悄悄看了远处的阿邯一眼,不好意思地对解珩道,“离得那么远,她听不见的。”
阿邯扶额,当然是听得见的。
太子爷也听得非常清楚,他听白豆儿如此说,扑哧一笑,然后摇着一个小凉扇,凑到阿邯耳边,“本宫有时候就喜欢豆儿这么单纯。”
“……”
太子爷眼中藏不住喜欢,“实在傻得可爱。”
不过确实,白豆儿单纯得讨喜,单纯得可爱,比世间那些口是心非,见利忘义的人好了不知多少,这样的姑娘总值得被好好对待。
她曾觉世事无常天命无情,刻在命运罗盘的人生有时也太过残酷,后来知道,就算再残酷,有相爱的人陪伴在一起,共同面对,也就不那么残酷了。
北山的夜实在是凉,一个特别有眼力的小宫女步步生莲地将太子爷的外衣送来了,太子爷投以赞赏的微笑,换来小宫女的一个娇羞。
夜越来越深,远方突然响起军号一声声,在空旷的北山显得尤其刺耳,大军举兵待发,这也意味着白豆儿和解珩告别的时间不多了。
听着这军号声,白豆儿的神情一下子就变了,紧紧抓着解珩的手臂,“你要走了?对吗?”
“对,”解珩神情严肃下来,将身上的长袍脱了下来,妥妥帖帖地披在白豆儿身上,低头在她眉心落入一吻,十分勉强地扯出笑意,“豆儿,你会不会怪我,怪我前日太莽撞。”
他将手放在她耳后,轻抚她耳边的发,“你看我现在还要再回到疆场,却把你置于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能一直守护在你身边……”他拉住她嫩白的小手,放在唇边,眼睛微红。
“你后悔了吗?但我不后悔的!”白豆儿微微仰着头,看见他一脸憔悴,心想,京城里最跋扈的解家三爷什么时候变成过这幅模样,她感到很心疼。
“解珩,”她轻唤他,“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愿意跟着你,总想缠着你,让你跟我玩一次家家酒,可你一次都没有答应我。”
“你对我笑,也对别家小姐笑,你对我好,也对别家小姐好,我偷偷问阿九,是不是你一直只拿我当朋友,而不是思慕在心的姑娘,阿九就跟我道,他们家爷一心想着回边疆保家卫国,哪里有闲心要什么姑娘啊?我听他这样说,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你不喜欢我,至少还没有喜欢别人……”
“父亲为我提供接近太子爷的机会,实际上,我只是通过这种假装不再喜欢你的方法引起你的注意而已……”
说着说着,白豆儿的眼泪就忍不住了,小嘴儿撅起来,眼泪吧嗒吧嗒的掉,“实际上,那支舞是我练了许久想跳给你看的,那件很美的裙子也是我想着哪一天要穿给你看的,都是给你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解珩静静地听着她说完,他心中思量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只看见他把那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小姑娘一把摁在了怀里,抱得紧紧地,“傻丫头,我不后悔,等我回来,这些日子……答应我,要照顾好自己。”
行军的号令再次响彻北山,远方的副官再三催促,白豆儿知道不能耽误行军,恋恋不舍地放开了解珩的手,眼见他上马,在朦胧的泪光里望着他纵马远去的背影逐渐远去。
解珩还是走了,白豆儿痴站了许久,北山荒冷,看到她这个样子,阿邯感到很心疼,可要想在太虚之境中看透生活的迷局,另外创造出一条生命轨迹来,就要承受住许多痛苦。
白豆儿今年不过十六七岁,心性单纯善良,从第一幕戏开始,她就知道她实在入戏太深,深到几乎分不清演戏和现实。
寒鸦扑扑楞楞地从树梢掠过,白豆儿在冷清的晚风中拢了拢额间的发。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阿邯真的十分后悔,恨自己没能及时阻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