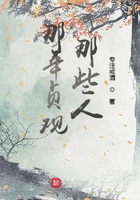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及学生到粤投考者二百余人,候已一月,旅费用罄,纷纷函诘,无从置答。现已定本月二十四日考军官,二十七日考学生。请即先期在沪考试,毕即归,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各事皆如兄意进行,四月一日筹备完竣,并闻盼复。
恺蒸(三月十日)
三天之后,廖仲恺回到筹备处。一脸苦相的筹备大员们围拢来,使得矮小的廖仲恺显得更加矮小。右眉上那颗黑痣却显得更大。他望着一张张目光专注、凝神屏息的面孔,这都是党军的精华,年轻有为和老成持重的,是国民党复兴的希望。他们到来之时,还都带着明显的热烈情绪,屋里充满了忙碌气氛。现在已有人在收拾公文包。筹备处的木牌也被人卸下,丢在角落里。他缓缓说道:
“应该了解,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
“留下这个烂摊子,谁来收拾呀。”有人还想离开。
“我。”廖仲恺不动声色,“在蒋先生回来之前,由我代行委员长职责,已报孙总理照准。”
军官们放心地点点头,随声附和了几句,又各自忙开了。
总务会计扔掉抽了半截的烟,皱着眉挨近廖仲恺,小声说:“孙总理曾呼吁各方资助经费,可至今才筹到一万元,重修校舍已全部花光。”
“广东筹饷局呢?”
“只给了5000元。”
“枪支呢?”
“仅有30支。”
“怎么这样少?”
“广州重要税收如番摊馆等机构,多半控制于滇军范石生之手。”
“我找他要!”
“先生!”总务会计闻言色变,“你不要去碰钉子了。蒋先生就是找他筹款,而被他当面奚落,一气之下离了广州。”
“就是给他磕头下跪,也得要钱呀。”廖仲恺边说边往外走,回头嘱咐着,“你查查蒋介石的回电来了没有。如无,再去封电报,就说,请他即行,以免先生加受一重精神上痛苦。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
在军阀烟榻上求款前面就是石公馆。这是一所半倾圮的房子,好赖用四方木头支撑着才不致倒塌。
四条挂有各种颜色的小旗和小电灯的彩带从屋顶拉过街道。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各条大街上的路灯都亮了起来。在这之前,廖仲恺去了几处,却没筹到一分钱。他强打起精神,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范石生府上。
穿着一双肥大鞋子的廖仲恺下了车,歪斜着脚步登上台阶。他走起路来老是这样。门卫客气地向他点点头。
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正卧在雕花牙床上抽大烟。他硕大的身躯一起一伏,像座活动的山。他嘴唇紧裹着烟枪的绿玉嘴,好像吹箫似的,两眼凝视着烟斗里的黄色烟泡一蹿一蹿的火焰。见廖仲恺进来,动了动眼珠,用手拢住飘动的火苗,托住烟枪,使劲抽了三口,这才欠起身子,招呼着:“借钱来啦?”
廖仲恺猛地一惊,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从你们那鸟军校来的,没有一个不是开口要钱的!”范石生一面说,一面指着廖仲恺腋下的黑公文包,“你要是那码子事,请免开尊口,我说出粗话来,叫你这个读书人脸皮发烧。”
廖仲恺马上随口答道:“哪里哪里。我是开会路过府上,进来看看。”
“我就喜欢你这个斯文劲。不像姓蒋的,跑到我这里张口闭口孙总理如何如何,他孙大炮借钱对我也是毕恭毕敬,我还尿你臭小子那一壶!”
范石生骂得痛快淋漓,骂完,又躺倒去吸他的鸦片。可廖仲恺站在厅中央,脸上红一阵、紫一阵。他是读书人,出身美国华侨家庭,多次出任孙中山组阁的财政部长,经他手下拨动的款子成千上万,他却不曾动过一分一文。他虽然谦恭温情,可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要低三下四地去登门乞讨!特别是他对范石生那种军阀趾高气扬的高傲态度从生理上厌恶。受了侮辱的自尊心在交战。嗓子眼发干,眼眶潮乎乎的,他真想一走了事,或者破口大骂,出出怨气。
他没走,也没骂,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望了望屋顶上的吊灯,马上提起精神,显出兴致极高的样子,赔着笑脸,在范石生床边坐下,凑近烟灯,帮助范石生挑着烟泡。范石生受宠若惊,朝门口一扬手:“再拿一副家伙来!”
廖仲恺急忙摆手:“我没这个口福!”
“你是男人不是?是就上来!”
烟具端来了。廖仲恺犯了难。他半生走南闯北,还真没吸过这玩意儿。为了使范石生欢心,为了军校的日子……他咬了咬牙,只得豁出去了!凑近烟嘴,使劲一嘬,苍白的两颊凹了进去,两眼哗地流出泪来——心也在流泪。虽然吸得十分不得法,还说不出烟的味道如何,但他还是连声夸奖烟的劲头好。“要这样!”范石生做起示范。
嘴唇闭得天衣无缝,没有一丝烟雾漏出来。随着他粗大的喉结往下一走,范石生仰面朝天,骨碌碌吐出一长串烟,舒服得直拍肚子,漆黑的胡须跟着抖动。
廖仲恺从自己博学见闻里挑出几段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范石生听。范石生闻所未闻,吃惊地张大了眼,连烟都忘了抽。正在要紧关头廖仲恺一下打住。范石生像个孩子般地纠缠起来:“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嘛……”廖仲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轻声说:“这是郊县该纳的一笔款子,你太忙,我给你代收一下。”
有一刹那,那双老眼发亮,露出一种老奸巨猾的神色。
“数目不大。”廖仲恺哄着。
“干什么用?”
“我的住宅破烂不堪,想重修一下。”
“你自己用多少我都给得起。就是不能搞鸟的军校。”范石生从怀里摸出个小图章,放在嘴里哈哈气,朝纸条上使劲按了个印。又想起那个没完的故事,催问道:
“后来呢……”
心绪不宁的蒋介石打了毛氏
蒋介石接到廖仲恺催回的电报,索性带着陈洁如,躲回奉化溪口老家。
溪口镇四面环山,一条剡溪曲曲弯弯。它是剡溪的第九曲出口。
蒋介石回到溪口前,下过一场雪。在背阴尚有未融化的积雪,映得屋里一切东西都泛白发亮。蒋介石独自坐在案前,给廖仲恺回信。信中极力推说他不回黄埔是对苏俄顾问的不满。他又铺开纸,准备给胡汉民、汪精卫再写一封,陈述不回军校的理由。正在这时,放寒假回来的蒋经国带着几个小同学,从楼上疯跑下来,惹得蒋介石一阵心烦。照他的一脾气,大骂一通才解气。他看见墙角神龛里母亲留下的那尊佛像,回想起当年母亲替他祈祷望子成龙的虔诚劲儿。也许是父亲蒋明火的遗传性格,他是天生的火暴脾气。和镇上的儿童戏嬉,总要做“大阿哥”:“我若做官,要做没有人管的大官”。他的功课似乎就是打野仗:经常邀集一大群少年同学到溪边沙石滩作械斗游戏,有的拿木棍,有的拿竹刀竹枪,排成阵势,由他发号指挥,直打得头破血流才散场。母亲因他常常闯祸,气愤不过,有一次随手拿起一根杠棍要打他,他急忙钻进床下躲藏,王氏举棍向床下捣他,被他猛力推开,迅即从床下钻出来逃之夭夭,气得王氏号啕大哭。15岁时,母亲给他讨了个老婆毛福梅。
成亲那天,正当燃放爆竹,把新郎新娘双双送入洞房之际,蒋介石的顽劣脾气发作,他把头上的红缨帽掷在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跨出大门,去跟凑热闹的村童抢夺爆竹去了,弄得新娘满脸羞红,两旁人则莫不掩口暗笑,摇头叹息。自己尚且如此,经国还不到当年自己结婚的年龄,随他去吧。他又沉下心来写信:
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对于军事亦徒仗一时之奋兴,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可目为狂且也。近来益感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为人。乃觉半生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自思生长于今,已三十有八年,而性情言行,初无异于童年……不惟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故人人应视我如孩提,而待我以至诚;亦即人人应曲谅我暴戾,体贴我愚拙……兄等如以弟非出不可,则当为弟代谋一持久之策,如何乃可使其安心乐业,以期成也。
毛福梅招呼蒋介石上楼去吃饭。毛氏有洁癖,除了把经国的衣裳换洗得干干净净外,就是指使侍婢打扫揩抹,使得丰镐房里里外外,窗明几净。今天她亲手烧了一锅鸡汁芋艿,这也是家乡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