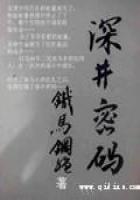墨玉点了点头,上前对着颦笉行了一礼:“侧王妃,这是公主的院子。她也是刚回,您还是晚点再过去请安吧。”
颦笉含泪笑道:“有劳姐姐,刚才是我造次了。”
含香见颦笉满腹凄楚地走了,忍不住对着她的背影深深一叹。自己又对着众人吩咐了一番,方才进了院子。她见梵月已经带着天均把书房翻了个底朝天,走过去叹道:“梵月,我知你今日也是为驸马不痛快,只是此事和侧王妃没什么关系。依我看,她也不过是个可怜人。俗话说,伤人不过舌头,我们又何必雪上加霜。若真把她逼急了,对公主未必就是福气。”
梵月撇了撇嘴,见天均在桌子后面偷偷看自己,对着他笑呵呵的做了个鬼脸,方才蹙眉道:“姐姐,我知你们个个不肯做恶人。可早上驸马的神情你也瞧见了,那么难听的话,这做岳丈的也说得出来!难怪驸马一心一意还是念着咱们公主。驸马既对公主好,我帮他出口恶气也是应该的。”
含香又笑又气:“你这丫头,原来也知道有人说话难听,你也不听听你自己素日嘴里红口白牙说了些什么。侧王妃他爹就是那种脾气,也不是单对咱们驸马才那样。你明知驸马不待见她,我们又何苦再去难为。让旁人笑咱们公主小性,究竟又是什么好名声!”
梵月听了,倒是低头想了想:“姐姐这话也是。既然驸马不待见她,我便也当见不到吧。”
含香见梵月肯听劝,一笑作罢。然而梵月和天均在书房里又翻了一会儿,见哪里也找不到他口里说的“蓝色封皮的,公主师叔留下的小册子”,放下手里的书,一个人走到含香身前,神神秘秘道:“姐姐,我刚才倒是又想起了一事,咱们公主以前多精神爽利的一个人,功夫和咱们驸马都不相上下。可自从侧王妃进了门,就一直病病歪歪的,你说这事是不是和侧王妃有什么关系?莫非是属相相克,冲撞了?又或者被她落了什么符?…”
含香听她越说越离谱,忙打断了她的话:“梵月,你可不是疯了。亏你还是宫里出来的人,这种话你也敢乱说。公主的起居一向都是我照料,莫非你是怀疑我在饭菜里下了毒?”
梵月忙笑道:“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事蹊跷,我要查一查,若真的与侧王妃无关,我便从此与她井水不犯河水。”
含香摇头一叹,也懒得再去理她,起身走开了。梵月见天均在书柜后面一身灰头土脸,笑着将他拧了出来,替他好好梳洗了一番,又拿了两块羊脂白玉,衬着两方碧雨天青绸束了两个稚角。含香回头见她居然拿了两卷缎子急急忙忙要为天均做套新衣裳,也不由对着他们大笑:“你这丫头就是个死心眼的,那里又爱死了?!这孩子也有福气,你梵月姐姐的手艺,宫中的织造也不过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