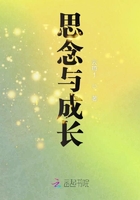唐黛跟着叶独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山路,如果说上山的路崎岖,那么下山的这条路或许已经不能称其为路。
到最后叶独城一手挟着她,一手抱着那个刚刚出世的婴儿,几乎是跑着下山的。
兰若寺地处城郊,月色虽佳,居民却大多已睡了。
偶尔三两声蛙鸣,夜静谧而寂廖。
叶独城抱着孩子大步走在前面,唐黛这时候却分外清醒:“叶独城!”她跟上去:“我们得找个人家,它……它可能要先吃点东西。”
叶独城神色严峻:“我必须带它回寿王府。”
唐黛知道自己争不过他,他之所以取出这个孩子,而不直接带走何馨,也只是不想累上唐黛。若是何馨活着,朝中便难免有人会借着她牵出唐黛,再牵出沈裕。
弑君之罪,足以撼动位极人臣的寿王。所以便是沈裕也只有出下下之策,就是要何馨永远闭嘴,死无对证。
何馨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她下手的时候已经知道结果。其实王上一直以来对她不错,他在试图用所有的宠爱去补偿那个他已经错失的人,只是可惜他遇上了何馨。
在何馨的世界里,爱与恨永远不可能相互抵消。
唐黛并不打算和叶独城争执:“就算是要带回寿王府,至少也得先喂它一点东西,你总也不希望带回去的是具婴儿尸体吧?”
叶独城的脚步便放缓:“找户人家吧。”
深夜敲门,一般人家是不敢应的。两人最后也只得找了一家规模极小、尚在营业的客栈,多给了小二几个赏钱,让他捣了些米,熬成米汤。
唐黛和叶独城都没照顾过婴儿,它实在是太脆弱了,叶独城将上衣解开,将它贴着胸膛,保持着它的体温。唐黛待米汤凉了,便准备拿勺子来喂,她舀了满满一勺,叶独城看了半天终于开口:“会呛死它的!”
唐黛轻咳了一声,将勺子里的汤倒去大半,轻轻沾在它唇边,那时候它也哭累了,皮肤皱皱的,全身泛红,还没有上次沈裕猎到的那只灰野兔个儿大。
唐黛小心翼翼地将汤喂进去,它还不会吃东西,喂了半晌也没吃多少。反倒是叶独城的衣服上全沾了粘稠的米汤。
唐黛很担心:“它……它好像吃不进去。”
叶独城也摸不准:“也许吃不了多少……”他倏然抬头看唐黛:“你先回去,这件事和你没关系。”
唐黛只能摇头:“这件事已经不可能和我没关系了。”
叶独城将它重新抱进怀里:“你知道何馨做了什么吗?那是诛九族的大罪。若是累上你,整个寒府怕都要受牵连。”
唐黛用手指去触它皱皱的脸:“你家王爷又不傻,若是他一旦发现王上死在浮云小筑,第一件事就是找何馨,刑远现在还在刑部大牢,要找何馨第一个就是找到我。他现在估计早已经派人将寒府包围了。我回不回去……没有区别。”
叶独城暗惊于她的镇定:“你想到应对之策了?”
她逗弄着他怀里的小婴儿,却是答非所问:“世人总说救命稻草,其实稻草救不了命,它只是给人以希望……徒劳的希望。”
二人回城时,长安城城门已经关闭,守城的军队竟然换成了护卫皇宫的御林军,长安城全城戒严。
叶独城向守军出示了寿王府的腰牌,又因着他们是入城,守城官兵严格盘查后将他们放了进去。
那时候寒府果然已经被重重包围,寿王正忙得不可开交,好在他本就负责长安城防,各关卡大多都是他的人,才不至于临时抱佛脚。
王上的死讯被严格保密,宫门提前落锁,好在他府中本就训养着死士、暗卫,为防异动,当下便将长安城握有兵权的外戚及亲眷控制住。
朝中诸臣,又属潘太师之子潘烈手中兵权最重,沈裕怎不知此人处处与己为难,却终碍着他一门忠烈,不予计较。如今王上初薨,太子年仅四岁,不堪大用。
非常时期,潘府便更是被明里暗里盯了个飞蝇难出。
琐事难叙,寿王沈裕一夜未眠,及至天色微明才匆匆回了一趟寿王府。
而长安城的百姓仍一夜好梦,改朝换代或是江山易主,皇城里发生什么事,他们其实并不关心。
这是唐黛第一次正式进到寿王府,穿越之初她曾经参加过寿王的诗会,还背了一首《将进酒》冒充原创来着,当时还没来得及多看两眼府中景致,便被裕王给叉了出去。
而今她当重新坐在这寿王府的客厅时,时间已过四载。
她怀里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孩,沈裕大步踏进堂中时,她正低头出神地看它,那情景不像是一个犯下重罪的自首钦犯,更像是千里抱子寻夫的秦香莲。
家人也素知自家主子的德性,尽管叶独城已经着人去兰若寺取何馨的尸身,但见是她抱婴孩而来,都没敢怠慢。而唐黛低着头却不是在看那小东西——她等得都快睡着了。
“王爷。”她这次很乖,听见他的脚步声便站起来。
“嗯。”他似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两个人有半年没有见过,唐黛当然是不想看见他,能躲便躲是最好不过。他却也觉得搁不下脸面,他毕竟是皇族,不是伏虎山或者什么山上的流氓匪类,霸王硬上弓这事,他自己也知道不光彩。于是便也懒得与她照面。
他走到唐黛面前伸出手,唐黛半晌才会意,将手上熟睡的婴儿递给他,她生怕他模仿着越氏孤儿里面的情景,将它当场摔死,递过去时便出声:“它才八个多月,很孱弱。”
沈裕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手中婴儿皱巴巴的小脸:“八个多月?”
唐黛点头,声音很是犹豫:“何馨不愿告诉我它的父亲是谁。”
沈裕对此自然是存疑,他并不十分相信唐黛的话,但是唐黛也明白实则虚之的道理,就好像何馨递给她的信件不作落款一样。只有虚假之物才会担心旁人的质疑,于是也就做得愈加有凭有据。沈裕不会想让这个孩子活下来,他的母亲弑君,是大荥王朝的千古罪人,他没有活下来的资格。而执政者,自然也不会埋下这个祸种,让他数十年后再来复仇。
但古时对皇子看得非常金贵,只要这个孩子有一分可能是王上的骨血,他下手时便会有几分顾虑。
沈裕果是沉吟了一阵,半晌他语声冰冷:“来人,将唐黛押入刑部大牢,以待后审。”
有侍卫上来拿了唐黛,用铐链缚了,便准备带往刑部,出门前他又吩咐了一声:“此乃重犯,未经本王允许,任何人不得提审。”
侍卫恭敬地应声,带着唐黛出去,唐黛还有两件事放心不下,可是她只说了一句:“王爷,朝廷的人肯定会要求重殓何馨的尸首,孩子……”
裕王并未转身:“去吧。”
唐黛想了半天,寒府的情况她最终也还是没问。也许这时候,只有漠不关心、绝口不提才是最终的保护。
唐黛便住进了刑部大牢,这里的格局和大理寺大致相同。只是她再也不可能遇上那个叫何馨的女子。
因着之前带兵,沈裕治下严谨,刑部大牢的风气倒是好很多,至少女囚的狱卒是不敢随意施虐的。整个大牢里一直有人巡视,每次时间间隔大约两刻。
唐黛就这么坐在那堆稻草上,外面已是天光大亮,牢里却只从气窗——准确地说应该是气孔里面依稀透了几束阳光进来。
这是六月的清晨,隐约可以听到渐起的蝉鸣。
唐黛突然就后悔了,她觉得或许自己不应该将何馨带出来,这样安安静静地呆在牢里和那样惨烈的死,也不知道哪种结局更偏圆满一些。
牢里与牢外,一堵厚墙隔成两个世界。
王上的死讯在第二天正式公开,皇城的九五丧钟一声一声,肃穆哀重,响彻半个长安城。
大荥举孝。
先王承明帝平生不好女色,后宫虽有粉黛六百余人,所得却也不过二女一子而已。东宫太子沈曦年仅四岁,朝中表面平静无波,暗里却是谣言四起。
四岁孩童登基,即使是戴上帝冠,穿上皇袍受万臣朝拜,最终也不过只是一个傀儡。一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懂得什么叫江山?什么是社稷?
而承明帝兄弟六人,现今真正余下的不过寿王一人,他现虽是文官,手无兵权,但军中旧部大多还在,而且他负责长安城防,这皇城兵力,大部分还在他手上,太子难以成事,只听令于帝君的御林军群龙无首。大家明里不说,暗里都在看着他如何窃国呢。
所以当次日晨,寿王进入东宫的时候,他的皇嫂表面上强作镇定,而端茶的时候,执盏的手都在抖。
她其实已经视他为洪水猛兽。
这就是信任,权势面前,危难关头,它不会比一张A4纸厚多少。
只有四岁的太子沈曦,仍然如往常般扑上来,声音还带着奶气:“裕皇叔!”他径自扑到裕王面前,将他的又腿抱住,仰头看他:“裕皇叔,你是来带曦儿去骑马的吗?”
皇后伸手想将儿子扯过来,却又碍着裕王,不敢动作,她只有僵硬地笑着:“曦儿,母后和你裕皇叔有些事情要谈。”她很自然地示意乳母将太子带下去,裕王爷却伸手将小家伙抱起来:“皇叔过几天再带你去骑马,到时候皇叔还教你射箭!”
四岁的沈曦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看见了母后的哀容,心思却还停留在和宫人的前一场游戏里:“那曦儿要射黑熊,父皇说黑熊是最凶猛的猎物了!”
沈裕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其实哪种猎物最凶猛,实在是很难说清的事。比如承明帝沈辄曾猎杀过六头熊,最后却死在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弱女子手上。
他将沈曦放在地上,乳母赶紧上前将年幼的太子抱了下去。皇后面色苍白,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时,她选择自保:“裕王爷,别的哀家就不说什么了,这大荥本就是姓沈的。曦儿年幼,这皇位他……”
时值盛夏,这坤宁宫有着冰雕降暑,而皇后却只觉得香汗淋漓。前一刻还是恭顺臣子的人,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就取她们性命。
那天沈裕着了深紫色的亲王朝服,他的目光如若深潭,表面平静,暗里激流凶险。他阅人无数,如何看不出自己皇嫂的心思,却一字一句,缓慢清晰:“臣弟已命礼官准备太子殿下的登基大典,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子虽然年幼,但有众臣辅佐,总会长大的。”
他不作此说尚好,话一出口,皇后更是面色如霜:“皇叔!”她竟然是不顾礼仪地扯了裕王的袖角,语声近乎哀求:“皇叔……曦儿年幼,求……求你放过他吧。”
她久居深宫,阴谋诡计已见过太多。而且……而且寿王与承明帝之间的一段旧怨,虽外人无从得知,她却是清楚的——那时候她已经是太子妃了。
四岁的太子,懵懂无知。她的父亲乃旧相,现已赋闲在家,朝中无势,便只好求个平安。若是裕王想要登基,放了她们那是最好,但就怕他心思狠毒。
先筹备太子登基大典,然后让太子在登基前或者后几天莫名死去,既堵了守旧老臣的嘴,又全了他一身忠孝之名。
她心思百转,语声已成哀求,而那个她视为即将取她母子性命的魔鬼只是静静地站在宫殿中央,夏风穿过中堂琉璃的珠帘,微撩起他金线绣祥云的袍角,紫气微漾,天神降世一般。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恐惧,神色依旧波澜不惊:“三天之后,是个好日子。皇嫂准备吧。”
辛卯年丙申月丙申日,宜祭祀、上册、受封、临政。
大荥幼帝沈曦正式登基,帝号顺隆,改国号丰昌。
同时,太后代新帝拟第一道圣旨,称因太子太过年幼,特赐权寿王沈裕监国,代帝君处理大荥一切政务。
江山其实并未易主,但悠悠众口,难免也就栽沈裕一个专权窃国的罪名。朝中老臣也有些是有意见的,但是四岁的孩子,真的是太小了。
思来想去,除此之外,竟是再无良策。好在他本也是嫡系的皇族血脉,这事便也就这般定下了。
新君临朝,这番更换,总算是未引出什么风波。
裕王直到半个月之后才去到天牢,那时候他已经是监国,何馨的尸首自然也是有人要求详验,但已经被野兽吃得只剩下一颗头颅,几根枯骨。于是这事,竟然也就栽赃给了太平天国的余孽,最终不了了之。
而唐黛与何馨交厚众人皆知,论理罪当同诛。监国大人沈裕以半个月时间下定决心,此人若是再留下,先帝死因与他怕是难脱干系,于是唐黛是无论如何留不得。
他站在刑部大狱的牢门前,神色严肃。狱卒不敢怠慢,紧紧地开了牢门,后面有人捧着托盘,里面竟然是几样可口小菜,一壶酒。
也不知是否从寿王府带过来,那壶身极其精美,配得上“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形容。
因有裕王在,狱卒搬了一方小桌进来,将八样小菜仔细摆好,却只放了一双碗筷。二人相对而坐,沈裕亲自替她斟了酒,语声不紧不慢:“临死之前,有什么心愿么?”
唐黛心中狐疑,仔细地留意他的神色,却见他神色严肃,不似说笑,心中亦是懊恼。她心知若自己的罪名定下来,寒府的人绝对跑不了。刺杀国家首脑,放在哪个时代也是诛九族的大罪。
她小心翼翼地喝了半杯酒,终于忍不住小声道:“小民还真有一个愿望。”
“哦?”沈裕坐到她身边,用她的筷子挟了口菜:“说。”
唐黛可怜兮兮地看他:“请王爷准许小民老死吧。”
沈裕拿了精致的酒壶,仰头往嘴里一倒就是小半壶,再给她斟了一杯:“你这算是求本王么?”
唐黛慢慢啜饮着杯中酒:“小民求王爷,让小民老死吧。”
说话间沈裕终是将壶中的酒倒尽了最后一滴,他劈手将壶往角落里一摔,砰地一声脆响,酒壶碎成一堆瓷片。响声惊动了狱卒,但见他无事,没人敢过来。他突然觉得很解气,语声仿佛也带了酒气:“本王准了!”
他用了半个月时间下定决心处死唐黛,又在一壶酒之后成功反悔。
唐黛只是看那一片白色的碎片,它们本是瓷土,某日因着机缘巧合摇身变成瓷器,而后又将还原为瓷土。地球是圆的,你以为你能走很远,而实际上,你不过是在划一个圈。
到最后,发现终点亦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