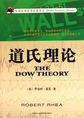边子远刚刚开完一个项目会议。他在会上严厉地训斥了开发组的负责人,进度太慢,BUG太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却没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最叫他无法容忍的是,那个项目主管居然以梅氏实验室的老人自居,仗着早年和梅教授的交情,在会议上公开顶撞他,说他“年轻、冒进,缺少对科学的敬畏”。
早已今非昔比的边子远当场拍了桌子。说到对科学的敬畏,他自认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超过他,毕竟谁会冒着失去生命和精神失控的风险,往自己的脖子上装芯片呢!
当然,他不会把自己为科学作出的牺牲像长舌妇一般地去宣传。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天才从不卖弄自己的天才,伟人也从不炫耀自己的伟大。
如今的他,是的确可以用伟大来形容“自己”的,尽管他的脑子已经变成了包租婆的屋子,快要住不下了。但只要一想起自己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以及将给世界带来的变化,他就飘飘然了。而最飘飘然的时候,无疑就是梅子青靠在他怀里的时候。
有时候,他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就像那些被外星生物寄生成功的家伙一样。这时候,他就会感到恐惧和孤独。
恐惧和孤独的时候,他就会去喝酒。唯一能陪他喝酒的,只有传达室的老于。
老于大概是梅氏实验室剩下的唯一一个与科研无关的人了。
从边子远进入实验室工作开始,这几年实验室已经经历过几次无人化改造,人工智能代替了大部分技术含量低的劳力,包括安保和清洁。
原本老于也在裁员的人员名单里,上一次无人化改造时,他就应该被清退。但梅以求主张留下他,理由是“保留一个时代的印记,让实验室留下一点人味儿”。
大多数人都没有反对,人工智能们也没有提出“意见”,反正老于也抢不走它们的饭碗。
边子远是乐意老于留下来的,至少,他喝酒的时候可以不那么孤独。
他愤怒地从会议室出来,把重重的摔门声留在身后。
他决定去喝酒,在离开实验室大门的时候,他想起了老于。
他朝老于所在的那间特殊的传达室看了一眼。之所以特殊,是因为那间屋子是整栋大楼唯一没有经过人工智能改造的屋子。屋子里用的还是几年前的电路,电脑也没有换过,甚至还有一台老式电视。现在,已经没有人看电视了。
老于没在屋子里。边子远有点失望,但很快就调整了心态。他现在毕竟是实验室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梅以求病重住院之后,梅子青成了实验室的实际掌控人,而他无疑是二号人物。他不能让人发现他内心的脆弱,不能让人看见他总是去找传达室的老头一起喝酒。
老于正在大门外的院墙角扫地,地上并不脏,有几片零星的落叶,大冬天的,树都已经光秃秃的了。
边子远经过老于身边的时候看了眼无处不在的监控,站直了身子,扯了扯笔挺的西服,轻轻咳了一声,像个领导那样说:“扫地这种事,让自动清洁机器人干就行了。”
老于抬起头,却抬不起佝偻的背。他扶着扫把站在那里,比边子远矮了一个头。
他说:“没事,我就是个劳碌命,闲不下来,一闲着,就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
边子远说:“唔,说得好啊,公司里做项目的人要是都有这样的觉悟就好了,一个个做事拖拉,不求上进。老于啊,我看要不明天组织个全员大会,你去给大家讲讲。”
老于连忙摆手:“哎哟,我可不成。我能讲什么?我啥都不懂。”
边子远说:“就讲讲你这种闲不住的心态,现在这个时代啊,缺的就是你们老一辈人的干劲和精神。”
老于说:“边总,您可别开玩笑了。这年头,我连扫个地都显得多余,哪能给你们这些大科学家去讲话呢!”
边子远也不再坚持,拍了拍老于的肩膀说:“没事,你好好干,实验室需要你。”说完就背着手走了,没提喝酒的事。
老于在背后喊他,“边总,外头冷,您不套个外套啊!”
边子远这才感觉到寒风刮在脸上像冰刀子。实验大楼里面是恒温的,永远保持着春天般的温暖,和外面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他出来的时候还受到会议的影响,余怒未消,热血上头,倒是忘记了寒冷。
他想回办公室拿风衣,最终还是没回头,忍着那忍不住的瑟缩,尽量在寒风中保持身体的笔直,微微凸起那不算明显的啤酒肚,仿佛这样就能抵挡西伯利亚南下的冰寒大军了。
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开过来,停在边子远面前。他上了车,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说:“天这么冷,去喝口酒吧。”
老于扶着扫把,看着汽车方向盘无人自动,幽灵般地开走了,憨憨地笑起来。
“喝酒,好啊,喝酒好啊……”他把最后几片树叶扫到角落,对着那个长得像勒色桶的自动清洁机器人说,“交给你了,我喝酒去了。”
老于放好扫把,转过身,佝偻着背走了。他没有注意到,一阵风吹来,那些收拢的树叶又被吹散了。
长得像勒色桶的机器人麻利地在地上转了一圈,所有的树叶就都收进了它的腹中。它回到它原先站着的位置,身子摇晃了两下,仿佛在嘲笑老于的笨手笨脚。接着腹中发出一阵吹风机似的呼呼的声音,又似吃饱了般打了个嗝,便定定的不动了。
老于来到小饭馆的时候,边子远已经在角落里坐了。桌上放着四个小菜,一瓶二锅头。这是他们喝酒保持的习惯,被戏称为四老——老地方,老四样,老一瓶,还有老于。
边子远说:“就我是多余的。”
老于说:“那是因为你年轻,你不老。”
边子远说:“是啊,等我老了,就变成五老了——老地方、老四样、老一瓶,老于和老边。”
老于说:“不,还是老四样。因为你老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边子远就莫名地伤感。
只有喝酒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真实的边子远。不是天才,不是科学家,也不是领导,更不是被寄生者。他就是边子远——曾经心怀梦想,又喜欢打游戏的那个边子远。
他说:“于大爷,你活了一辈子,值了。”
老于说:“我有什么值的,一辈子啥也没干成,不像你们,干的都是大事。”
边子远说:“不管大事小事,至少你踏踏实实活了一辈子。说不定明天世界就没了,大家一睁眼,发现只是做了个梦。”
“怎么会呢!”老于咪着酒,也眯着眼,“要是做梦,我不也得醒?”
“那您至少也是做了一个完整的梦啊!”边子远说。
老于说:“真要是做梦,晚醒不如早醒。”
边子远说:“真要醒了也好,就怕从一个梦里呀,掉到另一个梦里。”
老于说:“管它几个梦,那就喝酒!”
边子远举起酒杯,“对,咱喝酒。”
一瓶二锅头下了肚,边子远起身要走。
老于问:“要不再喝点?”
边子远穿上外套,掸了掸肩膀上那有的没的灰,又变回了领导的样子,挺胸抬腹地说:“人要守规矩。”
老于不觉得四老是个规矩,刚想说点什么,边子远忽然问他:“你是不是也在玩梦境指南的游戏?”
老于点头说:“是啊,去年教授把他用的那个旧空间盒子给我了,说实验室人人都有,不能独缺了我。嘿嘿……其实,我也不太会用。”
边子远拍拍他的肩,说:“不会用最好,以后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