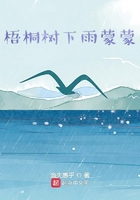李伦受儿子牵累,暴罪于后,儒师声名尽毁,谥号强夺为“文缪”,穷尽一生光耀的门楣至此崩塌殆尽。
铁屑楼掌柜在开封狱喝半月稀汤,得释后再世为人,二话不说到行会挂牌,托个可靠的知见,早早盘出地契回江南养老去了。
地契虽好,得之不易。新主顾姓苏,久浸商贾,待人一团和气。苏老板出手十分阔绰,酒楼大修一番,更名“人间秀”叫板樊楼,素日座无虚席。
“向未曾闻,晏探花也是个风流人物?”
“金明池,琼林宴,由来便是做媒的好地方。”
“俏帝姬,憨驸马!鸳鸯被里滚作堆,待制跌脚啐,亏亏亏!”
雨水渐滚,伞面紧绷,华无咎入楼暂避,略扫几眼,堂内一座大笑。
人间秀三层楼,凉薄雅致,内外三进深,他拣个不打眼不冷僻的位置,要一壶金片,只待雨停再出发。
“漫说是晏探花!”酸秀才口无遮拦,不晓得天高地厚,大谈登龙道,“科举但凡再开,贾某必当金榜题名!”
“贾秀才芳龄一甲子,难道还指望做驸马不成?”挑衅者嗄声相嘲。
“贾某再不济也是读书人,你又算个什么东西?”贾生拱手讥笑道,“怕不是浪荡子弟的入幕之宾。”
那人跳起来举壶便掷,差一寸未着贾生脑袋,酩酊怒叱道:“爷爷在皇城司高就!当街取你性命,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酸儒大惊,从头到脚淋个透彻,蹬一双兔腿便跑,那人绕堂紧追,一条长凳抡得虎虎生风。不过片刻,大铛头围拢醉汉,两方亟将大打出手。
“这位好汉,且卖老朽一个薄面,要打出去打。”
在此关头,苏老板施施然负手现身。贾秀才早也遁去无踪,二人所经之处一片狼藉。醉汉酒醒泰半,捋直舌头问道:“可否赊账?”
“三条白金,只当交个朋友,”苏老板笑哈哈道,“人间秀开张未久,断不能起了作乱的风头,倘若好汉手头不宽裕,也可留下皇城司腰牌暂抵。”
那人嘶声挠头,显见是个两袖清风的穷鬼。苏老板挥手,大铛头乌泱泱齐上,正欲扒掉他一身人皮,忽闻旁处高声道:“且慢。”
华无咎远扔来一只金荷茄袋,铛头接过,登时喜不自禁,袋中五枚银锭散发荧荧幽光,模样着实爱煞人。
苏老板顺台阶下,吩咐道:“上几道好菜,再请这位朋友喝一碗醒酒汤。”
醉汉三两步自来坐好,并不和华无咎见外,抱拳做个请,咧嘴一笑道:“大恩不言谢,在下陆畸人,敢问兄弟如何称呼?”
勾当官心道,男生女相,无怪受人揶揄。
“鄙姓华。”
陆畸人打个酒嗝,桃花醉眼,倏忽变色叩首,惶恐道:“小人醉得厉害,有眼不识泰山,华勾当恕罪!”
华无咎不叫他起,左右端详,扇柄往桌案一磕道:“脚程是快,这么一番打闹,衣裳半滴酒水没沾。”
“小人一匹活马,抽一鞭快一刻。昨日为勾当效劳,幸不辱使命!”
华无咎道:“可惜,太快了。”
陆畸人摸不着头脑,又打个嗝,自掴大耳刮子道:“是小人的罪过。”
勾当官曲指敲案,示意他起身,陆畸人脸上红红白白,又叩一头,虾腰在旁侍着。
“不必拘谨,只是讲些闲话。家中排行第几?”
“回勾当话,小人慈幼庄出身,无家无室的没个排行,”陆畸人赧然道,“早先慈幼庄有个姊姊,待我极好,后来卖去录事巷,小人便一个人过活。”
“不提那些,”华无咎饮茶,“昨日樊楼比试精不精彩?”
“李师师薛灼灼争美,樊楼内外连根针也扎不下。小人去时比罢,虽没福气一睹双姝姿采,去得却很是时候。”陆畸人低声道,“若否,傅提点必以官家安危为先,哪有功夫遣上二指挥捉人呢!”
华无咎见他眉目轻薄,遂道:“谢察子不是常说么,善泳者溺,善饮者醉。你是机巧人不假,事变如风,可不要毁于机巧。”
“勾当眼前人发话,小人向没有不听的理,多谢勾当提点。”
醒酒汤上桌,附赠几例小菜,梅雨天吃来最为爽口,二人殊无动筷之意。
华无咎喝罢金片,肠胃上顶,冒一遭冷汗,于是拾筷吃笋丝,略压郁气,问道:“你那胸前挂了什么?”
陆畸人扯下红绳摩罗像,双手呵腰奉上。木像拇指大小,身缠毒蛇,三头六臂趺坐,脖颈绕一环人指缨络,细密如穗,使人不敢正视。
“是魔?”
“是佛。”
“佛迎香火,必得慈眉善目,而非教人畏惧不前,”勾当官轻嗅佛像,“生魔恶鬼皆以佛名,照你这种说法,我也算是个活菩萨了。”
“华勾当有所不知,此乃央掘摩罗佛,杀九百九十九人得佛度化,戒恶从善,获大慈悲心,成大阿罗汉。
“照梵门这种说法,慈眉善目迎香火是佛,生魔恶鬼放屠刀也是佛,佛魔只在方寸间。
“大理国的小玩意儿,辗转北来,捞它图个新奇,小人并没有想这许多。”
……
……
“敢炸六鹤堂,晏探花也忒嚣张了!”邻桌拍案道,“茂德帝姬已为人妇,他竟不怕御史台参么!”
“情关情关,闯过去才能天高地阔,闯不过便没那条富贵命。”
酒客抖开东京小报,指点江山道:“探花郎少年才俊,庙堂由得他闯,嚣张也自有其本事。何况蔡太师活该。”
“茂德帝姬竟比李师师还好看?”闲汉半信半疑。
“不如你也去相府门前守一晚,与探花郎作个伴?”酒客噱笑,忽扬掌示警,“呔!”
小贼青衫木屐,背诸人而坐,闻言反身狼顾,现出一张笑嘻嘻的粉白脸。
她丢下小报,歉声道:“一时手快。”
陆畸人站直腰,华无咎将摩罗指像还他,恰巧没对上那张脸,漫不经心道:“非香非臭,我不曾闻过这种木料。”
“鬼市贩子说是滇南古木,”陆畸人抬臂系绳,“谢察子瞧见喜欢,不过旧物不值当送,小人说好再给她捞个大佛,看这三头六臂的恶相,上香供奉,拜一拜壮胆,不比拜关二爷强多了!”
“皇城司岂是你们兜搭的地方。”华无咎闻言心口烦恶。
“小人明白,小人明白。”陆畸人连忙告罪。
勾当官起身拿伞,后背倏忽冷汗淋漓,想是风雨夜着凉。一条虫钻进腔子吃穿心肺,把他从头吃到脚,只剩一具麻酥酥的空壳。
“往后管取安分,不许同人兜搭。”
话罢,橘红衫男子拔足而走,搅乱茶汤烟淖。陆畸人弯腰半晌,这才慢抬起头。
“也是个乱喝酸的,”他嘿笑落座,举筷道,“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
摩罗像滑出衣襟,陆畸人掖回去,道:“广府香客竟不识滇南蛊木,勾当官,阎王拦不住该死的鬼,全赖你技不如人。”
狸花猫踱来,酿呜蹭腿不休,他夹一块白鱼,倒金片茶水左右冲洗,洗掉鱼汤辣子,甩丢地上道:“嗟,来食!”
花猫伸舌果腹,盏茶功夫蹬长了腿,一动不动僵卧在桌脚。
……
……
雷疲雨霁,夏云多奇峰。
及至人间秀楼外,华无咎远眺,焦墨云烟随风逐流,直在翻云覆雨手中揉圆搓扁,是个潦草浅薄的命数,说走便走,不留一丝情分。
“三大王一旦回神,便会下令清查蔡京留在皇城司的暗桩,”华无咎心道,“傅宗卿侍蔡有如亲父,必无翻身之地,此人不论真精还是假傻,既为傅门所用,亦会被连根拔起。”
思虑底定,勾当官心稍安,一路摇扇,径往录事巷去。
近来流民奔窜至开封府,京郊混乱难安,巡街卒子倍胜以往,寻花问柳者如常。
花乃桃花,柳为菀柳。桃李之争落幕,菀柳阁鸡犬升天,桃花源门可罗雀。
“华勾当,哎!华勾当!”龟公鼓圆了眼,飞街来迎喜不自禁,勾腰笑道,“自打开春,爹可有日子没来了。”
桃花源粉帘绣户,华无咎挑帘跨进门首,道:“皇司事忙。孝官,你娘闹了没有?”
“爹也知道,娘她性子烈,昨儿输给李行首已是万般窝囊,我好汤好饭侍候着,端怕娘犯心口痛。”那小厮今年十四五岁,生得清秀,引他穿过重帘,伶牙利嘴道,“爹这一来啊,她什么病都溜去爪洼国喽!”
“李师师背后之人轻易得罪不起,你瞧着些,莫让她冲撞贵人。”华无咎叮嘱。
“李行首好脾性,娘寻不到由头顶撞,”孝官叩门喊道,“娘,娘你老人家醒了么?”
深门闺房里劈啪碎响,孝官惊推入内,不禁哎哟直叫唤。
“小混毬子,哪个是你老人家!”
“我若不来,谁能治你疯病!”华无咎拧眉径入,“早讲过白沉香别用太狠,纵能忘忧快活,一旦成瘾,福泽衰竭,十年寿数已是奢求。只输这场,当真输得好!”